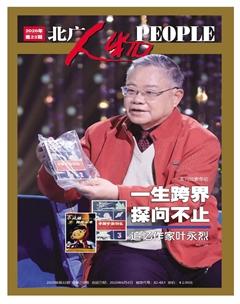郁钧剑:母亲给我留下的两个故事

我母亲在旧中国读过女子学校,肚子里有墨水,所以我是在她讲故事的摇篮里长大的。
母亲留给我的这两个故事
在许多的故事中,有两个,她反复地给我讲过许多次。
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孩子,从小有偷东西的毛病。开始只是偷邻居的一根葱一头蒜,当他拿回家时,他娘不仅不制止,反而称赞他能干、懂事。于是孩子越偷越大,最后被判了死刑。在刑场上他说他想见娘最后一面,娘来了;他又说他想吮娘最后一口奶。娘依了;结果他一口将娘的奶头咬掉了。然后泪流满面地说,小时候,我偷葱偷蒜,你从来没有教育过我。”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位贫寒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儿女养大成人后,自己却病倒了。辞世之前,说想喝碗鲤鱼汤。可是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啊,大雪纷飞、冰封湖面,上哪儿去找活鲤鱼?而此时只见她身边的小儿子飞奔至湖上,解开衣服,硬是用温暖的胸膛在冰面上融化出一个窟窿,而此时,又只见一条大鲤鱼从窟窿中飞跃而出。”
前一个故事是古代的一则寓言,叫《芒山盗》。后一个故事出自古代《二十四孝图之“卧冰求鲤”》。
長大后,我理解了母亲许多次给我讲这两个故事的良苦用心。她还在我懂事后一再对我说,做人的本分千千万,学不尽,用不完。但我只要求你将来在人生的道路上,至少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要诚实,一个是懂报恩。
我是带着母亲留给我的这两个故事走到今天的。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母亲
《三字经》里说过:“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似乎一个孩子的成长与做母亲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我家恰恰相反,母亲一直在言传身教。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我是绝对不可以上桌的,母亲会让我自己搬张方凳,再搬张小椅子坐在一旁,由她不时地往方凳上我的菜碗里夹些菜肴。如果客人是父母的长辈,母亲自己也不上桌,而会一直在厨房里劳作,端茶送饭。但餐桌上的碗筷摆放,如同如今餐厅里服务员的“摆台”,却是要我来完成的。至于吃饭时的规矩,母亲要求的就更多了,如夹菜要夹自己面前的,不能乱翻挑食;吃饭不能吧唧嘴;不能捧着饭碗;不能把鱼刺、肉骨吐在地上,而是留在饭碗里;等等。
我四五岁时开始用毛笔描红,也是母亲要求的。四五岁的孩子练毛笔字,最害怕的是墨汁,有一次我一不小心将墨汁打翻在身上,衣服顿时黑了一片,自己吓得赶紧去洗,没想到越洗越花,好端端的一件衣服就这么废了。正当我吓得不知所措之时,母亲回来了,非但没有责骂,反而和颜悦色地安慰我。她常说要想做大事情,首先要写好字,字如其人啊。她认为一个人长得再漂亮但字写得不好,便一丑百丑。母亲在世的年代,通讯方式大都是写信,她老人家给我写信,抬头往往都是同一句话:“见字如面。”长大后,我渐渐地懂得了这其中包含的多层意思。
一如所有的母亲,爱给孩子的幼时讲故事。像《孔融让梨》《孟母择邻》《岳飞刺字》《凿壁借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甚至《刘备卖草鞋》《韩信胯下之辱》等等,都是母亲至今教给我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因此,小时候我特别崇拜母亲,崇拜她肚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警句格言。遇到我的学习成绩稍有下降时,她会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饭店里吃饭遇到菜的味道好时,她会说“中国的厨子、日本的娘子、西洋的房子为世界三绝”;聊天聊到住房时,她会说“住房是有一间时想两间,有两间时想三间,房子永远少一间”;我上中学特别喜欢地理,是她告诉我“世界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兄长从小顽皮,常常使母亲长吁短叹,于是她又会说“世界上一共由三种人组成,无论出身是贵胄还是草民,只要是上等胚子的上等人,不教自成人,中等人,教教便成人,下等人,教死不成人”。
母亲当年爱唱的一首歌
母亲爱唱歌,她当年最爱唱的一首歌是《妇女翻身歌》。我母亲做过桂林市北上街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委员。她说她与我父亲结婚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地点在江苏海门乡下。那时候苏北乡下是新四军十分活跃的地区。
母亲说当时经常出入家里的有一对新四军夫妇。后来,她与父亲在桂林迎来了解放,当时有不少南下的部队在桂林做短暂的休整,也有部队临时驻扎在我家东镇路25号前院的西南纺织厂里,而在这支部队里,居然会有当年的那对新四军夫妇。母亲说,《妇女翻身歌》就是那位新四军大姐教唱的。
母亲爱唱歌,她在单位唱,在家里也唱。有母亲歌声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灿烂的岁月。有母亲歌声的岁月,也是我家最和谐幸福的岁月。陶醉在母亲的歌声里,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是忧愁和烦恼,感受到的尽是亲情的温暖与甜蜜。
邢大军据《新民晚报》郁钧剑/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