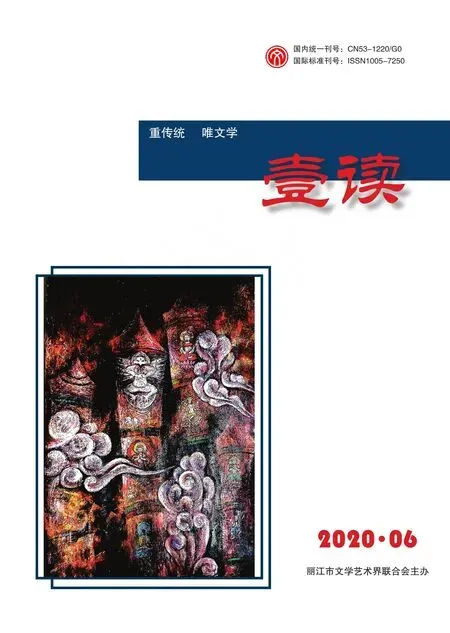丽江的雪及其他(外一篇)
◆杨学韬
生长在滇西海拔较低的三川坝子里,与雪相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小到大,与雪的几次相逢都在故乡之外,而且,非常之巧的是,每次与雪相逢都是吉日良辰。
第一次与雪相逢是在丽江,美丽的丽江是雪的故乡。那次下雪,从元宵节开始,一直下了三天三夜方有个了结。铺天盖地的雪把个丽江坝子装点成童话世界,苍茫雪原,与千山万岭连成一片,与巍峨的玉龙雪山融为一体。大雪把道路封住了,把千家万户的门封住了,原野没有车辆行驶,山庄没有人影出没,“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偶尔,有一个披簑戴笠的纳西农妇,突然出现在雪原之中,竟有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无穷韵味。
我那些远在故乡的函大同学要来丽江教育学院参加函大期终考试,丽江师范的考试结束,我便搬来丽江教育学院,洒扫庭除,等待老同学前来相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和几个老同学从来没有见过下雪,不禁兴冲冲地跑出宿舍,冒着雪花冲到足球场上,把地上渐渐堆积起来的雪,捧起一大捧抛向空中,任她悠悠飘下,沐遍全身。此刻,那些在静谧中的柳枝、翠柏和不远处古老、苍劲而茂密的栗树林,全都静静的,尽情地吮吸着上苍赐予的甜美乳汁。这奇妙迷离的雪花,让我品尝了初春的玉液琼浆,顿觉心胸开阔,迸发出勃勃的青春活力。我想放声高歌,又想低吟几句。雪花渐渐稀疏,苍穹被雪光映照,发出灿烂光辉,好像世界顿时大了许多。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傍晚,抑制不住激情,我三步并作两步,咚、咚、咚地登上教学大楼的顶层。我放目纵观:啊,那绿水依依、鳞次栉比的丽江古城,全都披上了银甲,散落在丽江坝子各处的灯火,像颗颗荧光闪烁的明珠,莽莽雪原和万古长存的玉龙雪山融为一体,仿佛玉龙雪山就是丽江这条巨龙之首,她直飞九霄云天,笑傲苍穹。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抒写了无数江南水乡的秀丽辞章,留下了多少描绘北国风光的华章。此刻,我的目光仿佛穿透了远山的轻云薄雾,看到了蜿蜒曲折,起伏于云天关隘之间的万里长城;看到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茫茫昆仑,看到了大海上风云变幻、波涛汹涌的奇伟而壮观的景象……
这一切仿佛预示丽江灿烂辉煌的未来!
在丽江师范系列中,有中师、幼师、美师、体师,而我们是民师。由于我同时兼读云师大函大,同学们就叫我“杨大学”。起初是华坪的几个女生叫,也数她们叫得最甜。
丽江师范一年一度的元旦运动会和元旦登山运动也在这个多雪的季节举行。
我们登的是象山的北坡。背阴的灌木丛中,还残留着一大窝、一大窝洁白的雪。我们家乡把女儿说成是生了个“锅边旋”;儿子叫“漫山跑”。我从小上山砍柴、放牛、拣菌子长大,是地道的“漫山跑”。登山、长跑是我的强项。我很老实,当我听到哨音起步时,那些躲在灌木丛中偷跑的同学,早已跑到了我的前面,我迅速杀入中路,绕开曲折的山路,径直地窜进灌木丛,甩掉追兵,直逼前锋。过了半山腰,就进入拼耐力、拼实力的决胜阶段了,我放慢几步,进行深呼吸,把丹田之气运往腿部,甩掉几个强手。在看见了山顶高标和红旗的刹那,又有一股新生力量加入体内,我冲到标杆下,领到一张裁判员发给的字条。一看,仅得了第五名。
班主任李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把元旦运动会拿高分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前几天的田径运动会上,我曾向班主任承诺,一定要拿下万米长跑冠军和登山的前三名。万米赛场上,我一路破关斩将,挑战自我生理极限,最终,打败了体师班甲班的体育尖子,不但夺得了冠军,而且还打破了学校的万米长跑记录。成绩为40 分19 秒。我自以为,凭我的实力,登山第一名,非我莫属,可终归是事与愿违。
我班的同学也已陆续到达山顶。
“杨大学,杨大学!”几个华坪女生呼叫着向我走过来,送给我一瓶饮料和一袋糕点,问我拿到第一没有。谈笑间,雷同学悄悄绕到我身后,趁我不提防,一手提起我的T 恤领,一手往我脊背里塞了一团冰凉的东西。

《在希望的田野上》 丽江拉皮古 摄影/张庆华

和品正
和品正,纳西族,1955 年生于云南丽江古城。供职于云南社会科学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参与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散文集《异域之神的乐土》,大型画册《纳西族与东巴文化》,竹笔书法集《纳西东巴经典名句欣赏》《东巴常用字典》《和品正东巴书法艺术》,图文并茂的《云南东巴艺术》等著作。研究之余从事东巴文字画的创作,作品曾到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展览并被国内外收藏家收藏。2004年受华盛顿大学和惠特曼大学的联合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作品展示及学术研讨。O8 年受邀到英国巡展并到北安普顿大学作学术交流。曾先后5 次参加韩国“世界文字书艺大赛”及学术研讨,被聘为“世界文字书艺研究会名誉会长”,并组织丽江书法界参加世界文字书艺大赛,有近50人次入选,30 人次获奖。





木欣荣木雕作品
木欣荣,纳西族,1970 年生于丽江石鼓,木雕及装置艺术家。作品古朴粗犷,天真放达,充满了生命图腾的灵性。2013 年受邀参加第23 届匈牙利光影国际电影音乐节,在艺术节现场创作,作品被组委会收藏。2015 年受邀参加加拿大Sentier Art3 艺术节,在魁北克进行驻地创作及文化交流,作品《经文流淌的红树》被当地媒体喻为“木语者”。

《经文流淌的红树》

《我不是机器人》

《生生不息》
“哦!往死里整啊!”我禁不住惊叫一声。
原来,她早有预谋,把准备好的一个雪球隐藏在身后。我一激灵,那挤碎的雪团凉透身心。当我醒悟过来,挥舞着饮料瓶,要去捉拿她的时候,她早已钻进了人群。
我们站立在象山顶上,一览众山小,只有玉龙雪山,洁白晶莹,鹤立鸡群,高耸云天。大地上的雪早已退去,而玉龙雪山的皑皑白雪万古不化,在那距离北回归线最近的地方,像一个洁白的幽灵永远矗立于滇西北高原的群峰之上,永远铭刻在古往今来游人的心中。
我们为了打发寂寞、放松一下,星期天是很难留在学校的。又是一个星期天,华坪的几个同学,事先买好一大堆菜肴、糕点、饮料之类,便来邀永胜的我和林、敏等与她们一起去郊游、野餐。我们骑自行车,我带芬,林带菊,敏带蓉。再加上些锅碗瓢盆,便一路春风,奔向普济寺。芬搂着我的腰说,今晚教育学院举行舞会,我带来几个音乐带子和录音机,扫扫你的舞盲,改变一下你这个书呆子的观念。
芬是美人胚子,有艺术天赋,翩翩舞姿让人眼花缭乱,从慢三步开始,到八步、十六步,先是示范,后来,又搂着我的腰教我舞。第一次跟女孩跳舞,自然别扭。我这个从不越舞池一步的乡巴佬,扭了一上午也没学到一点皮毛。再令人陶醉的舞会也只好慕而却步。芬十分恼我,多半认为我是一只呆头鹅,不解舞情。我至今深恨自己缺少舞蹈细胞,辜负了多少青春韶华。
归来的路上,少不了照几张疯疯傻傻的照片。就是考试临近的日子,我们也不放过星期天的郊游。晚上,则到教育学院的大厅里去看刚上映而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
有时,也邀林、敏同去黑白水林业局我姨父那儿打秋风。
大炼钢铁铜那年,姨父在县机械厂当工人。七十年代,林业局纷纷成立,姨父就是在这时候,转到了黑白水林业局当钳工的。姨父的钳工技术十分了得,他制作的“剪刀”型抓钩,可以和日本进口的抓钩相媲美。木料一旦被它卡住,轻轻地一抓就抓起来。姨父因此获得林业部的科技发明奖。我们到丽江师范读书的时候,姨父已改行去守油库。姨父守油库,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买了煤油炉等炊具,在学校开了小灶,许多民师班学生用的都是煤炉,烧的是煤球或是劈柴,惟独我们使用的是煤油炉,每星期不炖火腿就炖排骨,想吃新鲜蔬菜,只要到校门外清溪村人家的菜地里去买,摘来的菜,就在清溪边洗干净,回来时锅里的汤已烧好,顺便把菜拧做几截下锅烹煮。菜肴格外鲜美。仿佛我们不是来读书,而是来享受生活,我们成了学生贵族。
消逝的老大门
梁官街赫赫有名的老大门消逝了!
梁官北街第一条向西延伸的巷道,像一把旧时的铜钥匙,先是笔直的通往巷子的里头,往里走仿佛到了巷子尽头,突然右弯左拐,又转出一口老井和几户人家,我家就坐落在这把钥匙弯的左拐处。梁官街唯一有名的巷叫黄家巷口。我们家的这条巷虽然古老,却从来没有名字。这条巷和许多巷子一样都有一座总大门,这道门就叫“老大门”。老大门里起初有五座院落,其中三座是四合院,两座是三进式院落。五座院落就形成了一座堡垒,老大门就锁住了这座堡垒。巷里居住的都是何氏家族人家,我家的子孙流的虽是何家的血脉,却因父亲到杨家立嗣,随祖父姓杨。我们家的老宅不过百年的历史,而这座老大门却要早出许多年代。当年的老大门雕梁画柱,门枋厚重,门槛高有尺许。门枢和门槛安装在两条红色的花岗石石臼与榫口中。门廊高耸,共有三级台阶,一、二级台阶是青石板,最后一级台阶则是由红色花岗岩石条构成。当年何家的马帮就是从这高门大户中进进出出的。
从前,老大门的作用不仅仅用来防盗防匪、防野狼夜间偷袭,水位低于一米的洪水也可挡在大门之外,同时也表现出大门里人家的气派和庄严。逢年过节或是有人家婚嫁,大红喜字楹联往大门两边一贴,更添一番喜庆气氛。白天几个老太太领着她们的孙儿孙女们,坐在大门口的石廊上拉三纲、讲五常,傍晚石廊则是青年男女、婆姨老少纳凉、聊天、唱山歌调子、讲故事的处所。上世纪60 年代,“破四旧”时,梁嘴上雕的龙凤被人斧琢,梁上石青彩绘的山水人物麒麟异兽,也被人用石灰浆涂抹。两扇大门在我记事起就已不知去向。昔日曾经庄严辉煌的老大门,一时间破旧不堪。其后,大门两侧的墙壁上就出现了两条醒目的毛主席语录,白灰的墙,红漆写的字。在那“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时代,老大门也成了“红海洋”的一部分。1982 年秋后,家乡实行联产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生产队时,粪肥、粮草都是社员凭两肩挑出挑进。现在家家户户有了手推车,老大门高高的台阶和门槛,却成了车辆出进的障碍。
1983 年寒假,老大门里人家趁农闲忙着运输沙子、公分石,买石灰,筑院子的地平,以便用做收打蚕豆、晾晒谷物的晒场。材料运到大门外再挑回家,或者在台阶与门槛两边填许多砂土筑成高坡,车子虽然可以暂时出进,可是,事后又要清除填路的砂土,十分费力费工。起先动工筑场的人家吃尽了苦头,后来有几家想要动工筑场的,商量要拆除老大门的台阶、锯掉门槛,可谁也不愿出头露面得罪人。
仔细想来,要锯掉门槛的确涌上心头许多滋味。老大门是大门内十几户人家家声和文明的标志。近些年来,大门里人家人丁兴旺,儿孙们上过大学的不下二十几人,在大专院校任教的六人,其中攻读研究生的就有三人。何康林出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赞。我们家两个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我七个人都是大专学历。不说老一辈费尽心思盖了大门,造福于后代子孙。就说自己从小长大,在这大门下纳凉、避雨,在台阶上坐卧玩耍;在石板上刻各种棋盘,和小伙伴下棋;在门前门后,丢铜钱窝,打链排,格鞋牌,跳龙门,跳观音,斗陀螺,听山歌,听故事……成长过程中的桩桩件件都无不与之相联系。
要是何老太公还在,这门槛是断然不敢锯的,记得小时侯我的玩伴无意间说了句脏话,不知从什么地方走出来的何老太公颤巍巍怒目圆睁,抽出插在身后的那枝长数尺的金竹烟杆,猛然敲在了他的脑门上,登时起了个包,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哪家的父母也不敢出来护自家的犊子。
这回没的商量,这件事必须是先斩后奏。何况何老太公早已不在人世。1 月31 日下午,我趁血气之勇,找了一把锯子,把百年的老大门的门槛给锯了。锯门槛的时候,一个叔伯兄弟看着我锯,叫他帮忙,他说,还是你锯算了,我不敢跟你锯,怕有人找我的麻烦。我知道他家庭成分不好,他刚从阶级斗争的阴影中走出来,老大门门槛他的确是不敢锯的。晚饭后,我决定去瓦窑上要些瓦片来,准备筑我家的院坝地坪时用。
刚出门,老远就听孟廷叔怒气冲天在质问:哪个吃了老虎豹子胆的竟敢锯了老大门的门槛?把他叫出来。
旭明叔说,是海清锯的。
你把他叫出来,我问他。
还在老远,孟廷叔就恶狠狠地怒喝。我装作毫不在乎地来到大门前。大门前已聚满了人。谁叫你来锯门槛的?他气呼呼地问,你有什么权利,你姓何,还是姓杨?这是何氏家族的老大门,要锯也用不着你来锯。你同谁商量的?你说锯得对不对?
锯得对不对,请大家评。我说,达廷叔你们兄弟俩和何爷爷,你们这几位长辈都反对锯门槛,同谁商量呢?一商量就锯不成。
荷玉姐和其他几个年轻人都站出来支持我,荷玉姐家也正准备筑院坝,巴不得有人锯了门槛拆了大门台阶。孟廷叔见众人都支持我,便要我请出十几户人家的代表来评理。又推又搡,说要找我母亲说理。在众人的劝解下,我走开去了瓦窑。不料他还气有不平,他召集了达廷叔、何爷爷和其他十几户人家的家长等候在我家老宅的堂屋里准备向我发难。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家里早已吵作一团,见我进门,孟廷叔连板凳也不坐了,呼地站了起来,想给我个下马威。照样对我来了一通指手画脚的训斥。
孟廷叔,其爷和各位长辈,对不起,今天下午,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锯了门槛,我错了。等他消了气,我说,其实锯了老大门的门槛,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我家祖辈生活在老大门里,我的衣胞也和老大门血水相连。其爷,你曾经是区党委书记,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你说说,这老大门里人家除了孟廷叔一家都是吃皇粮的外,包括你们家哪家不是盘田种地的,大门不加改造,已经严重影响大家的生产生活。都分田到户了,转眼又是春耕夏收的季节,家家准备筑院坝,运秧田肥,夏粮入库缴公粮卖余粮。我们家也还有4 亩多田地。我在外读书,也是趁寒假回来做这些事。门槛也锯了,再无装上的必要了,也趁大家都在,还是商量一下如何改造吧。
大门多年失修,房顶上荒草丛生,破旧不堪,需要翻修。有人立刻把话题转移到如何改造大门上来。孟廷叔见众人一词,就立即逼问,海清,你打算怎么改造?
椽子该换的要换,瓦也要添,台阶拆除后,除了安装几块大石板在大门两边供人们休闲时坐坐,其余的都铺成弹石路面。我带头捐两元钱,在坐的各位愿意捐钱、捐物、出力的随便。
接着就有十多家各自捐了一元钱。其爷站起身想走,兰眼尖,叫了一声:其爷,你一个堂堂的党委书记,论退休工资比谁都高,你也捐上一元钱吧。
乖猴,管闲事,又少了爷一斤酒钱!其爷骂一声,十分不情愿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元钱,摔在我手中扬长而去。
几年前,我们一家举家迁往省城居住。重修大门到现在,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老家时,家乡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许多人家的大门都是砖混结构,盖以琉璃瓦,贴以“福、禄、寿、喜”之类的风俗瓷砖画,铁大门一开,卡车或各种农用车辆开出开进,畅通无阻;许多巷道都已筑成水泥路面。而老大门里巷子依旧是土路,雨水天泥泞路滑,冬、春两季则灰尘四起。老大门是梁官街上的第一巷,却与梁官街整洁的街道极不协调。我曾多次出面与大家商谈集资筑水泥巷道的事,都由于人心不齐而作罢。至今,老大门依旧是二十几年前改造过的样子,经过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甚至变得更加衰败与苍老,变得越来越仄,除了手推车、摩托车能够出入外,一般的农用车辆就难以通行。大门之上的瓦壕沟里,有几棵衰草在寒风料峭中瑟瑟颤抖。老大门真的老了!何老太公早已作古,其爷、达廷叔、孟廷叔兄弟也相继离世,再也听不到他们呵护晚辈们的声音了。他们为了维护老大门的尊严,为了守护何氏家族的利益挺身而出的无畏精神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原来住着的十几户人家,十有六七都搬去新村或因其他原因迁往城市居住了。
2013 年,母亲在老宅溘然仙逝,享年91 岁。老宅拍卖了。从祖父那一代到我们的子孙,五世居住过的老宅就这样成为了异族的居所。那是我的衣胞之地啊,多少无奈,多少记忆,多少坎坷与磨难,多少眼泪和辛酸,多少汗水与沧桑,祖宗的根永远留在了深深的小巷。人世沧桑,心里不免生出些悲凉与感伤。
2014 年8 月,我因出差,再次回到久别的故乡,老大门两边的人家修建了洋楼,老大门也早已坍塌并被拆除,只有两个做门臼的红色花岗石还遗弃在原大门的旁边,原来大门两边人家的土墙也变成了高有丈许的砖墙,至此,老大门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