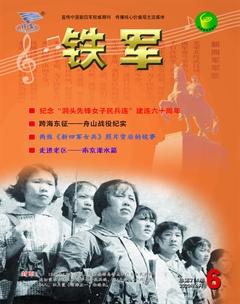界碑无言
姚定范
张耀淇是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军队保卫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是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干事,小老虎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同学圈里,很少有人喊他的大名,而小老虎却是响当当的。用东北人的话说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说起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外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是全国公安战线的最高学府,可这地方的大学里怎么会有一个军队的系呢?其实这很简单,我党是先创建了军队,再创立了新中国,这军队的保卫工作就是国家公安工作的根,公安工作的历史是从井冈山红军时期的锄奸团开始写起的。公安大学建校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决定给军队留一个系,当时叫五部,后来逐渐规范为军队保卫系,简称军保系。我和张耀淇是1993年3月入校,参加为期三个月军队保卫处科长培训班。这个培训班和地方县市一级的公安局长岗前培训班同步,分开编班,统一授课。毕业后没有多久,小老虎就去了中俄边境的密山边防某团任政治处主任。我当时并不知道密山在哪里,他在电话里说,你听说过兴凯湖吗,查一下地图就知道了。
后来他告诉我,兴凯湖在唐代时叫湄涂湖,金代改称北琴湖,到了清代才叫兴凯湖。她原本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直到1861年中俄勘界一分两半,成了中俄的界湖,湖的一半包括湖东的一大片领土被沙俄抢占了。就现在这半个湖,也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其面积仅次于青海湖,相当于78个西湖、10个梁山泊、2个太湖。站在兴凯湖边,游人看到的是碧绿的湖水,呼吸到的是甜甜的空气,品尝的是美味湖鲜。可只要稍懂一点近代史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军人、中国边防军人,站在这里举目一望,就会有一种令人窒息的不爽扑面而来,这么好的一个大湖,明明是我们的,咋就一夜之间只剩下一半了呢?
2015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俩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相遇,铁锅炖大鹅热气腾腾的,几杯东北小烧下肚,两个早已脱下军装的哥们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老哥,边防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你不在边防线上走上几年,那是绝对感受不出来的。身后是祖国,面前是界碑,边防无小事啊!我在密山边防团干了两年,铁丝网那边的人可不省心了。“一支枪惊动了党中央,一条路捅到了外交部”,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每次到前沿巡逻,到了界碑总要停下来,就算一点事没有,都要上去摸一摸,四周转一转,反复打量,多看几眼才觉得心里踏实。这几千里中俄边境线上的每一块界碑,联想起来,哪一块都有令人扼腕的心酸故事。
他猛喝一口酒,繼续说界碑的故事:
我们防区的一块界碑,原本应该立在山顶的山脊线上,因为这是国际惯例啊,后来不知咋的却到了山下,这里就有一个无法启齿的真实故事。据说,当年清政府和对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好不容易把对方的一大堆蛮横无理的要求给顶了回去,勘边定界,约定某年某月某时设立界碑界桩。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对方自然非常重视。到了设立界桩之日,他们出动整队的军人,荷枪实弹,四驾马车,浩浩荡荡开到山上,挖坑立桩,拍照留影,然后欢呼而去。我们呢,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由于严寒和疲劳卧床不起,无法理事,弥留之际把几个他认为比较信得过的地方官叫到床前,叮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并把身上所有的银两全部交给了所托付的人。谁知,这事却一下成了这几个地方官的肥差,他们先把银两扣下一半,几个人分入囊中。然后装模作样,任务逐级下派,银两层层克扣,立碑的事情最后落到了两个大字不识的农民身上,说把这块石头抬到山顶埋好,每人赏银子一两。两个农民很高兴,抬着界碑往山上爬,越往上爬越累,抬着抬着两人就抬不动了,便开始合计:“这破玩意死沉死沉的,有啥用啊,干嘛非得抬到山顶上,在这里不行啊?”“有啥不行的,我看这里就挺好!”于是乎,两人把界碑往路边一撂,其中一个人一脚将界碑踹下山沟,下山领了银两回家喝酒去了。
过了几年,双方根据约定对边界进行复勘。对方的界桩纹丝不动立在山顶,我们的界碑呢,踪迹全无。咋整啊?一级一级兴师问罪,找呗!这哪用找呢,把两个当年的农民抓来一审就明白了,我们的界碑静静地躺在山沟的荒草丛中。对方一看哈哈大笑说:“尊敬的阁下,实在不好意思了,这是你们自己把界碑定在这里的,那这里就是你们认定的边界。我们对此表示尊重,我们国家的界桩今天必须移到这里来!”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哑口无言,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边界又向我方推进了几公里,并且不费一枪一弹。耻辱啊!据说,事后这两个农民被斩首,几个官员也都革职查办,但失去的领土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彼此约定,等退休之后要专门到中俄边界的每一个哨所走一趟,把每一块界碑的故事都写出来。 (本栏目责任编辑 徐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