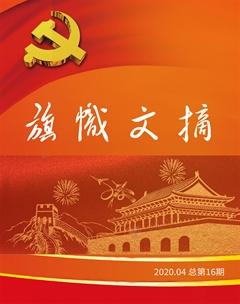“诗”“人”一体,文质相砥(评论)
在我看来,中国当下的诗人很多是诗歌和人格是不一致的,甚至往往是分裂的、反差的、龃龉的、矛盾的。中国诗学传统一直对诗人的人格、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有着特殊的要求,真正的像李白和杜甫那样的诗人是知行合一、诗和人一体。在他们那里,人格和文格是彼此共生、相互磨砺的。那么,看看当下中国诗坛,很多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极其功利、猥琐,甚至有了自媒体之后变得野心勃勃、一己膨脹,反倒是在诗歌中充当了斗士、公知、圣女、独立者、品性高洁者等形象。言行不一、名实不符、诗和人分治已经成为显豁的事实。历史上不乏人格卑劣者写出好诗文好书法的个案,但是从文学史和“诗人中的诗人”来考量,我们需要的则是诗和人一体的写作者,他们呈现出的是复杂、开阔且具有穿越时空的持续的精神膂力和思想能量,他们面向的既是自己的时代又是未来的读者。而我要谈论的商震,就属于诗和人一体的代表,观其人如观其文,反之亦然。
每次外出,商震大步迈出机场的第一件事就是狠狠地甚是极其惬意地吸几口烟。烟雾喷涌缭绕中若有所思,他瘦削的脸也暂时笼罩在了一团烟雾之中。他更愿意或宿命性地站在时间的逆光处,进而拨开虚假的光以及附着其上的颂词,对尘世暗影、乖张命运、内心渊薮进行不留半点情面地挖掘与自审式的探问与盘诘。在我看来,商震属于愈久弥坚、愈发老到、通透的写作者,冷峻、理性又不乏感性和幽默。这既涉及他的思想厚度、人生阅历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时与关乎他的语言及物性表达方式和想象能力、修辞精神。从诗歌人格和精神力度来说,商震更像一团冬日里的火焰,也像酷夏里的一块寒冰。他的诗歌一直在人性层面是温暖盈怀的,而对于黑暗和恶他几乎从来不留余地,从而像极了干瘦而尖锐的钉子。他是生活现场的观察者、摩擦者、勘测者,同时也是旁观者和审慎者,这种既介入又疏离的方式使得他的诗歌空间越来越开阔,他总是能够在日常事物那里找到亮点和缝隙,总是能够通过表层进入事物和世界的内核从而一探究竟。诗人是好奇者,但是不止于好奇,而是达成创造和发现。这些品质在他最近的组诗《相遇》以及前一段的诗集《谁是王二》中有着鲜明地体现。值得强调的是商震诗歌中的叙事成分以及戏剧化的效果值得关注,而通过“王二”这一中心人物和核心形象所贯穿起来的个人史、生活史、时代史、心态史则开创了当代诗歌崭新的写作方法。
冷热交替,世事无常,人何以堪!也许只有诗歌能够成为个人的记忆和时代的作证,也是对个体内心的慰藉。平心而论,商震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具有“风骨”的诗人,尽管他自谦地指认自己只是一个资深编辑。当年的诗人嗜好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浑身散发的“风骨”也免不了病态。商震又是具有“血性”和强度的诗人,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精神委顿、犬儒盛行、蝇营狗苟的时代商震这样的不隐恶、不自我美化的“敢说”“直说”诗人并不是太多。
“半张脸”是商震的精神自况,也可以视为他诗歌人格的代表性文本。那么,他的“半张脸”所揭开的是怎样的诗歌性格呢?甚至这样的诗为什么会遭到一些人的不满和抗议呢?
一个朋友给我照相 /只有半张脸 /另半张隐在一堵墙的后面 /起初我认为他相机的镜头只有一半 /或者他只睁开半只眼睛 /后来才知道 /他只看清了我一半 //从此我开始使用这半张脸 /在办公室半张脸藏心底下 /读历史半张脸挂房梁上 /看当下事半张脸塞裤裆里 /喝酒说大话半张脸晒干了碾成粉末撒空气中 /谈爱论恨半张脸埋坟墓里 /半张脸照镜子 /半张脸坐马桶上 //就用半张脸 /已经给足这个世界的面子
我想到一个情景。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临街的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式建筑里,商震着一身黑衣。屋里不禁烟,他半端着烟斗踱步。正午的阳光投进屋内,他身体和脸的一半在灿烂耀眼的光线里,另一半则在斑驳不明的暗影处。这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他的“半张脸”的深意了——温暖的、灿烂的一半留给朋友和这个世界同样诗意光明之物,而寒冷、严峻、刚硬、傲骨的另一半则冷对人世的暗疾、人性的丑恶和浮生的腌臜,将钉子扔给那些放暗箭的恶人、长戚戚的小人和伪君子——。正如商震自己所言——“我快乐的一部分来自对泼皮的嘲笑”。商震为人与作诗是一体的,真正的文如其人。而多年浸淫诗坛,我却看到那么多心口不一、人诗分裂的“写分行文字的人”——从人格和品性的角度看他们根本配不上“诗人”这个称号。
商震看得透彻,心知肚明嘴上还不饶人,无论多熟的人他抽冷子冒出来的话也能让你浑身一哆嗦或如芒在背。他曾经以大奸臣严嵩为例说过“好诗人不等于生活中的好人”。是的,一个十足的坏蛋也能写出几句好诗(实际上在历时性的诗歌谱系那里考量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这样的“好诗”“好诗人”我是不屑于谈论的。那些打肿脸充胖子、一嘴仁义道德满脸横肉一肚子男盗女娼甚至不惜用“崇高”、“正义”、“纯洁”装扮起来的伪诗人、坏诗人、假大空的诗人我们见的还少吗?自媒体时代任意踢破写作门槛的人我们更是司空见惯。自媒体带来的写作幻觉和虚荣心让写分行文字的人(在我看来“诗人”这一称谓是要设立高度和门槛的)纷纷如过江之鲫,秋风中的一片落叶足以覆盖这些短暂的渣滓与轻浮之物。动不动就是“著名诗人”、“国际诗人”,实际上都是令人恶心的土鳖和灵魂嗑药者。商震在《三余堂散记》中以“建安文学”为切口谈到过自己最瞧不起的就是人品和文品不一的人,尤其不能丢文人的脸。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
商震是敢于自我压榨、自我暴露和自我清洗的诗人。他的诗是“成人之诗”,知性、深沉、冷彻、刺骨,他的诗中有成吨的寒气让一些人浑身惊悸,他又会拉着那些受伤的人走向远处的炉火。但是他又时时以另一种“童真”来予以诗人自身的完善——情绪、热烈、燃烧。这一冷一热产生的是真实的诗——真人、真诗、真性情。进一步说,这不是一个自我美化、自我伪饰、自我高蹈、自我加冕的诗人。商震的诗歌里有硬骨头,有鱼刺,这会令一些人如鲠在喉。他这种棱角分明、爱憎立现、直言不讳的性格也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这是必然的,要不小人何以常戚戚。商震诗歌里不断有雨水、冰雹、沙土和大雪在黑夜中落下。他会耐心地烤干淋湿的衣角,翻检墙角里被瞬间击落的树叶、花瓣和往昔陈梦与过往碎片。显然,这是时间给生命体带来的冲洗。如果不时时清洗那日益劳损的沾满人世灰尘的皮囊该如何接纳灵魂的跳动?可贵的是商震在诗歌中不只是“自我清洗”——那样的话诗歌的“精神洁癖”就会导致诗歌的窄化和道德化——而是敢于自我去魅。这谈何容易!但是,商震做到了。
商震敢于揭开自己耿耿的隐情,敢于戳破人情世故一张纸,他也无奈地擂击世俗的厚厚“墙壁”。他敢于不留情面地撕下自己和他人的面具,他也敢于摘下神的面具甚至敢于撕下魔鬼的面具——这是一个与魔鬼下棋的人。这就是商震——有敬有畏,敢爱敢恨。他能忍如履薄冰,也可襟怀入火。他敢于自剖示人,也敢于刺人。他有时又情难自抑制,几把滚烫的老泪偶尔滴在朋友身上、滴在亲人怀里、滴在遥远的东北故乡、滴在曾经青春年少的梦里、滴在落了灰尘的爱情信纸上。实际上,商震的诗行里一直横亘着一把钢口绝好的剑,还有冷硬邦邦的结霜的胫骨。有时候你可能会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但是它们又时不时地以冷飕飕的气息提醒你要小心、要自知。他甚至有时候像一个未曾长大的孩子来点恶作剧(比如绘声绘色地编造我的子虚乌有故事,因为他高超的语言能力往往让人百口莫辩且由他信口说去),站在高坡上抖落满怀的坚果,让你惊喜也让你哭笑不得、不知所措。几次深夜,喧嚣的城市止息了,我们一起喝酒喝到眩晕,谈诗谈到嘴麻。我对一个活动如此众多、评奖如此频繁(自己也不免卷入其中)的时代能够倾心谈诗的人认作终生的朋友。甚至在那些亡故的诗友前辈(如韩作荣、王燕生)和同行兄弟朋友(如陈超)那里,他滚烫的文字会让你浑身灼热燃烧起来,也会在凄苦中抖落漫天雪阵。我记得陈超先生猝然离世,他陪着我到石家庄,在深夜的宾馆里呆坐苦熬。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烟蒂连烟灰缸都盛不下了,而我则一次次翻身一次次叹息。他连夜将自己的感情投放进了纪念文字里——有血,有泪,有劝慰有悲戚。
商震的一部分诗不避曲直、不隐内情、直来直去,甚至不留半点余地。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不懂得诗歌之“隐秀”,不懂得“少即是多”,不懂得呈现和表现的平衡。正如商震自己所透析的那样,“波中有伏,直中有曲”,而是证明有些时候诗人的声音是必然来自直接碰撞。实际上商震的诗歌并不缺乏转换和化用的能力,化大为小、化小为大他都能够驾轻就熟,甚至非常老辣,比如《一棵死去的大树》《看萤火虫》《相遇》《这天中午》《梅雨》《酷暑》《微信好友》《假寐的大海》《白衬衫》等。商震属于到老成精的那拨人,越老活的越自在透彻,越老诗歌写得越有道道,或清冷峭拔或讥诮戏谑地面对自我与俗世。
佛家语“道成肉身”,而到了商震这里则是“诗成肉身”。尤其到了一定年龄,身体状况会直接影响诗歌的“体格”。近年来商震不大喝酒了,因为胃部和肠道都受不了刺激了——他诗歌中的“火气”渐渐小了,或者这种“火气”转换成了另外的方式。但有时候在一些场合他又不能不喝酒,我当众说商震的胃做了手术不能喝酒,可他有时候不听话仍端起杯子一饮而尽。酒后身体会反抗他,他也知道难以消受。但有时候,深夜里年轻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登门造访,除了喝茶自然是喝酒。有一次在北京山区,他深夜拉着我去吃面,结果是喝酒,他瞪着小眼睛看我把一满杯白酒灌下去才满意。而 2015年 6月在台湾花莲,那个偌大的校园里没有卖酒的,只能步行到校外的小镇上。那天夜里商震想喝点酒,我手机正充电,就独自一人走在夜色里去买酒——校园太大了,岔路又太多,路上的丛林里有不知名的动物在叫,路上有很多巨大的蜗牛穿越马路。来去竟然花费了我一个小时。商震联系不上我,还以为我被校园里的什么豺狼虎豹叼去了,就让王单单四处找我。在商震的一部分诗歌中不断出现的是那些疼痛的、弯曲的、变形的“身体”“躯体”“皮囊”“肉身”“肉体”。有时候商震更直接干脆,在他看来身体实际上就是“一堆肉”“纯粹的肉”“纸糊的躯壳”,是“包子皮”和“肉馅”、是“脱水的竹竿”、是一把渐渐破烂的椅子、是“冬眠的枝干”。诗人敢于把自己置放于时间无情的砧板之上,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哉。这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而是需要才胆识力的综合素质。商震不仅还原了身体经验,而且参透了时间和生存的隐秘内核——不为表象的漩涡所动,而是以机心直取核心。在身体中感受宿命,在物化中确认自我,在自我中发现世界。这就是诗人要做的事儿——诗歌是身体感知的延伸与对应。而现在很多的诗人都不会说“人话”——往往是借尸还魂说“鬼话”,拉虎皮扯大旗说“昏话”。借尸还魂,即利用贩卖来的西方资源的翻译体或借助表皮的地方性知识装神扮鬼蒙人,拉虎皮扯大旗就是空泛无着的宏大乌托邦自我美化、自我圣洁。
商震很多诗歌具有“日常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甚至由于工作的原因还写了不少游历诗来点怀古的情调和那么一点忧愤。看看当下很多的诗人都在地理的快速移动中写旅游诗和拙劣的怀古诗。高速时代的诗人生活不仅与古代诗人的流放、游历、行走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就诗歌的历史对话性而言也往往是虚妄徒劳的。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对现代性予以了“风景的发现”,而商震也在努力发现属于自我、属于这个时代又超越这个时代的“风景”。商震在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真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和面对纷繁的当下,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还乡”“栖居”“诗意”“乡愁”成了城市化时代被写作者用烂的词语,但是对于商震而言,“还乡”却是来自于骨髓的,是“一滴酸楚的泪”苦熬成盐的过程,“再向前十几米 /就汇入渤海/辽河将走到尽头 /河水也要改名换姓 //河水前呼后拥的奔向海 /而河里的星星只搖晃 /却不随波而动 /这些河水啊 /在河里嫌滋味太淡 /进入海里就该知道 /什么是苦咸 //有一滴河水故意撞向石头 /勇敢地跳上了河岸 /尽管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它留在了 /辽河流域的土地上 /就是留在了故乡”(《辽河入海口》)。这既是地理变迁和家族血脉使然,又是人性本我的精神还乡。他的诗歌里会反复出现无声的冷月、凛凛的白雪,而且设置的时间背景不管是出自巧合还是出自于诗人的有意安排,大多都是黑夜。这样,黑夜、冷月、白雪和“埋伏着暗火的炭”之间的对话就发生了,而且这种发声简直就是杯盘与杯盘之间的惨烈碰撞与炸裂般的碎响。
如果你早年见到过铁匠铺,你懂得一把烧得通红的铁器伸进冷水那一瞬间意味着什么。明灭有时,人生如此。活得明白不等于诗歌就写明白了。如果都懂了,就成了商震这样的人。商震在朋友面前从来不说假话,有一说一。而商震对朋友要求也非常严格,他经常当众“敲打”我、批评我——这是真正对我好的人。记得今年春天在希腊,满街都是橘子树。导游小伙说这些橘子树是杂交品种而且打了农药是不能吃的。而几次看到风中摇晃的金黄黄的迷人的橘子我都想摘下来,商老头立即正色道:“不能摘!不能吃!”
多年来他一直站在阳光与暗影深处,慈爱有时,严厉有时。他的诗与人一体,他提供给我们以及这个时代的是真实不虚的生活记、灵魂史和思想志。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着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十余部,曾获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2018)、《诗刊》2017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四届“后天”双年奖批评奖(2011-2012)、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2018)、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诗学奖(2017-2018)、首届金沙诗歌奖·年度诗评奖(2018)、首届扬子江诗学奖(2013)、扬子江双年奖、首届《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2013)、《星星》年度批评家(2013)等。
本栏责任编辑 胡兴尚
(本文选自:滇池 202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