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负和希望

不知是誰把“acacia”率先翻译成“金合欢树”—它的希腊语词源“?κ?”大约意为“棘刺”—无论怎样,汉语“金合欢树”用在《到婚礼去》(To the Wedding)一书里可谓水乳交融。小说中已经失明的叙述者说道:“一只鸫鸟在金合欢树上唱了起来。鸟鸣,比任何一切都更令我想起万物从前的模样。”被古埃及人和犹太人不约而同奉为圣木的金合欢树,高高擎起华盖般的树冠,带刺的枝条向四方伸展,叶呈羽状,开出满树黄澄澄的形如阳光迸射的花球,甜香袅袅。埃及人用金合欢木打造家具、船只、棺材。埃及神话里,冥王俄西里斯(Osiris)和他妻子伊西斯(Isis)的故事都出现过金合欢树—伊西斯曾化身为鸟儿托庇于金合欢树梢头(小说中安全抵达的鸫鸟,则“像幸存者一样歌唱”),而俄西里斯被谋杀后棺材漂流到河边,金合欢树便神奇地用枝柯合围住他的遗体。伊西斯施魔法使丈夫复活。金合欢树从此与生、死、再生难解难分。

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
约翰·伯杰(John Berger,又译约翰·伯格)在他发表于一九九五年的中篇小说《到婚礼去》里五次提到金合欢树,寓意深远。小说梗概说来简单:分隔两地多年的父亲和母亲,同时穿越整个欧洲前往女儿的婚礼。美丽又活泼的妮农爱上了意大利青年吉诺。她二十四岁,将死于艾滋病。
妮农跟她将来的丈夫邂逅于一场埃及文物展,当时尚不知自己感染了病毒。展品有一具金合欢木棺材,上面绘着“情人之神,吻你到海枯石烂”的字样。情人之神应该是指女神伊西斯,她两次复活了遇害的丈夫俄西里斯;然而,这小说里令情人重生者当然是吉诺,不是妮农。事实上,正是由于从巨大心碎中重燃并升腾的希望,小说跳出了一般艾滋病文学走向低沉的叙事曲线。而约翰·伯杰极深厚的人文主义悲悯精神,又在整部小说中—尤其是占全书六分之一的婚礼当天场景里—给饱受痛苦的一家人灌注以人类亘古不灭的欢乐和希望。《到婚礼去》是一部希望之书。
故事假托为一个希腊人的讲述,他叫佐巴纳科斯,是个在雅典集市上摆摊的盲人,出售一种东正教常见的祈愿牌“塔玛”(tama),可佩在胸口,也可以挂在教堂圣坛前。每片塔玛“凸印着一块图案,是处于险境的身体部位”,可能是手臂、腿、肚子、心脏、眼睛等,寓意祛除灾祸、康复身体。小说开头,有个外国观光客来到佐巴纳科斯的摊位,从盲摊贩手上买了个便宜的锡制心脏塔玛,他说,塔玛要送给自己“哪儿都受苦”的女儿妮农。少顷,妮农自己也走来,向爸爸炫耀她新买的二手皮凉鞋。言谈间,妮农不经意提起自己的婚礼,被好奇的佐巴纳科斯留心记住了。与父女俩的一面之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种种触机都令他想起他们。几个礼拜后,佐巴纳科斯在朋友的酒馆听见希腊蓝贝蒂卡(rembetika)民谣—一种直抒胸臆的悲伤曲调,在周围起重机卸货的嘈杂中,耳边仿佛有一个嗓音响了起来,他认出是那个外国人—铁道工尚·菲列罗—在电话上跟人谈着即将来临的女儿的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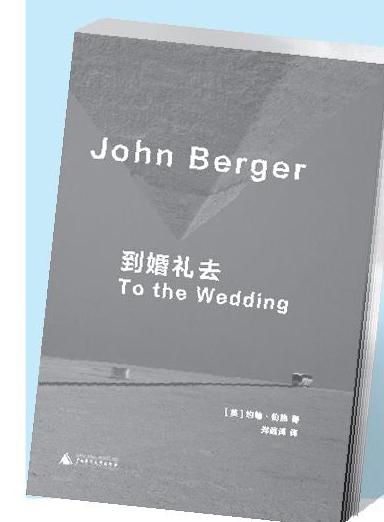
《到婚礼去》[ 英 ] 约翰·伯格著郑远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身为盲人叙述者,佐巴纳科斯以分外敏锐的听觉接入妮农的故事,随着小说发展,他渐次听到了妮农的爸爸尚·菲列罗、妈妈泽德娜、妮农自己、妮农的男友吉诺、吉诺的爸爸费德里科,乃至其他一些或有名字或不明身份的角色的内心独白,各人的嗓音汇集为一个多声部叙述。佐巴纳科斯这希腊人仿佛拥有灵视(visionary)能力,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他的祖先—相传亦为瞽者的荷马,甚至联想到忒瑞西阿斯(Tiresias,希腊忒拜城的盲先知,正是他警告过俄狄浦斯王不要穷究身世)。不过,佐巴纳科斯毕竟是个二十世纪末的现代人,千里之外的各人心声情态,他又如何听闻洞察呢?伯杰的写法暗示一切都来源于佐巴纳科斯的想象,屡次提醒读者,是由于“嗓音、声响、气味”这些触媒在佐巴纳科斯脑海中的作用,故事才被幻想塑造成形。以批评术语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结构。但是,高明的作家当然不会一味拆房子:佐巴纳科斯-伯杰的讲述勾起读者最鲜活的感官印象,我们都会一厢情愿地选择忘掉元叙事的机杼,为主角的命运牵动心弦。
叙述者佐巴纳科斯旁征博引,恐怕有读者会怀疑一个集市摊贩何能至此。这本来不算漏洞,但伯杰还是调皮地给读者打了一支预防针。佐巴纳科斯声称:“我失明以前干什么,我不打算对你说。如果你猜上三回,保准三回都错。”只要盲人叙述者的出身背景模糊不清,我们对他堪比约翰·伯杰的博学就无法挑刺了。伯杰在小说中的分身是佐巴纳科斯,但分身不止一个,其余两个稍后再谈。
在欧美,艾滋病题材涌现过许多作品,但高峰主要出现在正当危难之时,确切地说,是鸡尾酒疗法被发明并有效控制病毒载量之前。百老汇名剧《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首演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彼时艾滋病仍是世纪绝症,无数患者身陷地狱般的苦难;在欧美一些大都市中,病魔夺走的是整整一代精英。《到婚礼去》属于这一波文学作品,作者将英美两版的版税全部捐给艾滋病关怀组织。伯杰回忆, 当时他有朋友患艾滋病去世,这对于他“并不是那么遥远的事”。小说写到一半,他儿子雅各布的西班牙妻子确诊感染,消息令他一度考虑搁笔,后来决定往下写,一边从旁照料儿媳;书才出版,儿媳即与世长辞。尽管我们不必求证家庭悲剧对一部小说的影响(艺术品的价值跟它是否基于真事无关),却不难发现妮农的爸爸—铁道工尚·菲列罗,是约翰·伯杰的第二个分身。作者和人物都是移民后代、摩托车手,都倾向社会主义,并且同名(英文中的“John”相当于法文中的“Jean”)。

舞台剧《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剧照
尚·菲列罗要从法国小城家中前往意大利出席女儿的婚礼。出发前夜,他骑上摩托车仰望天空,没有星星。这里伯杰写下一个名词结构的独立句:“幽暗,一种依稀可见的幽暗。”(Blackness, a visible blackness.)“依稀可见”是车手对道路能见度的判断,但可能也暗用了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六十三行的典故—撒旦被全能的神摔下地狱烈火深渊之后看见的景象是“a darkness visible”,两者语句相当接近—人类失去乐园后坠入的幽暗,体现在尚·菲列罗身上,是他对女儿生命前景的黯淡心情。“摩托车亮着前灯蜿蜒曲折地开上山去。车子时不时会消失在悬崖和岩石后面,一路不断爬坡,越变越小。现在它的灯光忽明忽暗,像茫茫石壁前一支祈愿燭的火焰。”途中他曾在山路边停车,用山泉的冰水止住眼泪;又曾向道路旁神龛中的圣母玛利亚祈祷,求问她:如何将一无所有变为一切?这个叙事片断戛然终止于此问,余音袅袅。如同朱天文《巫言》第一句“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一般,故事将解答宕后。
德国的英语文学教授拉尔夫·赫特尔(Ralf Hertel)写过一篇精彩的论文《文本中的耳朵》(附录于《到婚礼去》中译本)来阐述这部小说倚重文字听感的叙事风格。听觉与视觉互不抵触,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共同唤起读者最强烈的想象。倘若认为《到婚礼去》带有几分古老的、说书般的质感,我们同样可以将它视为一部常以嗓音或声响先导画面的前卫叙事电影。画家出身的伯杰,写作生涯里确有电影编剧的一页,而且成就斐然。这小说中有些蒙太奇平行剪辑般的穿插叙述,最像是电影剧本的处理。伯杰说过书名的关键在于介词“to”;他显然借鉴了公路电影的结构来组织素材,用现在时态叙述的旅程作为小说主体,在叙述中不断闪回前事。文字的可视性与动感无懈可击,比如一句“最初的雨点落了下来。开始很稀疏,每一个都是水做的莓子,一撞上柏油路面就爆炸,微小的水籽散落各方”。故事里的风物都可以说是写实,但同时,许多描写又分明从数千年的西方文学传统中借来了神秘主义的象征力量,比如苹果树及其果实(性爱象征)、浓密的头发(孕育力和性感象征)、明暗或日夜、罂粟花(象征睡眠、宁静的死、遗忘;“一战”以来象征战场牺牲的士兵)、倒置的金字塔(象征永恒,又因其倒置暗示沙漏流沙般的时间短暂)等较为隐栝的象征,又比如山、道路、太阳、雨、河、海、风、指环、羊羔、星星、婚礼等意义趋于普世化的象征,遍布全书,不胜枚举,文本整体仿佛一个象征的森林。除了本文开头谈到的金合欢树的神话原型,书中还有另一个植物象征,与金合欢树的重要性不分轩轾,相互间构成某种匀称。它是柳树。荷马史诗《奥德赛》第十卷中,用巫术和魅力使奥德修斯羁留一年的神女基尔克(Circe)告诫这位英雄,返乡前,他要带着人马首先航船去一趟冥府,会见忒拜的盲预言者忒瑞西阿斯的魂灵。依据神女的描述,冥府外缘的海岸上有冥后“佩尔塞福涅(Persephone)的圣林,/有高大的白杨和毁坏果实的柳树”(第509-510行)。希腊文的字面“毁坏果实”是个费解的形容,王焕生灵活译为“果实随絮飘逸”。古人可能误以为柳树不结果,无论如何,身姿低垂的柳树后来成了西洋文学里的一种象征,与少女无子夭亡的命运相系。莎翁笔下有两个这样的少女:《哈姆雷特》里,奥菲利亚欲攀柳树悬挂花环,却随着断柳落水身亡;《奥赛罗》的苔丝狄蒙娜临死则唱了一首柳树歌。然而《到婚礼去》中的柳树不仅象征少女夭折,而且更强烈地关联着希腊神话中歌手俄耳甫斯只身进入幽暗冥府,解救妻子欧律狄刻的传说。拉尔夫·赫特尔文中有详尽分析,在此不赘。

《奥德赛》[ 古希腊 ] 荷马著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给一本首要诉诸感官的小说编写文学索隐大全毫不聪明,伯杰毕竟不是T. S. 艾略特。但我的初衷只在于试图指出他这小说的文学纵深,给予读者更多的欣赏角度。如果要举出仅仅一种象征物来作为理解小说的关键符码,那必然是鸟雀,它最基本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是自由。鸟在东西方文化里都代表人类想要超越重力与神之使者相颉颃的愿望,也经常象征着脱离肉身、无拘无束的人类灵魂;《庄子·逍遥游》有“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鸟,《山海经》则首次写到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青鸟。童年时,妮农听爸爸讲解过摩托车骑行的原理:拐弯之际“我们把体重向弯位倾斜,从而调整摩托车的重心,这便抵消了离心力和惯性定律的作用!鸟儿在空中也这么做,爸爸说,只是鸟儿在空中不是为了旅行—空中就是它们的家!”妮农在城市之间赶集的男友吉诺,居无定所而安之若素,似乎就是这样一只以天空为家的鸟儿。小说楔子里,妮农回忆童年时爸爸将她浴后的每个小趾头比作“一只喜鹊,偷这偷那,偷完就飞走了”。妮农少女时代去布拉迪斯拉发探望妈妈泽德娜,在森林中远足采摘的是一种叫“雀鹰”的菌子。和女儿妮农一起游泳的泽德娜“泳衣黑黄相间,像一只蜜蜂”。
妈妈泽德娜从新近独立的东欧国家斯洛伐克,乘坐跨境大巴前往女儿的婚礼。行前,她去了一家地下室工坊选购鸟笛,准备送给她预想到将被绝症禁足的女儿;鸟笛制作者一个学哲学出身,一个曾在爵士乐团演奏,他们俩“反思了很多年,后来相信制作鸟笛是(他们)在这世界上可以做的伤害最少同时又能赖以为生的事情”。伯杰写那示范着吹响鸟笛的人:“马雷克一只大手握着它,将音管就到唇边。他的气息通过微小的风管,一吸一呼连成流淌的鸟唱。”
伯杰酷爱公路,喜欢驾着摩托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他年轻时曾经这样从伦敦开到阿姆斯特丹,再到罗马;年逾八十,也依然骑摩托车穿梭于法国阿尔卑斯山麓的乡间小道,那里是他长居的村庄昆西(Quincy)的所在地。在前往婚礼的路上,尚·菲列罗骑得飞快:“正如河流有奔向海洋的本性,人也有追求速度的本性。速度包含在人类最初归于神明的特性当中。在这大河之畔,交通尚未繁忙起来的晴朗早晨,尚·菲列罗如神一般驾驶着。他最细微的目光移动、手指接触或肩部运动都立竿见影,应付裕如,没有一丝凡人的延迟。”伯杰谈及骑行心得时说过,高速要求镇静,要求专注,尚·菲列罗全神贯注地骑行,尽管他转弯时“倾斜着仿佛在谛听大地……怀着怜悯俯身而听”,他却一时超越了现世的沉重痛苦,感到自由。
尚·菲列罗的本田CBR摩托车是红色的—爱与激情的颜色,也是血的颜色,革命的颜色。

《本托的素描簿》[ 英 ] 约翰·伯格著黄华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伯杰说过,他青年时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是由于悲悯。到了晚年,他形容自己为“Marxist among other things”,表示他尽管终生葆有马克思主义信念,但卡尔·马克思的世界观只是他其中一重基本信仰。伯杰最深爱的哲学家并非马克思,而是斯宾诺莎,还为斯宾诺莎写了一本文集《本托的素描簿》(Bentos Sketchbook)。他赞赏斯宾诺莎主张物质与精神不可分割的一元性,反对笛卡儿对两者的“虚妄”区分。斯宾诺莎是泛神论者,认为神内蕴于自然之中,他将“身体/物体”(corpus)理解为“在某种一定的方式下表现着神之本质的样式”。《到婚礼去》空灵的文字,令读者不难感到仿佛万象万物皆为神圣性的缤纷显现。吉尔·德勒兹分析斯宾诺莎思想时,则有这样精辟的归纳:当一个身体(物体)“遭遇”另一个身体(物体),或一个观念“遭遇”另一个观念时,有时两者结合而形成更有力的整体,有时一个消解另一个,破坏其各部分的一致性。斯宾诺莎提醒,我们归结于“恶”范畴内的一切现象,疫病、死亡,都属于消解性的“坏的遭遇”;他的哲学贬抑“善/恶”而重视“好/坏”这对概念。值得注意,《到婚礼去》缺少传统上属于“邪恶”的意象,如蛇、蝎子、蜘蛛等。妮农与传染给她病毒的露水情人的相遇也无涉善恶,只是一场“坏的遭遇”。但《到婚礼去》堪称希望之书,当然由于它着重“好的遭遇”。妮农与吉诺的相遇自然是好,后来吉诺对女友不离不弃,激发她的求生意志乃至两人决定结婚,更是如此。书中提到古人相信水银与硫黄交合产生金属,又把婚礼安排在河海交界处,都加深了婚礼的象征意义—“两者结合而形成更有力的整体”。
在朝着婚礼进发的公路上,妮农的爸爸、妈妈各自不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构成一幅当代世界的寓言式图景。其中几个小故事带有细腻动人的处境反讽(situational irony),因为不知情的外人只能想象到婚礼将至的喜庆,却无法看透妮农父母挥之不去的伤感。妈妈泽德娜在跨境大巴上的邂逅也由一种处境反讽而引发。

约翰·伯格绘西蒙娜·薇依肖像
在前往威尼斯的大巴上,坐在泽德娜身旁的光头男子托马斯跟她搭讪,问知她要去出席女儿的婚礼,连忙道喜。泽德娜脱口而出“但是我女儿HIV阳性”,竟把她在亲密朋友面前难以启齿的隐衷告诉了这个陌生人。原来托马斯是官方百科全书的编辑,政权更迭后被扫地出门,开出租车为生。泽德娜从她工程师的理性出发,觉得吉诺要跟妮农结婚是疯狂之举,他们这一对毫无前途。托马斯则看出,吉诺的原型是古代森林中的骑手,个性潇洒,不问前程随遇而安。交谈中,泽德娜第一次哭了,她引用茨维塔耶娃的诗来诉说自己的绝望。托马斯百般开解。大巴行至意大利,他冒着误车的风险买上来热饮美食,跟泽德娜分享。一如小说别处,伯杰在文字间充分诉诸感官:
他们俩喝起咖啡来,用印着圣母般的人像的蓝色纸杯,咖啡泡沫在男人的上唇勾了一条线。接着他们开始吃面包卷。泽德娜有珍珠般的整齐牙齿。
饮啖之间,托马斯也分享了他宏阔的历史观,显然他也是伯杰的代言人、第三个分身:
两个世纪以来,我们相信历史是一条大路,带领我们去一个前所未知的将来。我们以为自己是例外。当我们走过昔日宫殿的画廊,看见所有那些彩绘的大屠杀、临终仪式、浅盘上的首级,镶在画框里挂在墙上,这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走过了漫漫长路—当然,没有长到我们无法同情他们的地步,但是已经长到让我们知道自己超越了那一切。現在人的寿命长多了。有麻醉剂可用。我们已登陆月球。不再有奴隶。我们用理性解释一切,甚至于解释莎乐美的舞蹈。我们不追咎过去的恐怖事件,因为它们发生于黑暗时代。现在,我们忽然发现自己远离着任何大路,像海鹦鹉一样栖立在黑暗中的一块礁石上。
托马斯说现代人失去了在礁石上生活的习性,但他相信绝处逢生,人在危机中可以重新学会它;即使站在礁石上,人也可以发现希望。如伯杰访谈中表示的那样:“乐观主义和希望毫无关系。希望的要点在于,希望其实产生于非常黑暗的时刻。它好比黑暗中的一束火焰;和对于前景的信心并不类似。”

《时间》[ 德 ]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泽德娜和托马斯的故事结尾,她“低头看这男人的手,上面卷曲的毛都像字母Q”,似乎表示她心中依然充满无解之问(questions),不过,这段短短的二人旅程也在她心田埋下了安慰和希望的种子,有待壮大,直到她在婚礼上分明感到快乐的那一瞬间。
《九歌》诗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吉诺和妮农决定不计算“生别离”的惨淡前景,蔑视命运的残酷,选择用结婚来庆祝两人最美丽的青春。妮农尚未一无所有,她(照一个医生给吉诺的预测)大约可以指望两三年好时光,何况医学进步为将来留有一线希望。如何将一无所有变为一切?小说虽未道破,呼之欲出的答案是:珍重地把握住所拥有的,视之为全部一切—伯杰另一本书的标题,即是“Hold everything dear”。
婚礼将会在吉诺的姑姑家举行,是位于波河出海口的小村子。为什么选择这么个荒僻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在小说出版次年的纪录片《些许恩典》(A Touch of Grace)的镜头前,伯杰用两根手指交叉成十字,谈着“中心”和“家”:
中心的关键在于它是生活自然而然发生意义的地方。家是世界的中心,好比一个十字,有一条垂直线和一条水平线。……水平线就是所有的道路从村庄、从那个中心延伸出来,通向别的地方,最终通向整个世界。……垂直线,则是死者,可能还有尚未出生者,在大地和天堂之间往来的通道。啊,两条线这么(伯杰再次画十字)交叉的时候……要回答“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要找到意义,会比较容易。但现在世界上有多少地方符合这个情形?少之又少。
扎根村落、熟悉乡土生活和农人心灵的伯杰,用他饱蘸快乐忧愁的笔写出婚礼的狂欢,让全书在飞扬灵动又低回不已的曲调里终结。他铺叙每一道大菜的做法,列举令人垂涎的各种食材,在物质描写中体现神奇和灵性。西瓜贩子“像谛听神谕一样听西瓜响声”;某商人供应的薄肉片是“神品”(leaves from the Bible);银盘托着的白梭吻鲈站在自己的尾巴上,“像个长裙贴身的舞者一般等待音乐响起”……本堂神父为新人证婚后,村子里大开筵席,香槟四溢,客人们在摇滚乐队的伴奏下热情拥舞,新郎新娘一直狂欢跳舞到酒阑人散。与此同时,伯杰用仿佛电影中闪进的技法,预叙妮农未来的病痛和最后的死亡,最深沉的悲哀交错在最热烈的快乐之中。
德国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在《时间》一书中指出许多人共有的体验:“在爱情的幸福中,时间看上去会刹那静止。……人们遗忘时间,由此也忘记自己,忘记他的操心、兴趣、苦恼和责任。”歌手安溥(张悬)新近推出一首电子声效与唢呐交响的歌,最后两行条件句式的唱词吻合《到婚礼去》:“明白了没有尽头是一切的终点/爱情才能是死生中最长的一瞥。”伯杰回顾欧洲数百年的沧桑,动用整个人类文明的时间(从古埃及到公元二千年)并援引创世神话,以最开阔的视野来映衬一个不久于世的少女“最长的一瞥”,可见他的时间观何其超越。伯杰所崇敬的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曾在《致一位神父的信》中写道:“我们须抛弃对线性时间的迷信才能找到永恒。”佐巴纳科斯-伯杰讲的故事里,未来的某天下午,妮农会找到力量抬高一只手臂,被吉诺握住手,海龟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两人的手都在半空停留。“海龟会向外游泳,游走。他的眼睛会追随她进入永恒。”当莎士比亚笔下的青年情侣誓言长相厮守,说的是“比永恒更多一天”(For ever and a day)。伯杰故事里的永恒却不在于时间的无限绵延,而在于毫不计较时间长短,以当下面对永恒,“从容地生活”(吉诺对妮农说的原话“Take our time”)。小说高潮在一片热闹中有个宁静段落,伯杰不失时机放进但丁《神曲·天堂篇》的诗句:“在它深邃的无限中,我看见宇宙纷散的纸页,因爱凝聚而合成一部书。”无数古代人和中世纪人曾经相信神是宇宙这部大书的终极作者。无论你我相信什么,无疑是爱凝聚成了伯杰的小书。不知他是怀着什么样的信心、希望与爱,才把我们这混乱时代所有纷纷揚扬的书页,合成这样一种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