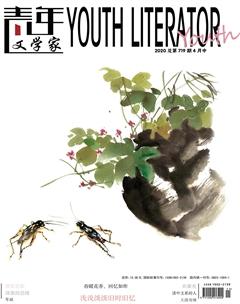车站
作者简介:冯歌迪(1999-),女,汉族,广东东莞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本科。
“这个假期,你跟你妈一起去旅游吧。”
……
装修得很宽敞的车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挤爆了售票厅。排队取票的队伍虽说没有买票的长,却仿佛永远也轮不到自己。四周黑压压的脑袋一次又一次抬起,骂骂咧咧之声不绝于耳。我不晓得他们丹田里哪里来的中气,居然能驱动人嘴像喷气式飞机一般一泻千里不间断地骂。
离上车还有大半个小时,我们兜兜转转总算捡了两个还算干净的位子。坐下后,母亲一时愤懑难平,还在絮絮叨叨地骂着某位插队的阿姨,我心底的不耐烦早就膨胀得爆出心窝,狠话不经意便露出了口:“可是你连个取票机都不会用,说你老怎么了?”她突然愣住了,下一句即将说出口的话还没来得及收回。随后,她吸了下鼻子,眼里的光涣散了,缓缓地把头垂得很低很低,整个人佝偻地坐着,愣愣地看着地板。我惊觉自己伤到她了,但怒火仍在心头烧着,倔强让我不愿低头认错,只得默默将身子背过去不再看她。
车站来往穿梭的人越来越多,行人掠过的风有股尘土的味道。我们两个坐在人群里,却仿佛与世隔绝,空气里一片死寂。
其实,我很讨厌她。
母亲从来都是要强的人,她永远像是在跟这个世界较劲一般发狠地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对与她有关的所有事。父母常常不避我地大吵大闹到半夜,最后往往发展到锅碗瓢盆摔了个干净,父亲夺门出走……此后,我的阳光被关进黑匣子,暴雨和阴沉成为生活常态。
我越长大,就越讨厌母亲,甚至一度认为是她毁了我,毁了我的家。
等到我已经年纪接近成年时,逐渐知道多了些关于母亲从前的故事。命运让她从小背负着沉痛的枷锁长大,支撑着年幼的她活下去的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个地狱。于是,她与家人不断抗争,并执意嫁了父亲远走他乡。婚后的母亲也没有过上想象中幸福的生活,婆家依旧重男轻女,但她为了保住我这个女儿做了更多的抗争……
母亲的要强,几乎是生活逼出来的。
我开始理解她变态一般的执着,和刻骨的刚强。但成长过程的伤痕已经存在,每每痛起来都让我无法真正放下心去接受她。
车站里黑压压的人群依旧在涌动,抬起眼四下都是急匆匆的脚步,或是沧桑麻木的脸。我沉沉地叹了口气,早就知道跟母亲出来会是这样尴尬,也不知我们是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无话可说,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即将开往华山的列车GZxxx开始检票!”
高铁车站的广播尖声响起,强势撕裂了我们之间的沉默。母亲很快站起来,轻松地说:“开始检票了,我们走吧。”一边说着一边手脚麻利地收拾好了东西看着我,我也同时站起来应和着她,一起走向检票口。
人流一下子就挤满了小小的出口,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和行李袋不仅堆叠得比人还高大,走的还飞快,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箱子自己要坐高铁,旁边只是碰巧挂了个人。我过了检票口走出大厅时队伍正好轮到她。母亲一碰到现代化的机器就头疼,我想她可能又不会了。果不其然,母亲手里紧紧捏着淡蓝色的车票,眉头紧锁地盯着眼前的自动检票机,将手里的车票使劲塞进去却怎么都失败,着急地整张脸都皱起来。我仿佛是冷漠的旁观者,但不忍和揪心却混杂一起不停翻搅,双脚生了根,明明想着应该要去帮助她,但又迟迟无法踏出哪怕是小小一步。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都游刃有余,永远要求完美永远优秀。
这尴尬得面红耳赤、一脸迷茫无错的人是谁?
这拼尽一切努力想要追上时代却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是谁?
她不是我的母亲,却又是我的母亲。
隊伍后面越来越多人抱怨,母亲的处境越发尴尬了,她面红耳赤,额头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神色慌张却又迷惘地听着旁人教她用机器的话。她根本听不懂,却又装出听得懂的样子不断附和点头。最终,在乘务员和四五个热心乘客的指导下,她终于成功了。霎那间,母亲整张脸都亮起来,好似初升的太阳将光洒进了她的双眼和笑窝,看见我就直直冲了过来,眼里流光四溢。
“其实也不难,高科技我还是搞得懂的。”得意的语调与她的嘴角、眼角一齐上挑。我本应该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咧开嘴角后发现喉咙被哽塞住了,最后只是生硬地张了张口。
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件小事。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辞掉了工作。她在家的时间更多了,发呆的时间却也更多,疏松的生活朝她展现出可怖的模样。母亲开始很有干劲地每天打扫卫生;到后来她的病逐渐加重,打扫得也不那么干净了,但依旧很卖力。某天晚上,她告诉父亲和我她今天又做了好多事,但见我跟父亲兴趣缺缺,说着说着就喃喃自语,然后很快地收拾碗筷钻进厨房去了。弄完厨房后她换了副模样,神采奕奕地出来看电视,拉着我继续聊她今天干了什么。我插了一句:“整天那么辛苦弄也不干净,你身体不好,还是歇着吧。”说完我就继续敲打电脑完成工作。她突然愣住,脸色黯淡了下去,头垂得低低的,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辈子要强的母亲,真的老了。而她却仍未察觉到自己的凋零,这,恐怕就是她眼里最深的迷茫吧。
谁又能一辈子在青春的车站里等候呢?在我还捏着淡蓝色的车票,隔着人群远远地向车站外眺望时,母亲在我不经意时已经过了检票口,坐上了不知通向哪里的列车。
“这是到哪儿了?”靠着车窗睡了一会儿的母亲突然问到。
“没到呢,我们还有很多站。”我看了看她,笑着说。
“哦——那还好,我以为这么快就到了。”她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我刚刚梦见自己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被列车丢下了,抓了抓头发还发现全白了!然后立刻吓醒了。”她有些嗔怪地皱眉,嘟嘟哝哝不知又说了什么,头一歪,靠着我的肩继续睡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吸了吸鼻子,抑住涌上眼眶的热流。
母亲,我们还有很多站,很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