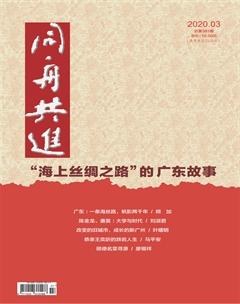广州“老宅院”漫记
王美怡


上世纪30年代的广州梅花村遍植梅花。冬天的时候,风把梅花吹落在深巷里,空气里飘逸着悠然的清香。在风起云涌的民国时代,“南天王”陈济棠和他的太太莫秀英,在梅花村的陈公馆里究竟度过了怎样的岁月?这一切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像那些在春天来临前凋零的梅花,秘密永远藏入了历史的泥土之下。
从陈济棠和莫秀英的一张合影中可以窥见某些故事的影子。陈身着西装,脸部线条坚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站在他身后的莫秀英却眼神复杂,透出一种不动声色的凌厉。当年的广州城里到处流传着他俩有点走样了的秘闻轶事。据说,陈济棠坚信自己的运气是他的太太带来的,一生对她珍爱有加。
当然,更多被提及的是陈济棠的治粤成就。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来,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1929~1936年,陈济棠在广州大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大动作。比方,他确定了城市的中轴线,建了一些至今仍被人称道的著名建筑,如市政厅、爱群大厦等,新辟了30多条马路,还大建糖厂和水泥厂。这期间,他拼命地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在黄埔建立了自己的雷舰队和雷舰基地,修筑了天河机场和白云机场,在东山开办了飞机制造厂,不断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
陈济棠曾亲笔写下长达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设计出广东1932~1935年的蓝图。据说他写完后竟“大病一场”。他期待广东在他的治下更加强大,最终问鼎中原。
那时,广州市面一片繁荣,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眼目。”
因了这令人目眩的“广州神话”带来的成功快感,这个旧时代的军阀按捺不住了。1936年,他联合桂系军阀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可是,这称霸的美梦瞬间就破灭了。1936年7月18日,兵败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踏上了逃亡香港的路途。
1936年冬天,梅花村的陈公馆一片狼藉,人去楼空。梅花依旧在枝头开放,可是树下已没有了主人的身影,梅花的清香在冷风里飘得很远,经久不散。一个时代结束了,这是
“南天王”的时代,纵然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可终究还是曲终人散、黯然谢幕。陈公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历史过客的驿站。
对山园
冬日的午后,街道上行人很少,我独自在广州西村福州路密集的民居间穿行。转过一条幽静的甬道,远远就可以看见那幢淡黄色的门楼。我知道,对山园到了。
每次走近自己要寻访的故居时,总有一种时空转换的晕眩感。周围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喧嚣的市声,而这些金粉脱落、朱颜已改的老房子,会在一瞬间让我不知今夕是何年,那些已成云烟的旧人旧事仿如电影镜头的推拉摇移,在我眼前倏然掠过。究竟是因为什么,他们的面影会从逝水年华中浮现出来?
比如说对山园的主人黄冠章,在所有正史的记载中,他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他是广东防城人,早年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以廉名勤慎见知于”陈济棠,官至第一集团军需处少将处长兼广东省银行副行长。1936年辞职去日本研究教育及经济学,后任香港建业银行公司总经理。
对山园看起来的确是富丽堂皇。正厅是一幢五开间重檐歇山顶殿堂式建筑,朱红大柱加斗拱飞檐,很像一座宫殿。后面的厢房呈四合院结构,清雅通透,树影婆娑。园内处处雕梁画栋,亭台水榭环绕。时至今日,这幢民国时期的私家园林仍然被某种挥之不去的富贵气息萦绕着。
在官方头衔和民间传说之下,往往隐藏着某些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黄冠章不仅是一个掌管“钱袋子”的官员,还是一间私立学校的校长。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他见“粤中士子罹祸赴港,学业荒废”,便在香港办了一间导正中学。香港沦陷后,黄冠章又把导正中学转移到茂名。1945年,黄积劳成疾去世,时年47岁,“弥留时,犹谆谆于教务之改进,校舍之增建,语不及私,其尽瘁教育,有如此者”。导正中学于1946年在广州复学,对山园别墅变成了学校的校舍。黄太太江瑞云继承夫志,独力支撑学校大局。
在一张残旧的黑白照片上,我看见江瑞云微笑着站在一群运动员中间,背景是由别墅改建成的课室。另一张照片上,一袭长衫的校长带领毕业生从对山园的门楼里昂然走出。这个时期的对山园一洗富贵的奢华,洋溢着某种让人怀想的刚健之气。
站在对山园重修的殿堂前,我忍不住想:当年的午后,对山园里的阳光是不是很暖和呢?雕梁画栋间是不是萦绕着子曰诗云的诵读声?从私家园林变成私立学校,从政府官员兼银行家变成呕心沥血的教育家,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主人黄冠章怎样的心路历程?
黄氏石屋
黄氏石屋藏在广州旧西关的街巷里。整幢建筑全用麻石砌成,门前有雕花的花岗石圆柱,屋内的落地满洲窗上是精雅的玻璃饰画,一派中西合璧的泱然大气,迥异于传统的西关大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族巨商云集西关,多宝、逢源、宝源、宝庆、宝华、长寿、毓桂、恩宁、丛桂等街道巨宅如林。世俗的热闹和贵族的雅致奇妙地交融在一起,氤氳成让人沉迷的西关风情。传说中的西关贵族,“好鲜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贪言中华文化”阿城语),有见惯世面的自在自足,亦有曲径通幽的格调情怀,在雅俗之间进退自如。飘在西关的梦痕花影间的种种传说,皆是活色生香的人间话本。
石屋的主人是西关名医黄宝坚。他好交友,好美食,家中常年聘请名厨。梅兰芳到广州演出,他在石屋设盛宴款待,满座宾客均盛赞黄家“治馔第一,任何酒家无与伦比”。他喜欢精美的家私,常请人到家里做红木家私,厅中的陈设亦不时更换。他又喜欢搞些小设计,家里的很多窗户、栏杆都是他自己设计的。石屋的大窗,也是他专门从江浙请来的名匠雕制的,据说一个月才能精雕细琢出一个花窗。他还嗜好收藏,和西关的大藏家黄咏雩是至交,家中藏有石涛真迹。
黄宝坚平静的生活中亦有可堪回味的韵事。他的二夫人梁少卿是香港的大家闺秀。1928年,19岁的梁少卿从香港来到广州找名西医黄宝坚看病,两人由此相識相恋,终成眷属。婚后,梁一直住在石屋,直到2004年去世。梁年轻时明眸皓齿,是典型的西关美人。在女儿黄媦德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都很忙碌,但他喜欢闲淡从容的生活。家里的花园虽然请了园丁,但他总是自己剪草种花,因为他觉得这样有乐趣。而且他心地善良,乐意照顾穷人。当年龙眼洞、沙河的那些农民,有时候天没亮就送个病人来,没钱的直接跟他说“我没钱”,他也就不收钱。
黄宝坚在石屋里度过的日常生活,有锦衣玉食的华丽,也有市井人情的浸润,铺陈出的是余味无穷的旧家格局。
小画舫斋
真喜欢“小画舫斋”这四个字,有天生的清气,让人如坐画舫,神思飞越。住在这个画舫里的主人,会是怎样的人呢?
有一天,忽然起兴去寻访小画舫斋。中午时分,在西关古玩街上,街上没几个行人,路边的古玩店里,稀稀落落地晃着几个看似闲散的中年男人,可分明有着警觉的眼神。走在这条新整修的街道上,总觉得有点神秘。
路边一排空荡荡的破房子前,一丛竹子从高高的屋檐上伸出来。竹叶被阳光罩着,绿得发亮。在竹影浮动的花岗岩门额之上,我看见了这四个字:小画舫斋。
这四个字,浮在那块古旧的花岗岩上,被影影绰绰的暗绿笼罩着,有一种令人着迷的清秀妩媚的气质。据说,这字是“善以北碑写行书”的赵撝叔题写的。
我站在那门额之下,呆呆地看了好半天。这屋子过去的主人叫黄景棠,早在30年代就故去了。到解放前,他的儿孙们还住在这个大宅子里。
黄景棠在旧时的广州商界,也是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他出身于马来西亚,父亲黄福是当地著名侨商。他自幼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回国参加科举考试,获拔贡功名,算是正途出身的士绅。他同情戊戌维新,梁启超等变法失败后,他也绝意仕进,专营商务。他在铁路、码头、房地产和新式商业等方面都有巨额投资,曾参与潮汕铁路的兴建,1906年粤路公司创办时更是关键人物,还投资开发广州的芳村地区,提出修建珠江大桥的计划。1904年广州商务总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坐办。
黄景棠不是一个只懂赚钱的庸商,他算
得上是有思想、有抱负的新锐商人。比如,
他曾创办《广东七十二行商报》。商报于1907
年8月4日开始发行,发刊词对广东商业的发展
以及广东商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充满自豪感:
“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
足迹,其民轻巧活泼,好冒险习劳,最合营业之性质,由是观之,我粤省于历史、地理、物
产、民俗上均占商界优胜之点,似非他省所及,谓为天然商国,谁曰不宜?”发刊词的结尾还号召广州商界向西方国家的商界学习,以爱国之热诚,为强国之基本”,达到“商业兴而国势振”的目标。1911年6月,黄景棠还策动广州商人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当时的粤督张鸣岐就一再在告示中点名威胁、警告他。他在兴办新式学校和参加慈善活动方面,也是不甘人后的。
黄景棠虽为商人,却有很高的文化修
养。他有一本诗集《倚剑楼诗草》留存下来。
有趣的是,里面多是四时感兴、诗酒唱和之
作,描写的都是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只字不提
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经商。
不过这也不奇怪。当年西关的巨商贵贾
其实都是很风雅的,讲究家世出身,喜欢诗酒
酬唱,绝没有一点暴发户的气息。大宅门里的
种种规矩,就像那些摆在厅堂里的紫檀家具,
有来历、讲格调。这些大宅子,在阴雨天的时
候,到处都泛着旧书的气息。
黄景棠,这个曾经泡在旧书里的商人,在荔湾湖畔修建了他的大宅子。它有一个好听
的名字:小画舫斋。
当年的小画舫斋是临水的。站在楼上,
可以看见荔湾湖上的清荷,连荷叶上蜻蜓那透
明的翅膀都看得清清楚楚。荔湾湖边种满了荔
枝树。到了夏天,白荷红荔的胜景就簇拥着小
画舫斋。那时候,小画舫斋是荔湾湖上一座最
迷人的画舫。
也许是临水的缘故,广东的风雅名士似
乎都有一种画舫情结。潘仕成的海山仙馆里,
有牡丹舸、莲花舸、红荔舸各一艘,极为豪华
精雅,是专供京中官员、文人雅士游湖品荔的
花舫。陈秋涛有舫名“此花身”,取唐人“几
度玉兰船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之义。邓云
霄有舫名“天坐轩”,取杜甫“春水船如天上
坐”之义。这些荡在湖中水边的画舫,寄托的
都是他们的人生感兴。
黄景棠干脆把宅子的主楼设计为一座画
舫,称为“船厅”。阮元的题匾“白荷红荔泮
塘西”就挂在厅堂正中,船厅的万字形红栏杆
上垂着疏帘翠幔。纯中国意味的审美,一向讲
究朦胧,翠幔自是少不得的道具。偶尔起身做
一回卷帘人,荔湾湖的清景尽在眼前,片片红
云、丝丝杨柳,都在清风里袅袅娜娜,人也如
在画中。
小画舫斋里船厅、花厅、书厅、画厅俱
备,亭台楼阁围拥着精致的小园林。这园子里
种满了九里香、白玉兰、米仔兰和茉莉花,一
年四季暗香頻送,配以嶙峋山石、古木修篁,
一派清幽意境。
小画舫斋的客厅名“静者居”。长日此静
坐,清茶袅袅间,有人泼墨挥毫,有人吟诗唱
咏,雪白的宣纸之上留下了这些旧文人的慨叹
感兴。广东书画界的名流,像朱疆邨、陈述
叔、丘逢甲、黄晦闻等,当年都是小画舫斋的
常客。画舫之中,自然是清景宜人,很助诗兴
画兴的。
黄景棠也是能诗之人。在诗人黄节留下
来的一本书画合册《蒹葭图》中就有黄先生的
题咏。诗云:春堂四面蒹葭水,吹作秋霜一
鬓丝。识透江湖风味恶,更从何处着相思。君
情一往深如水,惯听秋风忆故人。满纸潇湘云
水气,不缘风露已销魂。”
这蒹葭楼是黄节当年建在广州河南龙庆里
的书楼。这本《蒹葭图》册大约完成于1909年
至1912年间,写画题跋者多为书画名家,如苏
曼殊、陈树人、蔡守、黄宾虹、邓尔疋、潘飞
声、杨其光、江孔殷、黄孝觉等。黄景棠和他
们交往频繁、诗酒酬唱,想来亦是品味不俗。
黄景棠还好收藏,小画舫斋中藏有不少
珍品。比如李流芳的《山水图卷》、汪士慎的
《梅花图轴》、罗聘的《竹石图轴》由崇祯帝
朱批过的闽本《十三经注疏》全套等。吴昌
硕、康有为、张善子、吴湖帆等近代名家的作
品都在他的收藏之列。
就算是到了抗战期间,家国都在风雨飘
摇间,黄家人还是视藏品为生命。他们举家迁
往香港九龙“西洋菜街”居住时,还把大量藏
品带在身边,一俟住下,即把翁方纲书的“读
画楼”匾挂上。这读画楼很快又成了躲避战乱
的文人墨客的聚会之所。那时候,黄景棠已归
道山。可小画舫斋的后人,也有和他一脉相承
的气质、嗜好。
黄景棠的儿孙们都受过很好的西式教
育。他的几个儿子都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黄
子静学的是地质,九弟学的是法律,但黄氏兄
弟们都爱穿长衫,在家中不讲英语,日常生活
也无西方习气。兄弟们均能诗,尤以小弟黄明
伯为优。也不知黄氏兄弟做不做生意,是不
是也像黄老先生一般“识透江湖风味恶”,但
是,在小画舫斋的古树修篁下,他们总该获得
心灵的安宁吧。我情愿相信他们都是玉树临风
的男子,否则那些古画古书就被辜负了。
古旧的书香墨香和满园的花气融在一
起,画舫中别有一番风情在。中国风格的旧式
大宅子,是靠亭台楼阁、山石花草、字画古玩
营造氛围的,旧书古墨的气息缭绕其间,传达
的是书香世家的格局和气韵,簪缨之族的雅气
亦从此酿就。
旧时广州的大宅门里从不缺少诗书吟唱
之音,富商望族对文化素存敬畏之心,彼此以
儒雅相尚,对于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
石之事,无一不精。潘仕成刻印《海山仙馆丛
书》,伍崇曜辑撰《粤雅堂丛书》,更是自觉承
担起传承书香文脉的使命。而小画舫斋,承载
着乱世文人的黍离之悲,在旧时月色的笼罩
下,自有一种让人怀想的温情。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