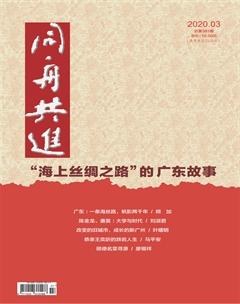外国人眼中的唐朝广州
郭晔旻

“广府是一个大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岸上,这条大河是流入中国海的。城与海之间,相距六七日的途程。从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岛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载运各种商品开进这条大河,一直开到广府附近。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袄教人就有二十万人。”
——阿拉伯历史与地理学家麦斯俄迭
从巴士拉到广州
公元八九世纪,正是西方历史上的中世纪。那时的西欧国家正处于“黑暗时期”,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市。天主教会的神学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触犯了教会的教条,不是被烧死就是被砍头。就在这时,文明的花朵灿烂地开放在东方大地上。中国的唐朝与阿拉伯的哈里发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两个中古文明高峰。
将这两大帝国连结起来的,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哈里发朝廷在商路上为客商设置了宿舍和驿站,开掘了水井,设立换马站,引得无数商队涌向东方。仅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从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798年(贞元十四年),先后来到长安的阿拉伯帝国(大食)使节就有39批。在怛罗斯战役(751)后被俘,流离阿拉伯帝国12年的杜环在他的《经行记》里记载,当时中国的绫绢机杼已经通过“丝绸之路”流入阿拉伯帝国。
可惜一场“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安史之乱(755-763)”结束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唐朝的军政势力退出了西域,使得“丝绸之路”陷于“道路梗绝、网络不通”的困境,就连诗人杜甫也发出了“乘槎消息断,无处觅张骞”的哀叹。
公元762年,杜环终于得以乘坐商船从阿拉伯半岛启程,回到广州。他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阿拉伯半岛,却从海路返回故国,恰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陆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固然盛极而衰,但东西方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未来属于海上。更值得玩味的是,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曼苏尔选中原本籍籍无名的村落巴格达(今伊拉克首都)作为京城的理由之一,就是“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已经把我们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
当时的巴格达在底格里斯河的码头长达数英里,停泊船只成千上万,有巨舰,有游艇、木筏、牛皮舟,还有中国帆船。“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至于地处巴格达以南,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附近的巴士拉,更是因成为大批中国货物上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转站而被阿拉伯史家称为“中国商港”。这与巴士拉因河网密布被日后的西方人称为“东方的威尼斯”真是相映成趣。作为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主要出海口(但因地理变迁海岸线淤塞外推现已远离波斯湾),《一千零一夜》中充满了有关巴士拉的故事,辛巴达就是从巴士拉出发周游世界的。
当然,巴士拉与中国之间远隔万水千山,海路往来谈何容易。好在唐代中国的造船能力可以说是傲视世界,造船工场遍布各地,仅扬子(今江苏仪征)一地就有造船场10所。唐代的中国商船大者可载600人至700人,载重万石。其船舶之庞大、坚固以及运输量之多,都是当时的洋船无可比拟的。时人盛赞,“只有庞大坚固的中国海船,才能抵御波斯湾的惊涛骇浪,而畅行无阻”。法国学者J·索瓦杰因此就说,“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人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
因此,在《汉书》里,中国商船航行到今天的印度“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的悲惨记载已经成为陈迹。成书于8世纪末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商人们利用中国造的海船从广州启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海岸西上,再沿海岸线西行至波斯湾,航行到波斯湾的尽头,全程最短时间仅仅只需惊人的89天。无独有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約825-912)在《道里邦国志》里也记载了从阿拉伯到中国的海路交通,即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海岸航行,途经印度境内各口岸,途径南海到达广州。阿拉伯人商人“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前进”,“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
长达万里的古代海上航行主要借助季风。阿拉伯商船“于9月从波斯或美索不达米亚出发,驶入海湾,之后逆东北季风行使到达印度南端。然后顺西南季风,于12月到达孟加拉湾。接着利用南中国海的南风于次年4月至5月到达中国广东。进入秋季后,他们借助北风离开,赶上印度洋的东北季风,并于来年4月至5月回到波斯湾。1980年阿曼苏丹曾卡布斯倡议并资助了一艘仿古双桅三帆船,由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直航东方大港广州的考察巡游活动。该船以阿曼古都“苏哈尔”命名,不装备现代动力设备和科学仪器,仅凭借季风鼓动风帆、罗盘针、牵星术以定方位航程。当年11月23日,“苏哈尔号”帆船从马斯喀特启航,沿着唐代海上航线驶向中国,途经中外历史文献记载的多个海域,总航程6000英里,历时216天,于1981年7月1日顺利进入珠江口,停靠在广州的洲头咀码头。这一壮举,无疑更加证实古代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海上丝路”交通的真实存在。
商人们的“广州梦”
在唐代的阿拉伯商人眼中,“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广州而非其他中国城市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广州称得上是唐朝海外贸易方面当仁不让的桥头堡。
广州城濒临南海,上接西江、北江、东江,三江由此汇入珠江,再流入南海。考虑到在古代,水运是唯一具有经济效益(运量大、运费低)的货物运输方式,作为海运和河运的交通枢纽,广州的地理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另一方面,大庾岭因其地势险要、环境恶劣,一度成为南岭南北交通的障碍。公元716年,“大庾岭新道”的开通更加改善了广州的陆上交通条件,打通了中原与岭南交通的咽喉。从此之后,从广州出发,从北江经过岭南重镇韶州(韶关),再越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境内,经赣江水系辗转到达当时大运河中心——扬州,再经由大运河便能到达大唐东都洛阳。这样一来,唐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就成了广州港的经济腹地。比如一位生活在9世纪的阿拉伯人曾说,“中国最好的麝香来自广府”。可见,本地其实并不出产麝香的广州,却成了麝香的最主要的集散和输出地。
交通上的优势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唐朝政府对广州海外贸易的鼓励态度。当看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船,以珍货与中国交市”的盛况之后,唐朝政府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使,掌管海上往来的船舶贸易、接待蕃客和征税。唐政府对外国商人之来贸易,只要是按规定依数交付价值(货税),和官市(官买)之后,就任百姓贸易(私人经营买卖)不加干涉。对此,公元9世纪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佐证,“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艘海商到达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对外国商人进行敲诈,唐朝中央政府还三令五申,禁止对他们滥征各种杂税。上面提到的苏莱曼还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一带)的商人,在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来到广州交易,与唐朝宦官发生了一场纠纷。宦官也就是俗称的“太监”,其职责原本是在宫中服侍皇帝。但从开元年间以后,宦官经常被派到各地充任监军,其中在广州任职者又往往兼任市舶使,称得上是权势熏天。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货品的交易上,那位呼罗珊商人与宦官发生了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宦官竟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谁知那位倔强的商人并不罢休,悄悄地从广府起程,花了两个多月光景,来到长安告状。按苏莱曼的说法,此时,如果呼罗珊商人取消控告,要被罚五十大板,再遣送回广州;如果坚持上诉,就要直接面君,并相应承担掉脑袋的风险。呼罗珊商人选择了后者,于是他被押到皇帝面前。好在经过调查,皇帝证实呼罗珊商人所讲属实,于是那个贪婪的宦官被召回,免去职务,没收财产,并派去管理墓地。
这样的公正处理不能不让苏莱曼感叹,“往时中国在行政上的卓著成效”以及“中国人打心底里尊重法制”,自然也使得唐代的广州成为海外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当时的另一个外国人,日本文豪真人元开在公元779年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就描述了当时广州市舶贸易的繁荣景象:“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阿拉伯、波斯商人远涉重洋来到广州,当然是因为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大利。公元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中就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列为三大名牌产品。阿拉伯人不惜一切代价订购中国精美的瓷器,或陈列于皇宫,或装饰于清真寺等建筑上。公元10世纪的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商人本·沙赫里耶则在《印度珍闻集》里记述了这么一则轶事:一位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到中国做买卖,公元913年自广州从海路携带大量中国丝绸和瓷器而回,发了一笔横财。他将一件精致的中国青瓷壶献给了阿曼城的统治者,从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尽管他是一个犹太“异教徒”。其影响所及,直到中世纪后期,著名的波斯诗人萨第(1208-1291)在《蔷薇园(Gulistan)》一书里,还曾记载了一个巴格达商人向作者倾诉他的计划,“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价,然后我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回到波斯。此后,我将放弃国外贸易而退居于一所大商店里”。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时阿拉伯、波斯商人心中的“广州梦”。
“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
每年春夏之交,唐代的外商借着东南信风,从西亚、非洲运来了珍珠、象牙、犀角及香料等商品,在广州叫卖,同时又购得瓷器、丝织物、纸、铁器、金银等回头货,在广州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季,等到秋冬时分,乘着东北风离开广州。
如此众多的中东商人来到广州,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阿拉伯商人因此很容易发现,唐代广州是岭南地区无可争议的中心城市。“广府是个港口,船只在那里停泊,另有其他近二十个城市归于广府管辖。”尽管它不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繁荣的贸易带来了滚滚财源,“纳入国库的钱每天可达五万迪纳尔”。
唐朝的广州已经居住着几十万居民,他们“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的习惯让阿拉伯商人大为震惊。那些在西方身价百倍的丝绸,在广州不过是寻常用品,王公穿上等丝绸,以下的人各按自己的财力而衣着不同”。中国丝绸高度精湛的工艺,更是让这些“老外”目瞪口呆,以至于由衷承认,“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苏莱曼记述道,一位阿拉伯富商去拜会广州城里的宦官。他注意到宦官胸口上长着一粒黑痣,这是透过穿在身上的丝绸衣服看见的。商人推测那宦官至少穿着两件衣服,里外重叠在一起。结果却发现,他竟然穿了五件之多,可是黑痣仍能透过这些衣服显现出来。然而,这甚至不是中国最好的丝绸。起码,“(广府)都督穿的丝绸,比这还更精美,更出色”。
广州的饮食习惯也给远道而来的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莱曼写道,广州人的“粮食是大米,有时,也把菜肴放入米饭再吃。王公们则吃上等好面包及各种动物的肉”。广州人“自己用发酵稻米制成的饮料(米酒)”,而不是西亚流行的葡萄酒。当然,苏莱曼接下来的判断——“中国人既不知道这种(葡萄)酒,也不喝这种酒”,其实并不準确。毕竟王翰早就写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或许这只是因为西域盛行的葡萄酒此时尚未传到岭南而已。值得一提的是,苏莱曼提到了“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此前他可能尚未见识过茶叶,因此对茶及唐人饮茶的嗜好还充满了新奇感。
相比衣食而言,来自海外的商人更关注的自然是广州的经商环境。阿拉伯客商惊喜地发现,“在商业交易上和债务上,中国人都讲公道”。财务通过契约文书约定,“放债人和借债人之间总是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尽管他们之间的交易没有证人,也不需要什么誓言的保证,但哪一方也不会背信弃义”。为了保障外商的财产安全,朝廷甚至发放专供他们使用的“过所”,上面注明持有者的姓名和父名、所属宗族、到达广州日期以及随身携带的白银、物品。“如果出现(物品)丢失,或(其人)在中国去世,人们将知道物品是如何丢失的,并把物品找到交还他,如他去世,便交还给其继承人。”
所谓“近者悦,远者来”。盛唐时期,法度清明。走南闯北见识颇广的西亚商人在心中比较了所经之地,终于还是得出了顺理成章的结论——“中国更美丽,更令人神往”。于是,海外商人云集唐代广州,其数量多至十余万,乃至在广州城里形成了外国人居住区——“蕃坊”。
广州蕃坊的范围,大体上包括今广州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以光塔街及其附近为中心。当时,珠江江面比现在要辽阔得多,怀圣寺以南还是一片汪洋,适合海舶停靠。各国人都可在此定居经商,保持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自印度的佛教徒居住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而穆斯林也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怀圣寺。据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座清真寺,其建立是为了纪念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先知,因此才得名“怀圣寺”。
这些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受到了地方当局的优待和尊重。唐廷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就是说,来华贸易的外商中,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日本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广州蕃坊设有蕃长或都蕃长,其办事机构叫蕃坊司。蕃长由蕃坊的外商推选,并经唐政府的认可,主要职责是管理蕃坊事务。此人同时也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领导和穆斯林间争议的裁决者。苏莱曼就此写道,“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位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按照中国皇帝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
如此一来,唐代的广州成为“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当时外国人的心目中,广州”甚至成为整个“中国”的代名词。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就提到,“支那(Cina)即广州也,莫诃支那(Mahacina)即京师也”。在梵文里,“Cina”就是“中国”的意思,而“Mahacina”则可意译为“伟大的中国”。唐代广州作为海洋贸易中心的显赫地位,就此也可窥豹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