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五毛钱电费
杨耀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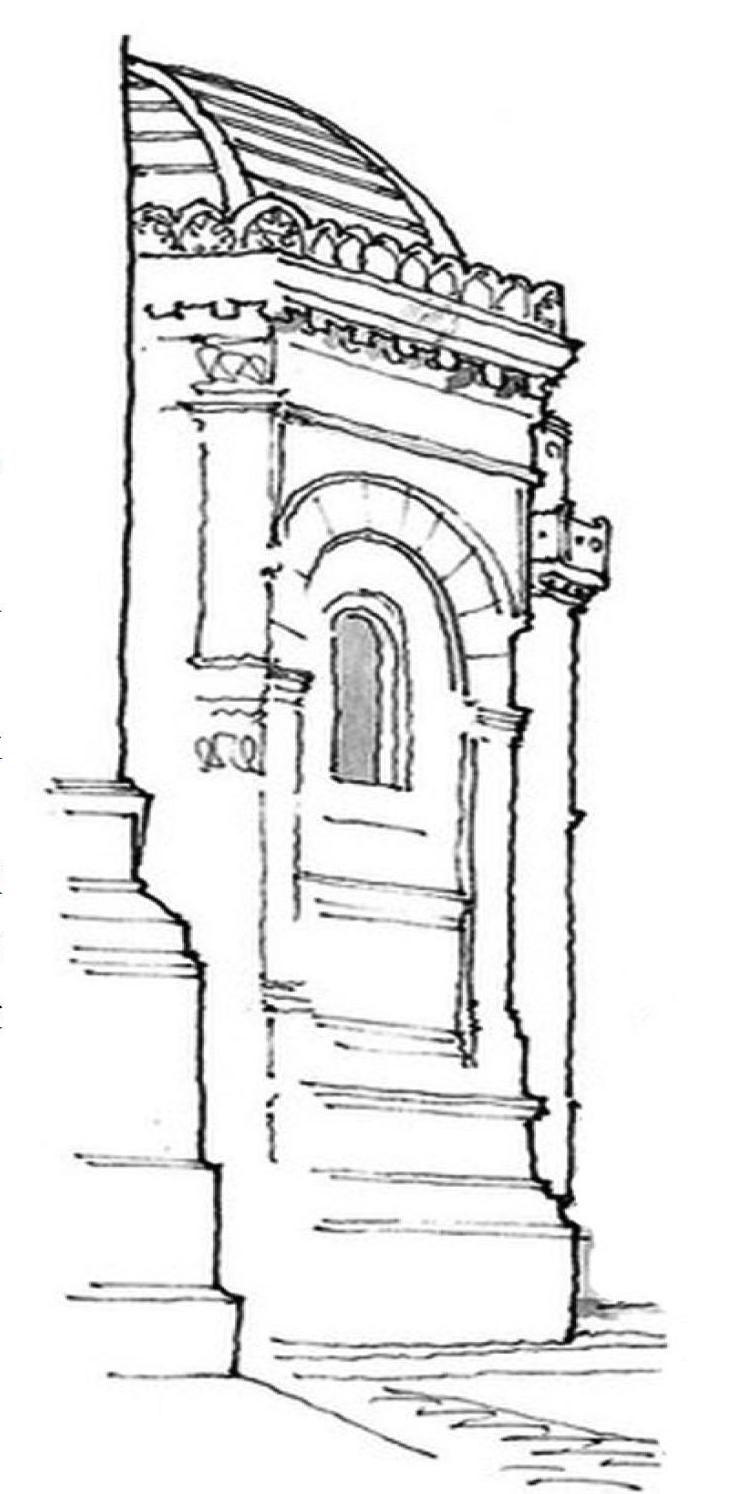
周龙在村巷里踽踽地走,耷拉着脑袋,神情沮丧,愤懑。
有人碰见了,问他:“周龙,咋了?谁惹你了?”
周龙头也不抬地说:“电惹我了。”
那人越发地奇怪了,说:“电咋惹你了?电会惹人吗?”
周龙说:“我上个月电费超支了。把我能气死。”
那人说:“花了多钱电费?”
周龙这才抬起头看着对方说:“六叔,花了两块五毛钱。”
叫六叔的哈哈大笑:“两块五?我还当是二百五呢!”
周龙把六叔拦住,看着他的脸说:“我上上个月才花了一块五毛钱,可上一个月就花了两块五。这不是超花吗?”
六叔把笑压抑住了,迎合他说:“就是超花了。这可是大事。哎,你知道超花在哪里了?”
周龙沉吟着说:“我想不出呀。你想吧,我不看電视,做饭不用电磁炉,睡觉不用电褥子。我家里没有电冰箱,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我的电灯泡是最小的,15瓦,可晚上我一般不开灯。我摸黑脱衣服,摸黑睡觉,摸黑剥玉米……”
六叔说:“你还摸黑睡女人。”
周龙说:“哪里的话。女人见我跑得比兔子还快。”
六叔说:“你给手机充电了?”
周龙大叫道:“没有哇。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手机呀!”
六叔说:“你用冰箱、空调、洗衣机了?”
周龙说:“我不是说了吗,我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呀!”
六叔又说:“周龙,电费超支了,你打算咋办呀?”
周龙说:“我不知道咋办呀!我现在是喇嘛抠屁眼,没有法了。”
六叔忽然想捉弄一下周龙,看看他的笑话,就又说:“周龙,电费超花是大事,你要找电管站,找镇政府,找村委会,让他们给你一个说法。不能这么白白地花冤枉钱。”
周龙眼睛夹了夹,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要是我不找他们,还不把我当成冤大头了。”
六叔说:“找去。大胆地去找他们。”六叔一天闲得蛋疼,最爱在村上捉弄人,看人的笑话。人们称他为瞎六。
周龙倒背着手,理直气壮地朝前走去了。
周龙是光棍汉。是我们驿马村众多光棍汉中的一员。周龙在成为光棍汉之前不是光棍汉,讨有老婆,老婆给他生有两个儿子。可是后来老婆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老婆走时带走了一个儿子,给周龙留下一个儿子。周龙的这个儿子后来初中没有毕业就去新疆搞火补。去了二三年之后出了事,死在那里。这样周龙就成了光棍汉。准确地说应当是鳏寡孤独者。
周龙在村巷里走着,迎面碰上了村委会主任张宝贵。周龙拦住了张宝贵。
“张主任,我有要紧事给你反映。”周龙说完眼巴巴地望着张宝贵。
张宝贵要去村委会上班,时间紧,可他还是站住了。“啥事,快说,我还要赶时间上班呢。”张宝贵说。
周龙扯着自己的衣角,眼睛朝地下看着。“你先说说,我的事你管不管?”
张宝贵生气了,“你没有说是啥事,我咋管?”
周龙在地上顿了顿脚。“好吧,我给你说。我家的电费上个月多花了。”
张宝贵瞪大了眼睛,“多了多少?”
周龙说:“共计是两块五。比上上个月多了许多。上上个月才一块五毛钱。”
张宝贵愣怔了一下,忽然就抡起了手臂。“我真想扇你一巴掌。”但张宝贵的手臂并没有落下,而是在半空中停住了,仿佛被人施了定身法,半分钟后,他的手臂收了回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周龙怯怯地说:“这事你管不管?”
张宝贵生气地说:“管你娘的脚!”张宝贵说着迈着沉稳的脚步走了。走出四五十米远了,又折转身子对周龙指指点点地说:“周龙,你再说你的电费的事,小心我收拾你。你把驿马村人脸上的皮丢尽了。”
张宝贵的声音引来了一群村人围观,他们把周龙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当听周龙说他上个月电费两块五多花了,就忍不住哈哈大笑。
有人说:“我当是二百五呢,才是两块五。”
又有人说:“二百五是爷爷,两块五是孙子。”
第三个人说:“对,周龙就是二百五孙子。”
第四个人说:“二百五孙子是周龙的绰号。”
周龙不接受这样的绰号。“你们才是二百五孙子。”
周龙勾着头、一本正经的样子越发引得人们哈哈大笑。
有人撺掇说:“这么严重的问题还不快找电管站去。”
周龙梗着脖子说:“当我不敢找他们。我现在就去找。我非要找出个眉目不可。”
周龙脖子梗着走出村巷,顺着通向小镇的公路向北走去。
村巷里的人们望着周龙远去的背影,笑得越发灿烂。
电管站柜台里坐着两个人上班,一男一女。男的白脸盘,女的满脸痤疮。周龙走进来站在柜台前,看着他们。
满脸痤疮的女人抬起头看着周龙:“缴费呀?”
周龙摇摇头,
女人说:“那你干什么?”
周龙咳嗽了一声,仿佛是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的电费上个月多了。我想问一下,为啥上个月多了?”
女人奇怪地说:“这有啥好问的,电费是按电表收的。你用的电多了,收费自然就多了。”
周龙说:“可我没有多用啊。我晚上一般不开灯,我不看电视。我没有电磁炉,我没有冰箱和空调。我没有用过电热毯。我没有用手机。我家里安的灯泡是最小的,15瓦。”
白脸男人从桌上的报表上抬起头来问:“你上个月电费多少?”
周龙说:“两块五。”
白脸男人说:“多少?”
周龙说:“两块五。”
白脸男人的眼睛瞪得奇大。“两块五?怎么就是多了许多?”
周龙说:“可我上上个月才一块五毛钱啊!”
痤疮脸女人明显在强忍着才没有笑出来,但眼角已经有了泪花。“那么你认为多少钱电费才不是多花?”
周龙想了想:“我不知道。只是我想,上个月比上上个月多了,可我又闹不明白多在啥地方。我上个月与上上个月用的电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我没有再多用啊。”
白脸盘男人这时候站起来,很近地靠近周龙,眼睛看着他,说:“你今天来的意思是啥?”
周龙觉得白脸男人的目光很尖,银针一样要刺到他的心脏里去。
“你们能不能查一下,看我多在啥地方?让我心里明白一下。”
白脸盘男人说:“你是哪个村的?”
周龙说:“驿马村。”
白脸盘男人这时候坐下了,说:“你们村主任张宝贵知道不知道你的电费一事?”
周龙说:“我来时在村巷里碰上他,我给他说了。”
白脸盘男人说:“他听了是啥态度?”
周龙犹豫不决地说:“没有啥……”
白脸盘男人说:“他是不是把你训了一顿?”
周龙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痤疮脸女人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白脸盘男人没有笑,而是一本正经地说:“这事太严重了,我们电管站处理不了,你去找镇政府吧。”
周龙讷讷地说:“镇政府管电费的事?”
白脸盘男人说:“镇政府啥事都管,你去找他们去。”
周龙转身向外走去。
身后传来了瓜脾、凉怂的骂声。
驿马镇政府座落在镇街东南角儿上,大门朝东。门前是一条南北向的黑油油的柏油马路,向前直通到陇海线。周龙走进镇政府时,镇政府大院里没有一个人影,院子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从一个办公室里走出一个青年人,问周龙找谁。周龙说他找镇长。年轻人又问他是哪个村上的人,周龙说是驿马村。年轻人笑说:“我就在驿马村包村,怎么没有见过你?”周龙说:“可我见过你。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轻人把周龙领到镇长办公室,对镇长何栋梁说这人找他,就出去了。
何栋梁招呼周龙坐下,给他倒水,态度十分热情。周龙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何栋梁问他可有啥事。周龙正了正身子,喝了一口水,说了自己在电站说的事。何栋梁听了晶亮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半天,说:“你看过医生么?”
周龙不解何意。“我看医生干什么?我没有病啊。”
何栋梁转过目光不看他。“一块钱就算多花了?那么多少钱不算多花呢?”
周龙说:“我就是弄不明白啊。一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谁能告诉我,我为啥会多花出一块钱?”
何栋梁不看周龙了,看桌子上的材料。
周龙说:“上一个月与上上一个月一样啊,我没有看过电视,我有时候晚上开灯,可也只开一会儿,睡觉时我总是把灯关了。我家里没有啥电器,所以也不用电。可一个月下来却比上一个月多出一块钱。我想,会不会是电表不灵了,所以这才错了。”
何栋梁强忍着厌恶,说:“你先回去吧,我让电管站的人帮你查一下,你看如何?”
周龙说:“电管站的人我找了,他们让我找你呢。”
何栋梁的眼睛瞪圆了。“电站哪个人让你找我的?”
周龙说:“电站那个白脸盘男人说的。说这事归镇政府管,让我找镇长。”
何栋梁说:“他哄你呢。这事归他们管,他们不管是失职。”何栋梁看了一眼周龙,又说:“你先回吧,我随后找他们电站算账。”
周龙说:“那我啥时候再来找你?”
何栋梁皱眉说:“你不用再来了。到时候会有人找你说明情况的。”
周龙转身出去了。
何栋梁给电站打电话,对着话筒狠狠地骂道:“门站长,你狗日的不想干了言语,我另找人干。你把一个上门问电费的二球打发到我这里要干啥?你马上查是谁打发的,问清了让他马上滚蛋。”
周龙回到村上等镇政府的消息,可一连等了三四天,没有丝毫音讯。周龙在村巷里行走,村人问他,电费的事问清了没有。周龙说:“何镇长说他问了电站后给我回话。我现在等他的消息呢。”有人说:“何镇长哄你个瓜娃呢。你当真呢。”周龙说:“何镇长那么大的官能哄我?我不信。”村人又说:“你不信就等吧。反正等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有人给你回话的。”
六叔也这样说。六叔看到周龙被他哄得到处乱跑,心里觉得可笑。但又有点于心不忍。
周龙又等了三四天,何镇长还是没有给他回话。他想会不会是何镇长打电话给村主任张宝贵说了,而张宝贵又把回话的事忘了。于是,一天上午,周龙吃过早饭后倒背手来到离驿马村有二里地的村委会。张宝贵正在里面上班,看见周龙了,眉头皱成一个紧疙瘩。這几天村上要迎接扶贫检查,他与村上其他干部正手忙脚乱地填报表,那些报表真多,他看着也眼花缭乱。
“周龙,你跑来又有啥事?”张宝贵虽然心里十分讨厌他,但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十分关心他的样子,招呼周龙坐下说话。
周龙坐在沙发里,双手抱着腿,下巴搁在膝盖上。“镇上何镇长没有给你打电话?”
张宝贵奇怪地说:“何镇长打电话?何镇长打啥电话?你咋知道打电话?”
周龙说:“我给他说了我的电费一事,他说问一下电管站,然后给我回话。可七八天过去了,他并没有给我回话。所以我想他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让你给我说一下电费的事。”
张宝贵这时候从座椅上站起来,走近周龙,眼睛很近地看着他。“周龙,你还嫌不够丢人?你的两块五毛钱电费已经成了天大的笑话,传遍了全千乔县,传离了全驿马镇。你把我们驿马村的脸丢尽了。”张宝贵满脸怒气,一双眼睛里似要喷出火来。“你哪里缺一两块钱?”
周龙说:“这是缺钱的事吗?”
张宝贵说:“不是缺钱你说你的电费沟子痒得很?!”
周龙说:“我不明白我的电费为什么比上月多出一块钱,找政府,找电站问问难道问错了?”
张宝贵离开周龙,屁股腾地一声坐进椅子里。
“电费是按电表收的,你比上一个月多出一块钱,那是你用电比上月多了一两度。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也想不通。你的脑子是不是装满了青泥?!”张宝贵脸上满是憎恶。“你不从自身找原因,你找电站,找何镇长干啥?他们能知道你为啥多用了一两度电,多花了一块钱?”
周龙嘴里嗫嚅着说:“我找他们问一下犯法吗?”
张宝贵说:“你不犯法,可你犯了众怒。”
周龙眼睛布满了怅惘,说:“我问我的电费,犯了啥众怒?与别人有啥关系?”
张宝贵说:“我告诉你,你再一天胡说八道,为我们驿马村脸上抹黑,我就把你的低保户取了去。”
周龙说:“你要是取了,我就天天拄着一根棍子,到全村讨饭吃。”
张宝贵怔了一下,笑说:“周龙,你回去吧,何镇长那里我给你问问,如果他没有跟电站联系,我让他给你问一下。你呢,回去以后再不要到处乱问了。你不就是多花了一块钱吗?这样吧,我这里有二十元钱,你拿去,把你多出的电费弥补了去。行吧?”说着掏出二十元塞给周龙。
周龙把钱放在茶几上。“我不要你的钱。我只是想知道超支的原因。我不为钱。”周龙说着起身走出办公室。
身后传来了村委会一班人的哈哈大笑声。
又等了一段时间,果然再没有人找周龙说他电费的事。村上人只有看到周龙了,才会想起不久前他的两块五毛钱电费的事。但也懒得再说什么了。只有六叔看到周龙了,还会旧话重提,对他说:“我说的没错吧,你说的事没有人管的。你不要再找人了,球不顶的。”
周龙看着六叔,觉得很遙远,似乎全身罩着一层雾,喃喃地说:“我不看电视,做饭不用电磁炉,睡觉不用电褥子。我家里没有电冰箱,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我的电灯泡是最小的,15瓦,可晚上我一般不开灯。我没有手机,我也不会给手机充电。我摸黑脱衣服,摸黑睡觉,摸黑剥玉米……”
六叔忽然说:“你的电灯泡瓦数太大了,现在商店有卖3瓦的节能灯泡,你买一支装上,更省电的。”
周龙去镇街上的电器商店买节能灯泡,见了售货员喃喃地说:“我不看电视,做饭不用电磁炉,睡觉不用电褥子。我家里没有电冰箱,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我的电灯泡是最小的,15瓦,可晚上我一般不开灯。我没有手机,我也不会给手机充电。我摸黑脱衣服,摸黑睡觉,摸黑剥玉米。可我上一个月的电费花了两块五。”
女售货员压抑住笑容,说:“那你就买一支小的节能灯泡吧。3瓦的。”
周龙看着女售货员,说:“有没有1瓦的?”
女售货员说:“节能灯最小的是3瓦的。”
周龙说:“啥时候有1瓦的我买一支。”
周龙走出电器商店,在镇街上转悠。
有一个与周龙在一家敬老院一起待过几天的光棍汉碰见周龙了,问他干什么。周龙喃喃地说:“我不看电视,做饭不用电磁炉,睡觉不用电褥子。我家里没有电冰箱,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我的电灯泡是最小的,15瓦,可晚上我一般不开灯。我没有手机,我也不会给手机充电。我摸黑脱衣服,摸黑睡觉,摸黑剥玉米……可我的电费上一个月花了两块五毛钱。超花了。”
那人呆呆地望着周龙。
此后,周龙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把这句话喃喃地说出来。
再后来,当他刚刚说了前一句话,后面的话别人就替他说出来。
当别人说出周龙要说出的话时,周龙就在旁边恶狠狠地瞪着他。
忽然有那么几天,村巷里没有周龙的身影出现。驿马村的人们在下面窃窃私语他干什么去了。分析了几种结果,都觉得不可能。终于有人怀疑他可能出了问题,翻墙进入他的家门,发现他已经死了。看样子,他是想把电表拆下来,拿给管电表的人去检验,却不想触电身亡。
责任编辑/乙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