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水
◎ 陈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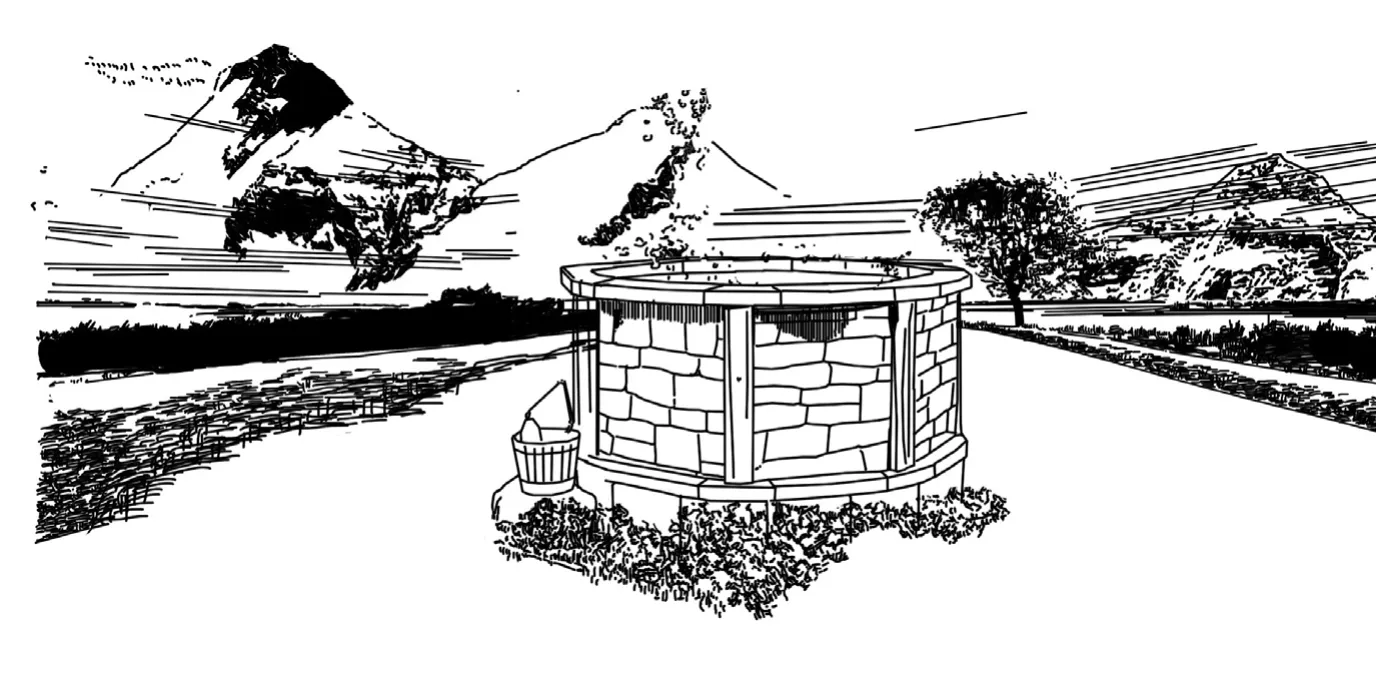
我们农村,一个村庄,一座院落,一处集市,甚至几户人家的屋前或屋后,都会有水井。我初挑水时还没有扁担高,见大人天天忙农活,便主动要求挑水。母亲很高兴,夸赞一番,指点一番,就任我挑着桶独往独来。
我们家南面的四方井最是热闹。挑水的人来来往往,洗衣服的、做凉水的、打神仙豆腐的,让水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立在井边,从肩上放下空桶,双手抓住桶的提把,蹲下身一按,水桶斜斜地没入水里,用力一提,将装了井水的桶一点一点弄上来,便又去打另一桶水。然后,套好扁担上的棕绳,弯下身子挑了起来,这下,仿佛一座小山移到身上。一走动桶就晃得厉害,一下是前边的,一下是后面的,水连连溅出。我忙弯下腰,让不老实的水桶待在地上。我生气地念叨:“看你还捣蛋不捣蛋!”我喘了口气,便又迈开脚。桶时高时低,这只一翘,那只一沉,弄得我无可奈何。歇歇肩,停一会,我又走起来。慢慢地,我找到了肩上竹扁担的中间点,摸索出了走路的节奏。水桶老实了,安静了。脚上像戴了脚铐似的,我挪步,向前,一刻不停,腿脚变成了木头。我忍着,我挺着,心里“一二三四”地数着步子。汗,虫子般爬在身上,我胸脯一起一伏,喘气声越来越粗。好不容易,到了家前面马路旁的坡上,突然嘭的一声,桶底檐碰在石头上,水溅了出来,弄湿了我的布鞋和裤子,幸好木桶没有碰坏。
这是我第一次挑水。怎么进的家门,忘记了,只记得母亲见我挑回半担水,面露喜色,连连夸我。当听我讲上坡时磕碰到,她二话不说,将水桶的绳一挽,仿佛把我挽成了男子汉。 再去挑水时,桶高度合适,一点也不磕碰了。日日挑水,久而久之,我俨然成了挑水的好手,但意想不到的事还是有的。
一天傍晚,邻村放电影,大小路上扛长凳、提椅子的人赶集一样涌去。我正挑着水往家赶,看到这情景,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萤火虫出来了,在水边、路旁一闪一闪;青蛙的叫声一阵比一阵密;蝙蝠在夜空下飞翔,绕弯转向,灵巧极了。月亮升起,四下亮晃晃的。我肩上沉沉的,步子踉跄。突然,一不小心脚趾踢在石头上,我痛木了,放下担子一看,趾甲翻开,血淋淋的……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段日子,我爱在月光下挑水。此时,清清静静,井水满满。夏夜,凉气直冒,井水化作厚厚的大玻璃,清亮亮的。打着手电筒往井里一照,如磁石吸住了小铁钉,我立在井边一动不动。只见井壁上是满满的虾子,有的弹跃着,有的划动腿儿,挤挤挨挨;水晶莹如珠宝;井底墨绿,枝枝蔓蔓的水草,厚厚的如地下森林;红鱼儿悠悠地游着,在水草间出没;而水草枝上横卧着几条胖乎乎的泥鳅,懒懒的像在做梦……我看呆了,目不转睛,好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好一口活力四射的井。
想想吧,满天星斗,夜凉如水,一个少年在井边,或立或蹲,久久地享受大自然杰作的恬静与美好,不也是一幅画吗?
每年正月初一这天,母亲是不要我去挑水的,她让我好好休息,多睡一会儿,自己则在天边还没出现鱼肚白,雄鸡还没打鸣的时候,就打开家门去了井边。母亲带上一叠纸钱、三支香,虔诚谢井。她到井边点香烧纸,喃喃自语,感谢井的恩泽与滋养。这是我们地方的风俗。等庄重的仪式完成后,母亲挑上满满一担水,高高兴兴迈开步,把新年的第一担水挑进家中的灶屋。母亲这新年的第一担水,永远挑进了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