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2020-05-30 10:48:04
语文建设·上 2020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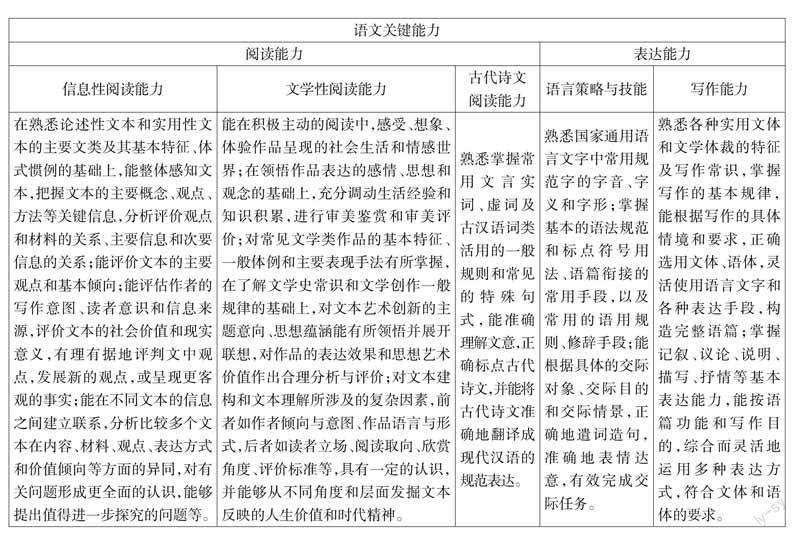
我以为文字白话的问题,没有什么多爭执;文字的本身,没有什么大罪。现在要攻击的,是那些将文字作玩物的罪人,却不可牵连到文字本身来。正和墨子“不受盗,非不爱人也”那句话相同。有些不分皂白的,见说不爱盗,他就连人也不爱了。这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的一类了。文字两字,在古来没有什么大区别。现在用通行的解释,文算成篇的,字算单体的。关于文的:
一、体无骈散。骈散分体是文的弊。古人偶有韵语,皆出自然。后世习于纷华,文亦浮靡,才有骈体。大都“徇物忘身,勾心斗角”,本无价值。于是有人破骈句成单句,号为散文。但是不知求新,一味复古,故有模仿六经,步趋诸子的文人。或好诡异,或逐空疏。道定一尊,人难异说。文也就弊极了。
二、用无古今。文本是代言语,达意思的。古今中外论文字用途,不出六字。至于习惯风俗不同,造句用字也就不同。说到真用处,不能因时有今古,文也就有区别。
三、境有虚实。文人用心的地方有虚有实。因为理想同实事是不能不并行,实与虚不能分优劣,恰如一张纸的两面,邻居的东西。如何我们可以论优劣?
四、意有深浅。情深的不是普通话可以表出;理真的不是平常文可以写出;事繁的不是简单语可以叙出;凡此皆功夫深浅的问题,亦不是故为深奥。
五、法有工拙。文作得工不必就深,作得拙不必就浅。但是有深意作得不工,和无深意作得工,一样不好。所以初学作文的人,一定要教他作法。如何才能作得工?如何才能省字省力,并且有趣味?这其中岂是没有定法的?
六、言有真假。记实事、说真理、言至情,都是真文。无病而呻、不欢而笑、口是心非,以及谀墓颂恩应酬的文,都是假文。真的虽古犹今,假的虽古当废。
——刘永济《对于改良文字的意见》
(选自刘永济《文学论默识录》,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原载1920年《太平洋》第2卷第3号)
猜你喜欢
今日农业(2021年15期)2021-10-14 08:20:12
东方考古(2020年0期)2020-11-06 05:34:58
家庭影院技术(2019年8期)2019-08-27 02:44:42
中华诗词(2018年11期)2018-03-26 06:41:36
小火炬·智漫悦读(2017年7期)2017-09-29 22:41:45
汉语世界(2016年2期)2016-09-22 11:48:41
新丝路(下旬)(2016年11期)2016-05-18 07:07:57
焊接(2016年4期)2016-02-27 13:02:44
时代英语·高二(2015年2期)2015-05-18 11:29:19
时代英语·高二(2015年1期)2015-03-16 09: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