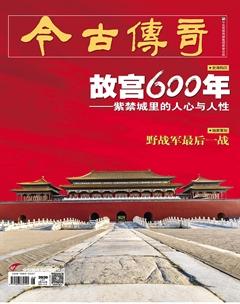伪满洲国的朋友圈



伪满洲国在1932年宣告“成立”之后,由于未能得到国联及列强认同,它的“外交”对象便只有日本。作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想要改变此种局面,也只能听从日本安排。在日本的授意下,为了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伪满洲国提出十分优厚的条件,但依然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
而日本在退出国联后,在伪满洲国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对伪满洲国的控制也更加严密。至此,伪满洲国的“外交”也只能沦为日本侵略及掠夺的工具。
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伪满洲国13年间仅得到17国承认,这其中大多为法西斯阵营国家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
日本:不择手段,逼迫中国承认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是日本陆军军人绑架国家和政府的生动案例。仅仅靠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几个中级军官策划挑动,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的背后支持下,关东军数月间便吞并了中国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莞尔三人讨论处理中国东北未来事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最初主张“将全满作为我国领土予以统辖占领”,土肥原贤二坚持“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经过激辩,土肥原贤二的意见成为最终决定。
土肥原贤二說干便干,跑到天津策动“便衣队暴动”,将退居租界的溥仪带到东北。1932年3月1日,溥仪被日本人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拥立为“满洲国执政”。3月10日,伪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等17个国家发出通电,希望“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好友邀约的结果很尴尬。通电发出次日,哈尔滨当局邀请各国领事参加祝贺伪满洲国“成立”的宴会,结果除日本代理总领事外,没有一位外国外交官出席。就连日本政府,也是在事隔半年之后的9月9日才宣告:“尔来帝国政府于半载之间,以绝大的关心及细密的注意,留意于满洲国内之事态发展情形后……乃期于此际从速承认满洲国,促进该地方之安定,并巩固帝国之康宁,与永维东洋和平之基础。”
对日本与伪满洲国“建交”抗议最激烈的当然是中国。1932年9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发出抗议书,直指“日本既以武力掠据东三省之全部,乃从事于傀儡组织之制造,谥之曰满洲国,而使溥仪为主,一切实权则操之于向东京政府负责之官吏之手”;“日本遽行承认伪组织,此项举动,一面适足以增加其罪戾,一面无异对国际联合会之权威,为侮辱性之挑战”。
中国越是抗议,日本便越是不择手段地想逼迫中国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越过长城线直逼平津,逼迫国民政府华北负责人何应钦签订《塘沽协定》。通过这次战争,日方不但将热河省(省会承德市,是中华民国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辖区分布在现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辽宁省。1955年7月30日撤销)纳入伪满洲国版图,还强迫要求解决伪满洲国与关内的通车、通邮问题。国民党官员王子壮评论:“其目的无非诱我对伪满国作事实之承认,但我国如果上此大当,外交前途益将陷于不利也。”立法院也向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提出“通车问题,决不可商,日如提议,只有拒绝,庶免有承认伪组织之嫌”。
但是,关内外本为一体,民众彼此往来、亲友互相通信是客观需求,国民政府不可能用长城将之隔绝。为免承认伪满洲国的嫌疑,1934年5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通车事务应交由商业机关承办,车票应由该商业机关发行”。经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亲赴上海,与规模最大的旅行机构中国旅行社老板陈光甫谈判,以“如不接受,则华北各省有被侵入可能,则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相劝,陈光甫终于答应试办通车业务6个月。
从1934年6月至12月,中国旅行社与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共同组建东方旅行社,进驻山海关,承办所有进出东北的客车车票、货运业务,以该社名义收费、结算,以此表示与政府无关。
中日双方也开始了关内外通邮谈判。会谈中,中国方面严词拒绝邮票上出现“满洲邮政”字样,不允许加盖“满洲国”邮戳,在票面上也不许印有溥仪头像等“不适当的花纹”,日本方面同样以各种条件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谈妥,使用仅有“邮政”二字的特殊邮票实施通邮。学者何辉庆评价“双方之上级决策单位察觉,邮票在主权的承认上有超乎他们想象的效力”。
政府的苦心并不被战区之外的民众理解。上海激进民众团体对中国旅行社参与通车极为愤慨,指责中国旅行社“于本年六月间,悍然不顾举国之反对,扶同南京政府之卖国政策,居然以第三者、纯商业机关之巧妙名目,与日合作,承办平沈通车,陷我国于事实上承认伪国而不恤”,号召各界断绝与中国旅行社的业务往来、不从中国旅行社购买车票。中国旅行社上海本部的玻璃也遭人砸毁。压力所迫,中国旅行社在1934年12月试办期满之后退出东方旅行社业务。
此后,历经华北事变、绥远抗战,直到“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突然发现了另一个达到“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目的的方法。1940年11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与满洲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闻爆出。不过,这个“国民政府”虽然尊奉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宣称遵循三民主义,使用民国纪年、青天白日国徽和满地红的国旗,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货——它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伪政府。
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政府的“外交”丑剧
日本侵华期间,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等地扶植了一批汉奸傀儡政权,并千方百计把它们捆绑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战车上,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驱使和利用它们,以达到其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扩大侵略战争的目的。
在日本的操纵之下,各个汉奸傀儡政权之间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其中,伪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尤为活跃。这场“外交”活动是近代史上的一出丑剧。
在日本的策动和操纵之下,1940年3月30日,南京伪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伪满洲国立即表明“全面协调友好”的态度。
1940年7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称霸世界,近卫文麿内阁通过了《基本国策大纲》,图谋建立所谓“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它竭力操纵汉奸傀儡政权,开展“外交”活动,以达到其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目的。于是,两个汉奸傀儡集团奉日本主子之命,开始打得火热。
此后,在日本的精心策划和导演之下,双方进一步调整所谓“满华外交”关系。伪满洲国派“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作为“全权委员”来到南京,于1940年11月30日同日本全权大使阿部信行及南京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一起签署了“联合宣言”,宣称“日本国、满洲国与中华民国谋求三国间以互惠为基调之全面合作,以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之成果,为此应采取必要之一切手段”,三方“将根据宣言之精神,迅即缔结条约”,为“建交”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至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双方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构成了所谓“日满华亲善提携”的格局。
为此,它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人员互访、互派“大使”、互设“外交机构”等“建交”活动。1940年12月10日,南京伪国民政府“特使”、“外交部长”徐良来到“新京”,向溥仪递交“国书”,开始所谓“国交”。1941年1月6日,伪满洲国任命吕荣寰为“特命全权大使”,一周后赴南京递交“国书”。南京伪国民政府也任命廉隅为驻伪满洲国第一任“大使”,并于8月25日递交“国书”。10月22日,伪满洲国将北平通商代表部改为“大使馆”分馆,把上海通商代表部、天津办事处改为“总领事馆”,济南办事处改为“领事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勾结更加紧密,汪精卫、周佛海、张景惠等大汉奸们纷纷粉墨登场,大张旗鼓地上演“外交”丑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虚张声势、摇旗呐喊。
1942年3月1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他宣称:“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后,中国政府声明与日本同甘共苦,满洲帝国政府也声明与日本同心协力,这是东亚轴心向全世界发扬的共同精神。”他还祝贺“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昌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1942年5月7日,汪精卫抵达伪满洲国进行访问。8日上午,汪精卫等人前往伪皇宫与溥仪会见。汪精卫“就建国以来,国运之昌隆和满华国交之日益发展前途祝辞”,“皇帝陛下致欢迎辞”。
汪精卫的伪满洲国之行,就其个人来说,他是十分不愿意去的,但是,他又不得不去,因为这是日本主子之命。而溥仪对汪精卫来伪满洲国,也是“很伤脑筋,但为了给主子面子,踌躇再三,还是在勤民殿召见了他,并赐宴招待”。
显然,这是日本主子不得不导演而其奴才们又不得不高唱“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民族之团结”的所谓“亲善访问”的一出丑剧。南京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之所以共同上演一出出“外交”丑剧,既是为了适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它们苟延残喘的需要。特别是两个汉奸傀儡政权在日本卵翼下出笼后,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处于可悲的孤立的阴影之下。所以,它们才不得不通过上演这样的“外交”丑剧来制造舆论,自欺欺人,掩饰其颓丧的情绪,摆脱其内外交困的窘境。
1942年6月8日,张景惠等人去南京回访,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到机场迎接。张景惠在机场大放厥词:“日前贵国汪主席阁下,正式访问我国。皇帝陛下为此答礼,特派本使,今抵贵国首府南京。回顾两国满华之交,前年十一月,由于满华日三国共同宣言而确立,贵我两国,而来基于本来之关系,日增友好,而汪主席阁下,访问我国,更增亲善,诚不胜同庆之至。”
随后,汪精卫在伪国府礼堂迎接张景惠等人。张景惠在大庭广众之下则继续高唱“为新东亚而迈进”,而在背地里却对汪精卫说:“现在咱们处境困难,日本的处境更难。”
在南京,张景惠还专程拜见了日本“大使”重光,又大谈什么“三国步伐一致”,“建设东亚新秩序对于日本帝国所执处理中国事变方策,实衷心感庆。自此次大东亚战争以来,日本帝国得赫赫之战功,满华两个当对日本帝国遂行之战,倾力协助,亦为日满华三国同相结之好”。
1943年4月8日,周佛海也窜到东北,访问伪满洲国。他的这次出行一开始就不顺利,可谓险象环生。
他在日记中写道:飞机“过山东半岛,山岳甚多,颠(簸)不堪,余乘飞机向未吐过,今则吐矣。有次机急降,人离座位与机顶相碰,后机师谓此机简直坚急(实),如系别机,则直坠地下矣。险哉!”接着,又遇到“新京”降大雪,飞机不得不迫降在大连。
周佛海在东北呆了十余天,不仅在“新京”会见了溥仪、张景惠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而且还赴抚顺、鞍山、哈尔滨等地窜访,所到之处,接二连三地会晤日本关东军高级军官、特务机关头目和伪满军政要员。其間,周佛海不断胡言乱语,比如在观看伪满洲国的所谓“建国忠灵庙”之后,他说:“亦如外到我首都之谒总理陵墓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对于他的东北之行,早在行前的3月9日就说:“余实不愿前往,但影佐盼余一行,赴哈尔滨与渠会谈,商今后大计,此行恐不能免。”所以,他说“来哈,本为晤影佐”。影佐即影佐祯昭,他是日本军部为侵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中国通”,以领导上海日本特务谋略机关“梅机关”并炮制汪精卫傀儡政权、任日本陆军驻汪伪政府首席武官及最高军事顾问而臭名昭著。
1943年4月12日和13日,周佛海三次与此时已是日军第七炮兵司令官的影佐祯昭密谈,并说“来哈之目的已达”。可以看出,他的这次“外交”活动,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局不利和汪伪政权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困境下进行的。其目的无非就是“商今后大计”及此后向汪精卫报告的那样,了解“华北情形和日苏关系在东北之现状”。
在东北各地,周佛海尽管观风景、泡温泉、吃西餐、喝美酒,忙得不亦乐乎,但热热闹闹的场面终究掩盖不了做汉奸的内心恐惧和对前途的无望与哀伤。所以,离开“新京”时,他“与张(景惠)握别,依依不舍,均有难言之隐”;离开哈尔滨时,“于(静远)省长、张(文铸)司令来送,握别时彼此有言语不能形容之情绪”。
周佛海东北之行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战屡败,已是穷途末路。而日本卵翼下的各个汉奸傀儡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再也打不起精神搞什么“外交”活动、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戏了。
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承认最终也达到了“明示”的程度
除日本外,苏联是和中国东北地区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一部中国东北的近代史就是日俄(苏)两国在东北相互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两强侵略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然而,苏联的对华政策很快从《第一次对华宣言》后退,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实际上已经被苏联“继承”。中国地方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的计划也失败了。
日本在扶植伪满洲国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国东北“门户开放”,只是为了消除欧美列强的疑虑。其实,日本更在乎苏联的反应。
1932年1月28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会见了中东铁路苏方副理事长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向苏联方面提出借用中东铁路运送日军北上的请求。
1月29日,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拜会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
1月30日,土肥原贤二会晤了中东铁路中方副理事长李绍庚。经过多方斡旋,日军得以利用中东铁路,在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接下来,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态度就成了日苏关系的一个焦点。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一直是妥协多于冲突。正如前文满铁调查部提出的报告所说,日本希望促成苏联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是“南北对峙”。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苏联不可能放弃在“北满”的利益,又不可能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默认伪满洲国的存在,换取日本对苏联在“北满”利益的承认。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频繁地和苏联方面接触。1932年5月26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致外务大臣斋藤的电报表明,苏联驻哈尔滨代理“总领事”已经有意承认伪满洲国“领事”驻在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电报称:“本国(苏联)政府已有回训,承认满洲国任命的满洲国人领事及日本人副领事驻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同时,亦有承认满洲国领事驻在赤塔、伯力、海参崴之意向。”在国际法上,接受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就是对该国的承认。苏联已经在承认伪满洲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日本随即开始为伪满制定领事派遣规则,准备正式派遣伪满驻苏联“领事”。伪满洲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领事”于当年9月正式“赴任”。1932年9月16日,日本驻长春代理“领事”田中正一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满洲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领事一行预定于18日从当地出发途经清津和海参崴赴任,而苏联方面已经在领事、副领事和书记生的护照上签字,两名雇员也担负着公务,并承认在赤塔、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设置领事馆,对于满洲国方面新提出的在维尔钦斯克、尼库里斯克两地设置领事馆要求(苏联方面在满洲国内已设有6处领事馆,据此,基于相互主义提出此要求)也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表示要向莫斯科请示此事。上述苏联方面承认设置领事馆及发给签证一事,可被视为苏联方面在事实上默认满洲国。”
1932年正值“十月革命”15周年,一向标榜反共的日本,竟然破例派出驻国际联盟外交代表松冈洋右赴苏,参加11月7日的纪念活动。松冈洋右此行的目的是就承认伪满洲国等问题与苏联斡旋。
访苏期间,松冈洋右表示:“本人此次出国所负使命,乃向国联解释日本政府对于李顿报告书所持态度。吾人相信满洲国政府之成立,将为稳定及廓清目前局面之元素,远东和平,以利赖之。邻近中国,犹在无政府统治之下,而满洲新国之进步,日益显著,满洲国果能树立统一平等和平之模范,以便中国之追随,则此种变动,当为日本首先所欢迎。吾人决定在此(莫斯科)多住数日,俾能参加苏联共和国十五周年纪念。”
为达到外交目的,松冈洋右极力制造两国虚幻的友好气氛,他声称:“日本侨民常受满洲中国救国军之包围,幸得苏俄政府,同情援助,本人愿乘此行之便,向苏俄正、副外交委员长李维洛夫与加拉罕二氏,深致谢忱。”
在与苏联互派“领事”的问题上,伪满洲国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紧缩在东北的外交人员,只保留了哈尔滨“总领事馆”和驻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三处“领事馆”。伪满洲国最终只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设置了“领事馆”,对其他地方,苏联没有应允。1938年以后,苏聯再次紧缩外交人员,只保留了哈尔滨和满洲里两个“领事馆”。
除互派“领事”外,苏联还与伪满洲国签订了多项协定。1934年6月,缔结《满苏邮政联络协定》;9月4日,缔结《满苏水域航道协定》。这在国际法上都属于对“国家”的承认。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特别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由默认变明示,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换取了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国际联盟:“我们中出了叛徒”
伪满洲国成立时,联合国还不存在。维持国际秩序的政府间组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日本吞并东北三省后,中国即将此事上告国际联盟。1932年初,国际联盟派出以英国贵族、前孟加拉总督李顿伯爵为首的代表团前往东北,调查认定伪满洲国政权并非日本方面所宣称的“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运动”,其背景“一为日本军队之驻在,一为日本文武官员之活动”。9月,李顿调查团在北平公布报告书,提出“满洲将交还于中国”。
1933年2月,国际联盟根据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进行投票,以42国赞成、1国弃权、1国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唯一的1票反对来自日本,1票弃权则来自亚洲仅有的几个独立国家之一、一直同日本交好的暹罗(今泰国)。
投票之后,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也在6月发布《不承认满洲国办法》予以反击,向各成员国提出拒绝伪满洲国政权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团体、拒签护照等七项要求。
日本历史学者安部博纯指出,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目的是“摆脱中国和支援中国的小国集团的牵制,取得‘自由,通过对列强的直接交易,诱使他们采取绥靖政策”。但是,紧跟日本之后第二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却正是一个小国——萨尔瓦多,以至于国际联盟的一些代表惊呼:“我们中出了叛徒!”
萨尔瓦多是一个1841年才独立的北美洲农业国家,面积2万平方公里,当时由军人出身的独裁总统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统治。1934年5月21日,萨尔瓦多驻日本东京总领事通知伪满洲国“驻日公使”,该国已在3月3日宣布承认“满洲帝国”。消息传到中国,国民政府极为愤慨,指责萨尔瓦多身为国际联盟成员“不独违反国际信义,抑且触犯国际盟约”。
溥仪对萨尔瓦多从此有了特别好感。1941年10月,他还有过随萨尔瓦多使团逃离东北,摆脱日本人控制的想法。伪满洲国政府为了维持这个新朋友,也不惜成本大批进口其唯一特产咖啡豆,甚至由伪满洲国“外交部”官员亲自包装和推销。伪满洲国“外交官”宋淇涵后来回忆:“大家笑着说:各国都像这样来承认,外交部员变为洋商店员了。”
萨尔瓦多与伪满洲国“建交”的缘起,始于一个德国记者对溥仪的采访。尽管作为傀儡,但溥仪也希望世界承认“满洲国”是一个国家,不被承认的尴尬也困扰着他,德国记者捕捉到了这一点。这篇报道发出后两个月,萨尔瓦多表示愿意与伪满洲国“建交”。原来,当时萨尔瓦多的总统马丁内斯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为了报复,他公然违抗国际联盟,选择与伪满洲国“建交”。萨尔瓦多不仅不被人熟知,其与伪满洲国的“建交”也是一场闹剧。
萨尔瓦多和伪满洲国“建交”后,双方并未互设外交机构,一直到1939年,才由伪满洲国指定长春工商会副会长王荆山为萨尔瓦多驻伪满洲国“名誉领事”,萨尔瓦多驻伪满领事馆的牌子就挂在王荆山的裕昌源公司门前。王荆山既没见过萨尔瓦多人,萨尔瓦多人也没到过长春。对等的是,伪满洲国也通过日本的驻外机构,在萨尔瓦多找了一个叫拉法尔阿兹的人,担任伪满洲国驻萨尔瓦多名誉“领事”。在这场闹剧中,可悲的是王荆山,他在长春工商界很有名气,对长春工商和教育做出过很大贡献,却因此身败名裂。
萨尔瓦多的行为,属于明示承认伪满洲国,而默示承认者同样大有人在。
哈尔滨外国侨民汇聚,英、美、法、德、日、苏联等各国均设有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以保护本国侨民利益。根据国际联盟的《不承认满洲国办法》,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只是领事馆在继续工作。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习惯,外交关系并不等同于领事关系,断绝外交关系也不等于断绝领事关系。只要侨民在,领事馆就有必要继续存在。但双方如互设领事馆,就会被认为是默认对方为一个“国家”。
首先采用这一方法对伪满洲国作出承认的是苏联。在苏联之后,波兰也采取默示方式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6月,波兰驻日大使开始接触伪满洲国的“驻日公使”丁士源,之后往来逐渐增加。1938年10月,波兰接待了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韩云阶率领的访欧使团,双方签订经济互惠协定,随后又同意伪满洲国在波兰开设“领事馆”。
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外交承认与事实承认之间形式复杂、关系微妙,自然存在关系模糊的国家。梵蒂冈在1934年委派“吉林代牧区宗座代牧”法国人高德惠负责“本教在满洲国境内各教区以与满洲国政府接洽关于天主教会一切事宜”。另一个北美洲小国多米尼加,该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连任之后,时任伪满洲国“外交总长”的谢介石致函祝贺,对方于1935年3月回函致谢。这两国是否属于承认伪满洲国一直存在争议,1942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中两者均未列名邦交。
有意思的是,1933年国际联盟会议上唯一的弃权国暹罗,却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际,才承认了伪满洲国。
德王三次“访满”:伪满与蒙古伪政权之间的傀儡“外交”
1936年2月,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因内蒙古地区脱离中国与日本进行西进的意图不谋而合,日本关东军给予伪蒙古军政府以支持。关东军希望借此以内蒙古地区切断中国与外蒙的接触,得以保障伪满的安全。
受日本政策的影响,伪满洲国于5月20日制定《指导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针》。在该方针中,伪满洲国表示:“对于国外的蒙古民族的指导,唯有依存日本,与满洲国保持亲善关系。支持现蒙古军政府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使其成为国外蒙古民族的经略基石,逐渐向新疆方面扩大。但不允许国内蒙古民族的离满解体运动。”
从此方针中“支持以蒙古军政府为中心的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的表述可以看出,伪满洲国对待这种分裂行为是支持的,但需建立在亲日亲满态度的前提下,这完全是遵从于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殖民系统的意愿。
在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其总裁德王(内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的简称)听从日本的建议与伪满缔结协定,德王的第一次“访满”活动就此开始。
德王等人分乘两架飞机到达“新京”,先后访问板垣征四郎、张景惠、张燕卿等人,就伪满与伪蒙之间缔结协定事项进行会议商讨,过程中伪满与伪蒙双方仅就“军事问题”产生争议,争议的核心是伪满支援伪蒙后何时撤军问题。
其实,关于何时撤军这个问题,决定权最终在于关东军而非伪蒙与伪满双方。最终双方“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满蒙协定”的签订表明伪满与伪蒙确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开始进行更为密切的“外交”往来。
“满蒙协定”签订后,德王又会见了溥仪。德王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蒙古贵族,传统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他本人在自述中曾谈及:“我年轻时期,因受封建社会遗毒很深,忠君思想至为浓厚。但我承袭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之后,已入民国时代,无君可忠,就把忠君思想寄托在溥仪的身上。”
此前在天津,德王曾拜访过溥仪,此次访满缔结协定本来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但由于德王的“忠君情结”,见到溥仪时仍行跪拜礼。德王回忆这次会见时说:“但念过去的关系,对溥仪个人仍愿以君上事之,以臣属之礼相见。因此,当我单独见到溥仪时,还是行了叩拜礼。”
而后两人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此次“访满”之行的最后,德王还参观了兵工厂并到大连参观访问。德王的“忠君情结”被日本人得知,日本希望借此拉拢德王,以便于日本更好地控制伪蒙,于是便有了德王第二次访问伪满。
德王被告知溥仪将封其为亲王,最终定为“武德亲王”。伪蒙汉奸金永昌表示:“封为武德亲王最适宜,因为武是采取成吉思汗圣武皇帝的武字;德是采取德王的德字,把武德二字结合起来,是表示德王继承成吉思汗伟业的意思,一定适合德王的胃口。”
日本也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就有了德王在自传中所言:“溥仪又召见我,亲自授予武德亲王《钦任状》,我即拜领接受,表示谢恩。”
而此《钦任状》也有明显的日本操纵印迹,德王在描述这个《钦任状》时表示:“我返寓后,仔细看看这个《钦任状》,上面还有溥仪的署名,我很奇怪,怎么皇帝封号还自己署名呢?认为不合前清封王只盖大印,皇帝不署名的惯例,足见这个不伦不类的《钦任状》是出于日本人的指使,不是溥仪近臣的主意。”
日本此做法的目的一是拉拢德王,二是密切伪满与伪蒙的关系,显然加强双方的联系能够辅助日本建立其所希望的殖民体系,也有助于在表面上形成双方“独立国家”间的“外交”假象。
德王第三次“访满”正值伪满“建国”10周年之际。德王此次“访满”的目的一是参加伪满“建国”10周年活动,二是对伪满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德王等人于1942年4月21日到达“新京”,稍事休息后会见记者,并发表有关于此次“访满”的声明。第二天,溥仪正式接见德王,德王也在此次与溥仪的会见过程中,表达了代表伪蒙政权统治下的民众对伪满洲国给予“支援”的感谢之情。
下午,德王拜访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创建以来对关东军难以计数的支援的深深感谢”。接下来,德王又拜访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
此次“访满”于24日结束,德王随即返回张家口。伪满方面为答谢德王的来访,于1942年6月派遣于琛澂等11人进行为期三天的“访蒙”活动。
代表团于6月9日到达张家口,第二天受到德王的接见,李守信与大桥忠一均出席,当晚德王宴请伪满代表团一行人,于琛澂等人于11日访问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后返回“新京”。
德王的三次“访满”每次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却均是在日本授意下进行的,所谓的伪满与伪蒙之间的“外交”活动不过是遵从日本的意愿,两傀儡政权相配合出演的一场闹剧而已。
1942年秋,伪蒙还派遣了50余人的大型代表团前往“新京”访问。代表团“以‘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为团长、‘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上将)为副团长”。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被日本视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所以,在伪蒙“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在日本授意下,伪满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伪满洲国就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获得援助这一事实曾吹嘘道:“该政府建立以来始终受到满洲国的仗义援助,并且对于关东军的深厚友谊支援,蒙疆全体官民呈現出深深的感谢之情。”
除在物质方面的供给,伪满派遣大量人员到伪蒙担任政府中重要职位。
在扶植伪蒙政权方面,早在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时,就与关东军有一份交换公文,其中第二条规定:“本委员会最高顾问、参议、顾问及委员会职员中主要者,请由贵军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充当。三政权内日满系顾问亦参照上述内容。”
这份秘密文件无疑是将人员任命的权力完全交给关东军,即把实际权力转让,其规定和《溥仪致本庄书》全无两样,均是直接交出核心权力。可见,日本在建立各个伪政权的方式上所采取的策略大抵一致,因此,这些伪政权之间的联系被日本控制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略有不同的是,由“日满两国”人员担任伪蒙疆联合委员会重要官员,伪满在伪蒙政权运行过程中受日本安排担任重要角色。
在日本掌握人员任命权力后,将伪满人员派至伪蒙政权中进行统治:“就最高顾问而言:首任金井章次原为伪滨江省次长;第二任大桥忠一原为伪满参议、伪外交部次长,第三任神吉正一原为伪满间岛省省长。”
除最高顾问外,曾在伪满任职的人员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担任着其他重要职位。
这些人员有着丰富的统治伪满的经验,他们的到来,便于将伪满制度套用于伪蒙疆政权,从而维护侵略者的统治。
伪满与伪蒙之间的“外交”往来,虽涉及双方共同签订的协定与条约,但纵观两伪政权“外交”往来活动,不难看到双方的基本目标一致,即服从日本对于傀儡政权的控制;双方对于彼此地位的设定一致,即同一宗主国控制下的“盟友”,对于彼此要相互“扶持”及“提携”。伪蒙政权的元首德王三次访问伪满,足以看出伪蒙对于同伪满“外交”关系的重视程度。双方的“外交”往来频繁程度与涉及的内容,比伪满同伪冀东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更为广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失败,那些轴心盟友和傀儡盟友也陆续消失了
拥有独立的外交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标志,伪满洲国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傀儡政权,但日本也要将其装扮成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的样子,于是,伪满洲国“外交部”就应运而生了。但尴尬的是,这个“外交部”在最初的五年间几乎无事可办。
从1932年3月9日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是伪满洲国政权的“国家机关”形成和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伪满洲国各部的业务不断发展,人员、机构也日益膨胀,但唯一没有起色的就是“外交部”,它五年间几乎没有任何发展。1937年,伪满政府对“中央机构”进行大规模整编,将“外交部”降格为隶属于伪国务院的外务局。
德国、意大利两国与日本结成轴心国联盟,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德、意两国却对伪满洲国不置可否,在1933年的国际联盟会议上还投了反对票,到1937年之后两国才先后承认伪满洲国,其间历程颇为曲折。
以德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中国攻占了德国建立的租界城市青岛,在太平洋还占领了原由德国支配的几个小岛,使德国外交界始终存在对日敌视情绪。以至于纳粹党登台后虽然主张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关系,外交界却建议以承认伪满洲国为价码,和日本讨价还价一番。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便明确表示,伪满洲国是“德国可以用来从日本那里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唯一王牌”。
与此同时,德国对华贸易总额却一直在攀升。到1931年,德国对华贸易总额达到3.57亿马克,是对日贸易总额的两倍。外交和经贸往来上,德国同时与敌对的中日两国密切交往,场面十分奇怪。一方面,德国与日本在国际关系上不断走近,1936年11月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了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德国与中国仍然保持军事往来,中国从德国采购大批军事装备,还聘请德国军官训练抗日部队。
这种情况与德国正在积极备战,对中国的钨、锑等稀有金属有迫切需求关系匪浅。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德国仍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的意思。德国政府不但一度拒绝日本关于从中国军队中撤出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还出马担任了中日停战的中间人。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德国最终选择倒向日本。1938年5月,德国与伪满洲国在柏林签订条约,互相承认。而意大利在1937年11月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后已经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政府虽然向两国表示强烈抗议,但也无济于事。
有了轴心国这个大靠山,伪满洲国的朋友圈突然热闹了起来。在德意日之外加入轴心国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西班牙、芬兰、暹罗,以及轴心国集团扶持的一批傀儡政权,如维希法国、“自由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等,前后有超过20个政权和伪满洲国互相承认。
到1940年初,伪满洲国除了在日本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设立了“公使馆”,其他政权或设“领事馆”,或有代表处,俨然拥有了一个热闹朋友圈。。
随着业务的逐渐繁忙,1942年4月20日,偽满洲国“国务院外务局”又升格为“外交部”。在“新京”设立使馆的有日、德、意、暹罗和汪伪政权,伪满洲国的一切外事活动,均由日本指挥伪满“国务院”及其“外交部”办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扩大和同盟国的节节胜利,伪满洲国的朋友圈也在发生剧烈变化。波兰在1939年亡国之后,由流亡英国的西科尔斯基政府于1942年2月宣布取消承认伪满洲国。最早承认伪满洲国的萨尔瓦多在1941年加入了同盟国,随之停止了与伪满的“外交关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失败,那些轴心盟友和傀儡盟友也陆续消失了。到了1945年8月,伪满洲国随着日本战败而垮台,它的整个朋友圈也随之灰飞烟灭。将它消灭的,正是曾“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苏联。★
下期预告:伪满十三年(三)——伪满高官的复杂面孔
(责编/闻立 责校/陈小婷 来源/《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著,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1版;《抗战时期的伪政权》,费正、李作民、张家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伪满洲国对外关系研究》,王文锋/文,《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1期;《伪满外交官的回忆》,替夫、金淑梅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