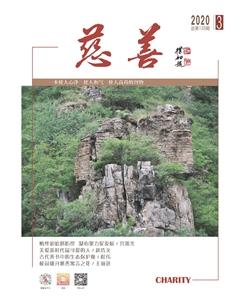生活中的美
周佩红
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我看来深奥复杂。所以它才能发展成为一门学问:美学。记得在大学听美学课时,大部分时间总听得脑子昏昏沉沉,只有当一位教师搬出“柔滑的绸缎”和“挺括的涤纶”做比喻时,才因惊讶而打起了精神。说美是一种存在,一种精神,一种创造,都可以,不过这样的归纳和界定最好只在做学问时出现,倘若生活中也如此,我会觉得累。对于我,生活中的美,往往只是一种感觉,纯属私人,是无须经过逻辑和规范判定的。
譬如说,走在大街上,看到在一大群环佩叮当的时髦女子后面,穿纯棉素淡衣裙的一个姑娘不紧不慢地走着,眉宇间满溢着温柔的自信,眼前就会霍然一亮,会忍不住多看她几眼。这是街头少见的风景画,让人感到赏心悦目。
可是别让我在公共汽车上再碰到她。我怕座位上的她会头一扭,脸一别,无视老人或孕妇婴孩在她身旁艰难站立。有时,听打扮悦目的小姐开口说话也是一种灾难。那样的尖声利语,肆无忌惮地大笑,或者是委琐粗俗的言辞,常使我怀疑这声音是不是出自那美丽的外表。
我在一个称得上富丽堂皇的店堂里买东西。眼前的营业员小姐拧起一对柳眉,表清淡漠地看着我。说实话她长相不坏,但脂粉涂得太厚,眉眼画得太浓,唇膏上得太艳。这使我难以判断她的真实年龄。不过,这样的打扮一定出自她的某种良好愿望,她必以为这是妥帖的,美的。美本来并无统一标准。我请她把柜台内的一盒食品拿给我。她拿了,手指习惯地在算盘上拨出钱款数。我又请她再拿其他两种。她也拿了,但脸色沉下来。我接着请她调换其中一种,然后一并算钱。她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道:“看准再说话!”语气急促锐利,像在训斥犯错误的小孩。她的眉头皱在一起,红红的嘴唇向下撇出两条线。我看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我付了钱,离开她的柜台。她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开。也许我的挑选使她厌烦。也许是别的什么事使她不开心。这很难深究。我也感到了不快。她紧皱的眉头和下撇的红唇使她变得很难看。这必是她在晨妆时始料不及的。那时她的本意是想让自己更美的。
不過,倘若她对她的亲人和好友温柔地一笑,轻轻地说话,那么春风一般的和蔼亲切必会柔化她脸上刚硬刺目的化妆效果,她必会在那一刻美丽无比。
是的,美有时就是那么娇嫩难得,犹如惊鸿一瞥,昙花一现,远不在人的刻意设计中,而是在一种发自本心的自然流露中散发,又消逝。
我的孩子从学校里奔出来,拉住我的手。他圆滚滚的脑袋在蒸发热气。几滴汗珠在他脏乎乎的脸上淌下来,变成一道道黑辙。放学的队伍潮水般从他身后涌来,夹带着一股顽皮孩子特有的带汗酸气、混含着尘土味的气息。我喜欢闻到这样的气息。这些小顽童都像是刚刚冲锋陷阵过的士兵。儿子伸出的手是黑的,有点黏。“他刚才在操场上皮得打滚呢!”一个白裙黑辫的干净的小女孩向我“告状”。我拍打掉儿子身上的草屑和灰尘,俯下身,使劲嗅了嗅他的头发。一双清亮健康的孩子的眼睛忽然离我很近,美得令人炫目。
在远方的一座城市,两个初次相见的朋友送我去火车站。走之前他们请我在街角的小吃铺吃水饺油饼。再以前他们曾在一家豪华餐厅请我吃过鲨鱼皮、海蛏之类古怪的海鲜。这两次在我看来没有太大的不同。小吃铺是一间极简陋的低矮平房,煤烟和油气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尽量不说话。我一直在看屋子另一角面饼师傅的操作:揉面,做饼,烘烤。仿佛我离去前的心情也被这样地搓来揉去。然后我和一个朋友去黑乎乎的灶间催促快些煮水饺,免得误了火车。回到店堂,远远只看到另一个朋友坐在油腻的餐桌边,低垂着头,手里紧紧握住一副手套,像握着一双有形的手。他身上那件的风衣不再显得沉重刻板。
我们去京城一个著名的公园玩。我的凉鞋有一只鞋垫出了点毛病,总往后移。走不了几步路我就要停住,把它往原位放好。这分散了我观景的兴致。出了公园,同去的一个朋友骑车拐上马路,找到一个鞋匠摊,再把我带过去。朋友指指我脚上的鞋,然后示意我坐下。鞋匠师傅用两枚铁钉就解决了我鞋上的问题。朋友自己的鞋襻儿也得到了修理,它们没坏,只是快松了。也许朋友是为了免除我不必要的尴尬。他看上去总是大大咧咧的,和我并不熟。坐在鞋摊前的小马扎上,我想起他写过的一些纯粹而优美的诗句。鞋摊上大大小小的铁钉放了一地,还有五颜六色的模样可笑的鞋跟。西斜的阳光柔和均匀地洒在它们之上。朋友靠在一棵行道树上,脸转向一边。这是个毫无诗意的黄昏,但我受到了感动。
生活常就是这样,在芜杂和糟糕中隐藏了一点可爱的、令人心颤的东西。我将它们笼统地称为美。我没有,也不想把它们放到更深的背景中去探究。深究的结果,不是美的僵化,就是美的失落。这都将违背活生生的美之初衷。而我原本记住它们,只是因为它们是复杂且普通的生活土壤上罕见的花朵,虽然将会或已然枯萎,但带给我的惊喜、希望以及力量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