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三种破坏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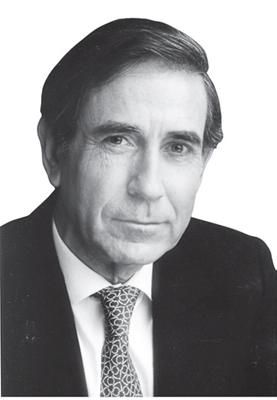
索洛莫·本·阿米
早在人员和商品实现不停顿地全球流动以前,疾病流行就是人类文明中所无可逃避的一种特性。但由此所产生的悲剧往往也与一线希望相伴相生,因为常被认为是充满神秘感的历史性“元事件”,大规模的疾病暴发往往能够破坏旧的信仰和发展路径,预示着人类的一些行事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不过,新冠疫情可能打破这种既有模式。
在许多方面,这场疫情看上去和之前发生过的疫情并无二样。首先,无论可以预见与否,疫情暴发往往使政府措手不及,各国政府也无法迅速、果断地做出应对。
面对疫情暴发,如果领导人们缺乏远见,民众往往就只剩下社交隔离这一种防御手段。这次疫情期间,封锁等社会隔离政策同样阻止人们探望垂死的亲人,同时也颠覆了葬礼的传统。而倾向于采用试验性的保守治疗,是另一个相似之处。
科研人员已经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这种疾病,但在我们等待治疗方法或疫苗时,现有的一些抗病毒药物,例如长期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正在接受测试,但结果却不尽相同。其中,羟化氯喹因为服药患者显示出心脏相关的并发症迹象而引发关注。
与此同时,一些“神药”也应运而生。通过社交媒体,江湖骗子发布虚假且危险的声明,提出吸食可卡因、饮用漂白水等各种可以预防新冠病毒的方法。在没有任何科学测试结果支持的情况下,特朗普本人则一直在吹捧羟化氯喹“有可能扭转局面”。这还使得一对夫妇进行自我治疗的尝试,结果是丈夫丧生,妻子侥幸生还。
此外,疫病流行不仅会破坏经济,而且突出了社会不平等,并滋生“阴谋论”,从而极大加深了人们对现状的不信任。疾病可能并不區分贫富,但因为生活条件不同,疫情还是更容易影响贫困和边缘化人口。
伊朗政府控制的媒体警告民众,不要使用以色列科学家研制的任何疫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出版物,称新冠病毒为以色列的生物武器。奥地利、瑞士和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指责犹太金融家和慈善家乔治·索罗斯,认为索罗斯希望借此削减世界人口并且从疫苗当中获利。
尽管和以往的疫情相比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新冠疫情又有其标志性的独特之处:它不太可能颠覆原有的秩序。历史上,安东尼和查士丁尼瘟疫促成了基督教在整个欧洲的传播;而黑死病则促使人们不那么信仰宗教,而是从更人性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西班牙流感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反帝国主义抗议;在死亡人数高达成百上千万人的印度,疫情刺激了独立运动。
相比之下,当前的这场疫情更有可能强化本已存在的三种破坏性趋势:去全球化、单边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几乎从疫情暴发开始,降低对全球价值链依赖的呼声就高涨,尽管早在危机前这种呼声就已经引起了注意。欧盟在制定共同战略上滞缓,再次暴露了这一区域组织的固有分裂。特朗普则决定,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
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表明,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所主导的全球秩序,是与人类的和平、安全相冲突的。从此次疫情中也能明显看出,民族国家与超国家机构之间迫切需要实现新的平衡。否则,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杀伤只会越来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