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
袁一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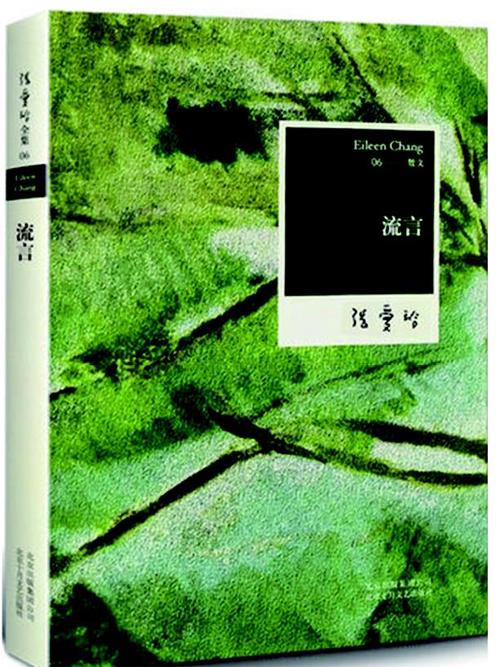
我們的世界很小,哪怕走了很久很久,可能也只能停留在原点。
我想在你的身边种上小小一棵草,它很小,却足够长出一本本书来,在风雨欲来时,把你安置在它们的荫蔽里。
我会给你唱情歌,也会给你讲故事,让你享受我的爱也享受清风。
请让我好好地珍重你。
提起张爱玲,除却她那“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头衔与绮丽绝艳的饮泣文字,为人在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胡兰成的一段情。
1945年,话剧《倾城之恋》继续上演,随笔散文集《流言》紧随其后出版。在《有女同车》里,张爱玲用一种漫画般的语气描述了两个女人在车里谈论自己的丈夫与孩子。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她的一番剖析,其实带了点儿新潮女性检视自我的成熟与自省。
然而她到底再清明通透,写文下笔时再如何伪装成冷眼的旁观者与看客,到底不知情地入了戏,成了梦中人。
因此那句十分有名的“噢,你也在这里吗?”说的其实是一种人间理想,不,是人间妄想。
更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仅仅符合了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种情感波纹不仅充斥于上世纪40年代的街巷生息里,同样,我相信,也影响着现今与后世行走于天地间的人们。
我们说张爱玲遣词造句像用艺术来描摹艺术,“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可我一天不能克服那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流动鲜活,是童言童语似的快活。
正如常常有人将冰心与林徽因相比,与张爱玲一同置于天平两端的,则是三毛。因着文风处事,有人大大咧咧地一挥手一张口,便将二人概括为一句诗:“一个是孤灯落碎花,一个辛苦向天涯。”
道三毛是飒爽绝唱,张则是清绝伶仃。
不偏袒谁,但你倘若把文卷翻来覆去地读,拿心去尝试触碰人生与隽永,你会发现,其实她二人,无论是内里还是外里皆是反过来的。
读《流言》的期间,心与文字一般悲怆却坦然,曾在雨夜里撑着伞行走在矮矮的路灯下,拿伞沿去遮了头顶的光,在陆离的光帘里剩下的,则是细碎纠缠的雨丝。
你会懂她的童年,懂她的傲气与自怜,懂她的孤勇与胆怯,也会懂她的别致与生而不凡。
她不比寻常人家,曾外祖父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晚清名臣李鸿章——身为名门之后,却面对着日渐衰微的旧式家族,父亲吸毒嫖妓,母亲漂泊任性,心里不感到点儿无根无依的悲怆是难的。
但圈圈绕绕再说回来,比起在评论家笔下一生都敏感且苍凉的张爱玲,我更喜欢那位在1942年至1945年的张爱玲。那时的她什么都有,爱情、名声、地位、思想,最真,也最可爱,周遭充斥的全是再普通不过的纯真。
《流言》诞生在那儿,也死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