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走遍世界回到香港

徐学

也斯
也斯去世好几年了,我对香港文学的研究也“退居二线”,但每逢想起香港,想起诗歌和摄影,想起红酒和食物,或者仅仅是在寂寞的时候,就会去书架上找他的书,翻开来看一看。最近疫情严重,打开那首《非典时期的情诗》,我仿佛又听到他粤腔粤调的吟诵:“喉咙在发痒/忍住了许多睡不着的夜睌/不敢咳出来,怕惹起周围恐慌的目光/脚步沓杂/安抚惊蛰的季节……/在隔离的病床上想念彼此/墙外的人目光想穿透墙壁/看见墙内人模糊的形像……”
跟着也斯去行街
30年前初入港岛,我是一个内地客,自封闭且淳朴之地而来,觉得香港复杂又暧昧,一道道嘈杂与速变的街景,一群群匆匆与寂寞的人群,一重重混杂又挤迫的空间,说它可爱,是客气;说它可怕,却又自有韵味。我想到张爱玲说的那段话,“我喜欢听市声。比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聽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左右徘徊之时,是也斯的文字让我靠近了香港。
一天,我在岭南学院图书馆随意翻书,找到一本《雷声与蝉鸣》,这是也斯在16岁到28岁的诗作合集,清新可人。他写雷声中的蝉鸣,自述情怀:“在这些新扬起的声音中保持自己的声音/蝉鸣仍是不绝的坚持。”诗集中有一辑《香港》,收入了《傍晚时,路经都爹利街》《五月廿八日在柴湾坟场》《寒夜,电车厂,罗素街》《拆建中的摩啰街》等多篇描绘香港地景的诗作。于是,我可以在诗里和他漫步在多尘的柏油路上,走到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对岸轮胎厂冒出漫天枭枭黑云,如同火灾;走到罗素街的水果摊和干货店,再看看鲗鱼涌的大排档和花店……
读完意犹未尽,我又去找了也斯的摄影集和散文集,里面有美丑参半的九龙城寨、鬼魅的湾仔、忧郁的兰桂坊、春秧街市附近张爱玲等文人曾经的住所,还有太古广场的时装店、竹节般矗立的中银大楼,尤其是汇丰银行新厦这样的后现代建筑取代了过去稳重对称的旧貌……也斯的城市观照,不甘浪漫沉醉与粉饰美化,也不愿肆意批判和痛加鞭击,他只是亲近本土日常,从平凡风物中撷取意象,以白描的方式实录生活,尽显香港的浮华与苍凉、丰富与局促。“我沉浸于某个瞬间,捡拾某个意向,可能是觉得在无人注意的东西那里,也有值得留神的东西。写几个字,拍摄一幅肖像,也不过是想:那些小路旁边的事物,那些没有放大登上报刊头版的人,也许有他们值得听听的故事呢!”多年以后,也斯这样评述自己的创作。
“时间过去,我仍是一个旅人”
诗就其根本而言就是乡愁,是一种小小的纵欲,放纵亦是创痛的治愈,有修补破碎的力量,能把失散的涓滴重新导入本源。所以,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但乡在变愁也在变,所以诗人也斯一生都在找寻归乡的路,就像鲁迅《野草》里的过客所说,“从我记得的时候,我就这么走”。

也斯的代表作品:《也斯的香港》《雷声与蝉鸣》《蔬菜的政治》。
也斯最爱香港的乡村景色:“一头牛走过,低鸣/一个女子走过,摹仿它的鸣叫/然后雨再剧密,成为更响亮的声音,但牛仍然站在树下/黑色皮毛反映着湿润的微光/固执的低头吃草/在迷蒙中/某些山形坚持完整的轮廓/生长又生长的枝丫/接受不断的涂抹。”
也斯说:“我和我的影子穿着木屐穿过岁月……不知可不可以跟失去的声音相约。”他穿过岁月到老街,早晨的阳光淡淡的、暖暖的,街口坐着卖水果的老人、修理水喉的老人,好像是小街的守护神。街尾有个小小的垃圾站,后面是一条泊车的小巷,再后面就是山边了。风吹起来,山上绿竹沙沙作响,给人清凉的感觉。
屋村有孩子游玩和晒太阳的空地,但渐渐地,许多空地都划成了车位,在汽车尚未占去的地方,母亲和孩子悠闲地在石凳上坐一个早晨,晒着暖暖的阳光。孩子身上健康的皮肤反衬着阳光的颜色。也斯喜欢这样的悠闲,但也看到孩子的背后是搭着脚手架的大厦,它们像是蒙着阴郁的屏障。
也斯怀着乡愁带着外地友人探访香港乡土,特别是元朗旧墟,这里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围村,有酒家、药铺、商行和传统客栈。废弃渔塭和荒凉的河道旁,还有低矮的铁皮或木板拼装屋…… 他的小说《爱美丽在屯门》女主角爱美丽就出生在元朗大水渠旁。爱美丽的父亲白天去钓鱼,晚上开档卖鱼粥,她“就像元朗仅余的少数自然植物,在毫无规划的发展与地产商不择手段的牟利手段底下,于满天灰尘之下的货柜车残骸之间粗生粗养”。
也斯还带着乡愁走遍大陆和台湾。我尤其喜欢他的散文集《越界的月亮》,卷首他引用的俳句“时间过去,但我仍是一个旅人”出自日本俳圣松尾芭蕉。此书中第一辑《七十年代之旅》是他1976年初游台湾的札记。二十来天,也斯走访许多台湾人文地标和偏乡小村,旅伴是作家西西和吴煦斌。台湾和香港一样,是一个移民社会与难民社会,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人口,从贫瘠渔村农庄迅速发展为繁华的转口港。殖民与移民的身世,造就两地的暧昧特质,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呈现出特有的挣扎和两难。也斯敏锐地攫取了这混沌的事相, 在书中,他赞叹台湾那时存在着朴实人情和田园精神,感慨这些情感和观念在香港曾经有过却已消失。他也喟叹,这些与农业文明并存的文化,因城市化的冷漠而日渐稀薄。
路越走越长,人越见越多,也斯变得能接纳和包容许多此前不太接受的人和事,但有一点没变,就是朝拜缪斯的执着。一如他少年时的诗句:“当人们都睡了, 我们还留下来看星,并且说着,那些常在的云。”
第二辑《时空的漫游》是他的内地人文之旅,从沈从文到苏东坡,他都要慢慢参透、细细体会。看他的游记,想到30年前游船上的我。船行漓江,岸边山头,千变万化似梦如歌,正飘逸出尘,忽听导游喝道,“快看,这是骆驼,那是马”,众人一拥而上,我灵感俱失。也斯亦是如此,看到被导游命名的石头,他总是不以为然,说:“它们像是还在蓬勃生长的生物……是混合而成的新生物,它们汹涌且蠕蠕而动,可以感到内在的呼喊和跃动。”
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
家园外貌被地产商支配,乡土记忆被传媒淹没,走在那些被工业化裹挟而去的香港地区,也斯在不可抑制的乡愁中捡拾光影。文字只是他探索、思考、观看世界的一种方法。“如果我觉得家园变成陌生地,那并不表示所有陌生的异乡都可以轻易变成家园。人的远适异国,正如诗文之翻译成另一种语文,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冒着丧失自己被吞没的危险。”他走遍世界,终于还是立足香港,在大都市的冷漠里,在人情乡土的蜕变中。
没见到也斯前,我已听友人多次提起他,有人赞叹他的才气,有人批评他的尖锐,有人说他是和某派对立的“也派”。见面后,我发现他很和蔼,但说起身世,他又分明处处反叛。他祖籍广东,幼年跟家人来到香港,四岁丧父。香港家长爱把儿女送到英文中学,很少人念中文中学,也斯却偏要上中文中学。到了学校,他却不满意老师古板的教学方法,到了大学又去读英文系。20岁,他开始专栏写作,又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他说,从他的散文开始阅读,会更容易了解他。后来,我果然接到他寄来的散文集,不像别人从右到左竖写题签,他工工整整地从左到右写,前面是敬赠,后面署名“梁秉钧”,这是他的本名。我听说,早期他写散文评论都用也斯,这个笔名由两个虚词组合而成,只有发表诗才用本名“梁秉钧”,后来就一视同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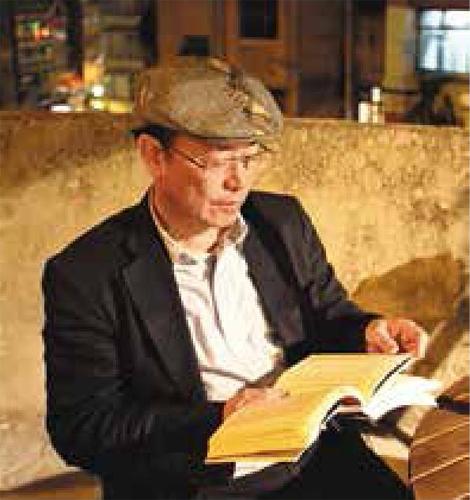
也斯在香港。
路越走越长,人越见越多,也斯变得能接纳和包容许多此前不太接受的人和事,但有一点没变,就是朝拜缪斯的执着。一如他少年时的诗句:“当人们都睡了,我们还留下来看星,并且说着,那些常在的云。”2010年,也斯患上肺癌,2013年辞世。这段时期,他依然行走于艺术世界,在内地,在大陆,在大学的讲堂上,坚持到最后一刻。
也斯喜欢飞的意象,他第一本书题名为《灰鸽早晨的话》(后来再版改为《灰鸽再飞》),这让我常常想起电影《阿飞正传》的独白: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也斯以展翅、拍翼、穿越、頑强抵抗坠落的一生,在香港乃至华人的文学版图上,刻下了绚丽和不屈!
也斯(1948年—2013年)本名梁秉钧,广东新会人,1949年到港,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文化研究等方面均有造诣,著有《雷声与蝉鸣》《灰鸽早晨的话》《蔬菜的政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