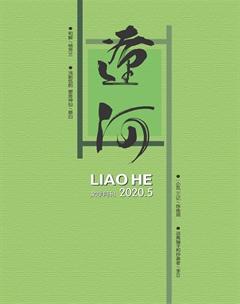一群喜鹊在飞(组章)
胡世远
一群喜鹊在飞
旧年已去,永无归期。
大悲大喜,亦不足挂齿。我亲眼目睹,一片片雪花在阳光的辉映下,从枯黄的叶子上飘落下来。那一刻,我从这白色的花瓣间穿过。
一路上无语。在东陵公园的后山上,十二属相园的小动物雕像被白雪烘托,愈发显得栩栩如生。更有红布条系在上面,红白相间的轻盈,在这春节来临之际,每一丝美好的感觉都值得珍惜。
吵闹着跟随上山的小狗曲奇,在树林间来回穿梭,仿佛在寻找新年的礼物。它的欢快和四周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应,被积雪压着身体的枯草从容自在。
一切好像剧中的场景,或许就是真的,当我们踏进这圣洁之处。我相信,有一片安静是属于我的。我看到的,也只能是局部的画面,事实上,我们从未真正进入过冬天。当一片飞雪像亲人一样扑过来,我还在抱紧昨夜的睡眠。
像往常一样走向春天。风吹过尘世,它留下故事。等待有人记住,等待有人讲述,等待有人倾听。眼前这些上百年上千年的树木,看起来如同一本厚重的书,关于静谧、孤独和归处。
布满绿苔的石头,尚未腐烂。我仰慕树的形象,能够做到物我两忘。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在白雪覆盖中我看见自己。
还有,一群喜鹊在飞。
道路之上
我们到来之前,地面上早有无数双脚印。
此时的凌乱,纠结于开始和结束。神秘的隐喻之中,阳光很轻。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拐角,那些走远的人突然折返,我们和影子重叠在一起。
风一直在刮。那些惊慌的叶子,逃往各自的方向,就像一群人刚刚还聚在一堆,忽然间就渐生凉意。你所遇见的人和事物,每一个都不是多余的。
似乎冥冥之中,我们早已和生命达成默契。当星辰落在酒杯里,在这钟情的土地上,我们像所有的人一样,一次次面对选择和放弃。捉襟见肘的窘境里,柔弱的肩头试图托起落日。就像其它所有的时间,我们不知道风究竟来自哪里。
一片孤零零的白云挂在天空,像在关注大地上每一个被影子追逐的人。容易打折处理的光阴,来自沉默或麻木,来自虚假或禁闭。
失去拐杖之后,我不得不尝试着踉跄前行,只是后来,当我确信自己可以站稳脚跟时,熟悉的道路却消失了。
那么多分岔面前,远方那么近,又那么远。每每回到故乡,我不说话,没有人知道我是回来寻找记忆的人。
无数条道路属于双脚。一份信念,照亮了道路之上,所有的荆棘。
风吹不皱思绪
所有不甘现状的人,多么像你,如此清晰。
在树丛中,像星星,像鸟鸣。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
当寂静回归事物本身,我们的秘密,有时候我喜欢闭上眼睛想。
我知道,风吹不皱思绪。就像空旷的草原,迎来春天。草继续生长,马继续吃草。我慢慢靠近马,仿佛离春天近了点。 辽阔的草原,一片寂静。除了心跳,只有穿过的风声。草儿睁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绿色里,我把自己想象为一阵风,一棵青草,抑或一匹马。
我记得,在童年胆子小走夜路的时候,大人们说,折下桃枝,或拿一截桃木的棒子,就可以避邪。
长大后,落下一个习惯。身上揣着桃木挂件,家里藏着桃木斧头,就这样过去了好多年。
直到有一次,误入桃花深处。
我突然感到,一种恐惧,苍白的脸,仿佛风带走最后的炊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笑容,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整个下午都是晚上,一直在刮风。
而且将要有大风。
思绪坐在一个人的心中,像个婴儿倒立于母亲的子宫。
老槐树
穿过一场场风雨吧!
你和我一樣,都不是瓷器。
你就是一棵树,一棵上了年纪的槐树。该绿时,就绿;该休憩时,休憩。
这辈子,如果不留下世俗的顽疾,也就好了。
都说生活需要存在仪式感。我在你的影子下打坐时,风从旁边刮过去。一些尘埃,爱上了我的身体。
于是我重新变成了宝贝,听到摇篮曲。
以前,我听过隔墙有耳。现在,我坚信地下有人。不同的是,走在路上我不敢发出异样的声音。好在小草葱郁,掩饰了我的担心。
关于命运,或生,或死,或生死之间。这三种想法,就像枝头蹦跳着三只鸟。
我们迎着夕阳而行。风,吹开叶子的嘴唇:“好好活下去!”
——你说。那么多的美好,我们已经错过。
哪怕一片叶子不剩,我也不想,不想就这样被生活的绿色忽略。
我想要的,仅此一点。在一次次闪电中,我愿意
——燃烧自己。
把一只鸟放走
无聊之时,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
似乎自从买回来之后,它就一直在那儿。现在已被灰尘所掩映,书依然是崭新的,灰尘是什么时候的,我不得而知。
现在看来,在此之前,这书根本就不属于我。而灰尘却常常与我相伴,就像随时随地涌出的丑陋的念头。
看来一个人真的需要随身揣面镜子,空闲的时候掏出来,照照自己的脸,不知不觉就有了皱纹。时间久了,变黄的叶子好比时间,是记忆,也是遗忘。
在爱的一面,死亡的另一面,我们抱得很紧。
直到把一只鸟放走,剩下自由的鸟笼,仿佛空旷的老屋星光般般寂静。风刮着一片云彩,飘过大地最高的树木上空。
我们把有梦的男人,比做挖掘机。世界永远是一片青草地。青草还在那里,在记忆的废墟和钟声里,不需要调解。
以玫瑰的刺去想起一些人,有疼痛最好。时间拥有我们,而生活是脆弱的——
余生挤出一些时间,多读书吧。一行行文字就像一盏盏善良的灯笼,它会替你看见,许多正在移动的事物……
当风停下来,安静,来自遥远,来自身边。
命运如雪
在哪里,你我都是异乡人。
当我们还没有从心底爱上脚下这片土地时,每一个时辰都充满着微笑和假想,身体随风而飘摇,看一粒尘埃慢慢落下,用余生交换宁静。
反复无常的春日里,相对于一场“疫情”的举国之灾,阳光显得特别金贵。被困于房间的人群,和按捺不住的心跳,将希望寄予古树之上的红布条,为天地祈福。
天气变暖,去南方猫冬的鸟儿还会陆续飞回来。在适合自己的枝头,唱响完美的歌声。至于它们分别叫什么鸟,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
可贵的,它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至于今天清晨,我坐在临窗的沙发上,怀抱可爱的小狗“曲奇”,任它在我的臂弯安静地熟睡,均匀的呼吸仿佛就是愉快的问候;我望见窗台上盛开的花朵,那些花瓣仿佛就是喜悦的词语。原来我渴望的,竟是这轻盈的幸福。
而这一切,承蒙阳光的恩赐。此刻的景象,如同绿色填满草地,万般温顺。我突然幻想时间就此按下暂停键,我还有大把光阴,为各种意义呈现。
或许命运就该像那厚厚的白雪,白雪象征着包容之善与纯净之美。大地被白雪覆盖之时,我一步一步地往家走,离故乡越来越近,离炊烟越来越近,离童年越来越近。
雪化之后,我又一次变为异乡人。依然走在人间,每条道路还在这里,一如往常。
往前走,继续走。以雪落的方式。
江城有雾
翁筱
最后一班驶向江北的船,是晚上九点。
我们穿过春夜的雨幕向着渡口走去。虽是春天,这个城市的港口却异常阴冷。夜里航班是间隔半小时的,我们打算坐倒数第二班船,上岸后再等末班船过去接我们回江南。
售票处离渡船约500米,途中是露天的。我跟亦老师各撑一把伞,不紧不慢地跟着老李和江小天,也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他俩的谈话。听到有意思处,便用不高不低的嗓音打趣道:可以了可以了,悠着点,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说完,我和亦老师相视而笑。
“舌头倒不会闪了,你的腰可能会,这叫‘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老李回头笑呵呵地看着我说。江小天一旁附和:就是就是。
随着汽笛声响,船从江北渐渐向我们靠近。
乘客们争先恐后地朝船上涌去,就像在武汉封港前赶上汉口江滩往武昌中华路码头的最后一班船。我们也随着匆忙的人群,变得躁动起来,脚步自然而然加快了些。
一上船,我就雀跃着往楼上跑。因为乘客比较少的缘故,楼上的灯并没有随着渡船的前进而改变。它仍旧是黑乎乎一片,我们不说话,也看不见彼此的脸,仿佛空气也是静止的。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近距离的海风似乎并没想象中的那么腥,它只是淡淡的和着初春的细雨,绕着我的鼻尖、耳垂、下巴,还有微动的睫毛。
船到江心,借着南北岸的灯光,整艘船顿时变得明朗起来。
“大诗人李白,人称‘诗仙,一生佳作逾千首。纵观其流芳百世的诗作,‘明月和‘美酒是百用不腻的字眼,他的人生结局也和‘月与‘酒息息相关。”我首先打破沉寂。
“看来是酒成就了‘诗仙李太白,只可惜今晚没有月亮。”江小天接茬。
“据《唐摭言》记载,这酒也毁灭了李太白。所以说,酒是个东西,也不是个东西。”老李摇头感叹。
“中国的汉字真是博大精深,此处这‘东西用得巧用得妙!”江小天伸出大拇指,不无夸张地说。
“话说回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比起李太白,屈原的投江倒是有意义的多。”江小天说。
“屈大夫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相继被楚怀王、楚襄王驱逐,在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汉北期间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依然洋溢著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后被召回,却在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郢都时,带着绝望和悲愤之心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江小天继而说道。
“那投江的爱国文人多了:商朝贤大夫彭咸,北宋丞相江万里,还有唐代著名诗人骆宾王……”说起这历史来,老李那是一套套的。
“阁下简直是一本活的历史名著啊!”这次换我夸张地竖起大拇指,且是左右手都用上了。
“那谁,来首诗吧!”对于这一点,我是满怀期待的。
“呵呵,你以为我们是曹植啊!不过,回去倒真是可以写几首关于咱一线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诗歌。”老李的声音划过上空,瞬间销声匿迹。
“是啊,怎么着也要对回去的这趟末班船有个交代,你们说是不?”我扭头看一眼身边的亦老师和不远处倚着船栏杆的江小天。
“也对,是得有个交代,我们仨傻乎乎被你骗上船,虽不是贼船,那也是船。”亦老师与我并排站在船栏杆旁,没想到一向严谨的他幽默感十足。
“这个提议好!回家后,我通宵完成作业。你俩呢?”我扭头看老李和江小天。两人离我们约有三四米远,从半明半暗的火光判断,两人正猛吸刚点着的烟。
“一言为定,反正写的不比江小天那《封城手札》差就行。”老李说。
“你这是谦虚还是骄傲?不过,我的散文还真不算好。就当是非常时期的一个记录吧。”此时的江小天,是谦虚的。
“武汉封城了。刚刚我们上船时,轮渡码头的大喇叭也喊过几嗓子了。等末班船回去后,就要面临封港了。”老李叹了口气。
“机场、动车站、高速路、国道都即将被封,港口自然也不例外。” 亦老师不无担忧地说。
“封吧,只要能控制疫情的蔓延。一切我配合。”江小天接话。
“一起加油,为自己,为武汉,为中国。”大家异口同声道。
“喂,前面那仨,我们能不能不去江北呀?我很累,不想走了。”渡船靠岸。封港的消息让我有了莫名的紧迫感。
“再不走,我们拖你了!”江小天见我没上岸,便催我。
他似乎永远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即便前方的路很难走。
“上不上岸都是江北,更何况来都来了,上去逛逛呗!”江小天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江北的夜景很美的,接下来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来了。”老李接茬。
“走吧,一起!”亦老师做了个Lets go的手势。
“你们去好了,要封港了,我就在船上等你们吧。”我站起来朝岸上的他们挥手。
“你一个人坐船回去也可以,包我就先背走了。”老李不怀好意地说。这才反应过来,我的背包还被老李拽着,于是也顾不上地滑,拔腿就往岸上跑。
“小姑娘,雨伞掉了。”船老大在身后喊,追上来将雨伞递给我。
“哦,谢谢大伯。”
“嘴挺甜,魂没有,下次要是把人丢船上就好喽,大伯捡回家去。”
小城市的人很会自得其乐,封港也好,封城也罢。或许,是追求自由的心跳动得没那么疯狂吧!
夜晚的江北,并没有老李说的那么让人魂牵梦绕。随着春节的到来,老李曾经工作过的厂子早已大门紧闭。似乎,这里并不欢迎我们。
“回望,是一种伤。”老李悠悠地说。
“不过,江北的街道宽了许多,地面也变得干净,这证明老百姓的素质越来越好了。”老李边走边看边念叨着,仿若回到了阔别数年的家。
回江南的渡船上,江小天举着手机朝江北“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你是准备发朋友圈吗?”我问。
“来时发过了。”
将近两小时没看微信,朋友圈多了好几十条新消息,均是新浪、网易、搜狐、腾讯、澎湃等网站发布的“疫情最新信息”,以及微友们转发的各种真假难辨的链接。人生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像人类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幸福?背叛?死亡?多少年后,当我们回想多年前在封港前结伴夜游的此刻,又该作何感想?
前段日子,有位诗人朋友走了,离开了这个在他眼里“肮脏”的世界,而他所向往的那个世界:没有焦虑,没有欺骗,不会有苦涩和罪恶。
之前,我们都没有发现他也有抑郁症,跟海子一样:在海子的大量诗作中(《太阳·诗剧》和他至今未发表过的长诗《太阳·断头篇》等),他反复具体地谈到死亡,鲜血、头盖骨、尸体,甚至天堂。我们天真地以为,他们都只是基于对诗歌的狂热,而无时无刻地在用我们自以为变形的句子,演绎着一个诗人的情感。
1月23日之后,武汉成了一座“空城”,也让围城内的人们终于有机会抱团取暖。而除了网络,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几乎断了联系,包括父母、包括手足、包括朋友、包括两地分居的恋人。空旷的街道上,斑马线清晰得如亚当的一根根肋骨,而夏娃却远在他乡。谁不喜欢浮云般自在: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是否两鬓斑白。可无声的恐惧,一直蔓延,在每一个角落。
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亲人们已没有了眼泪,因为哭泣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连灵魂也是虚空的,如年轻的肺叶迅速被病毒入侵,在影像中没了色彩。尽管青春依然如芙蓉般绝美,却匆忙间成了一部默片,压抑、冗长。
记得托尔斯泰在一本随笔集中阐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点燃着一支蜡烛,在这烛光下他曾读过一本充满了焦虑、欺骗、苦涩和罪恶的书,此刻这蜡烛爆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隐没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给他看,然后噼啪响过,闪动了一下,便归于永久的寂灭。”我开始讨厌托尔斯泰,讨厌一切思想家、哲学家,包括尼采。尼采说:“女人学哲学,既是女人的不幸,也是哲学的不幸。” 我讨厌极了这种剖析人类的感觉。他们无法挽救生命垂危的人,就算剖析得一清二楚又能怎样?病患还不是在病毒的侵袭中渐渐呼吸衰竭,嘴唇和指甲随着血色素的降低而一點点变白。
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里提到:“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这一点而言,他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恶的。当然,我也会时常解剖自己,因此,我有多喜欢他,便有多喜欢自己;我有多厌恶他,便有多厌恶自己。在疫区人人自危的关头,是那些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指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线医护人员逆流而上,是他们点燃了生的希望。医者仁心,心怀天下。倘若先生健在,弃医从文的他能救回那么多条鲜活的生命吗?他不能,我也不能。
随着汽笛声响,船从江北渐渐往江南靠近。
雨下得似乎更大了些。我回头看一眼冒雨前进的江小天,再看了看走在前边各撑一把伞的老李和亦老师。乘客们争先恐后地朝岸上涌去,我们也随着匆忙的人群,加快了脚步。
是夜,江城有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