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殉难者的回家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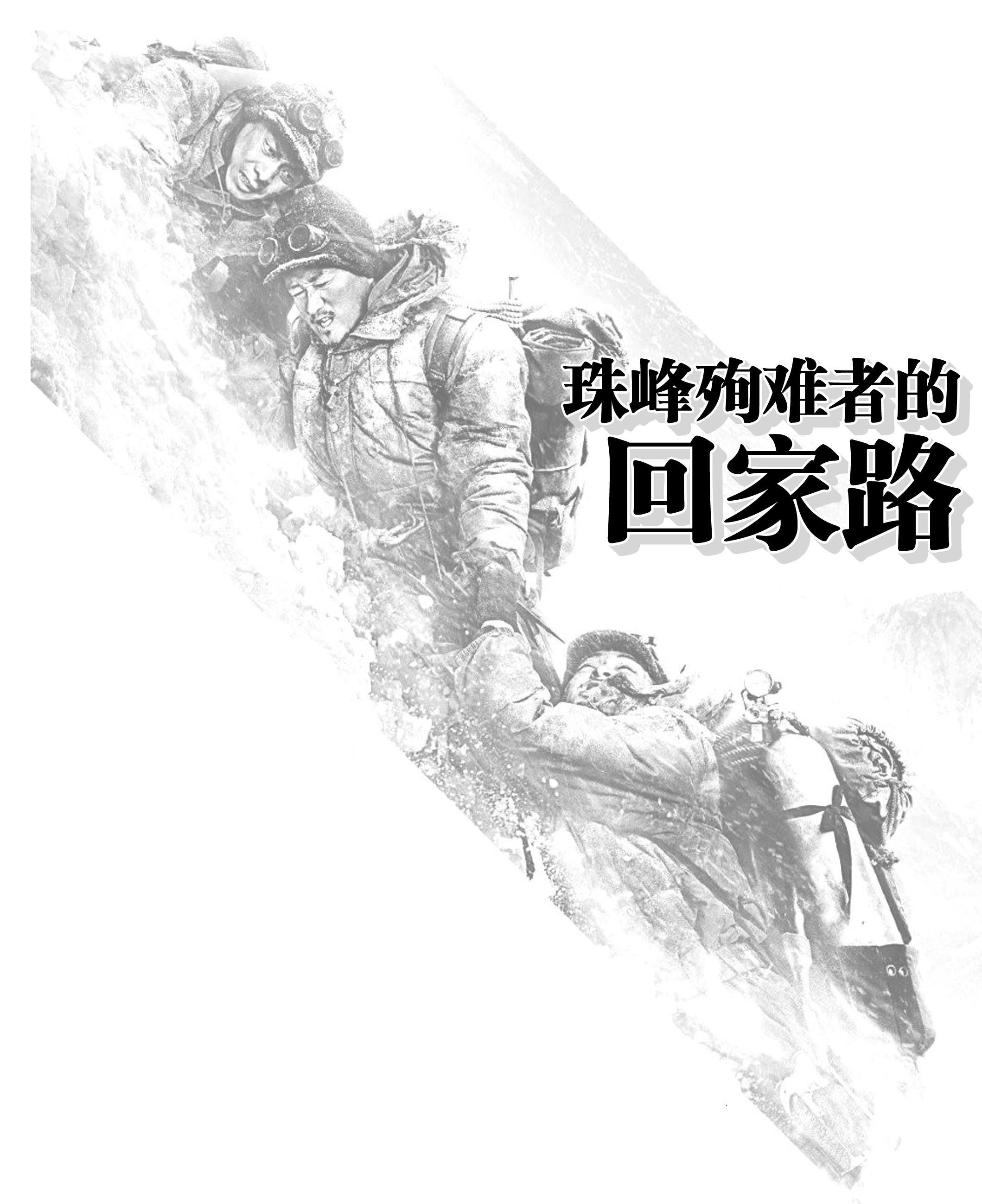
几个夏尔巴人围着那具冻僵的遗体,朝遗体的边缘挥舞着斧头,试图把它从冰的坟墓里撬出来。他们敲落遗体上厚厚的雪块,清理出一条腿。将那条腿抬起来时,整具僵硬的、扭曲的遗体,就可以移动了。
这一天,阳光正好,但这个海拔27300英尺(约合8320米)的地方寒冷彻骨,空气稀薄。珠穆朗玛峰的峰顶近在咫尺,一团雪烟笼罩着通向峰顶的山脊。当夏尔巴人到达这里时,这座陡峭的山上唯一的动静,来自这名死去的男子已经磨损的夹克口袋——它们在如刀的风中上下翻动,拍打着夹克表面。
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环境中暴露一年多后,逝者的脸和手都变得黢黑而干枯。亮黄色的登山服亦褪成了落叶的颜色,他的靴底朝着上山的方向。冻僵的胳膊越过头顶向着下山的方向张开着,仿佛只是坐下休息的时候向后倒去而从此被冰冻。
夏尔巴人拉扯着遗体,压低了声音讨论怎样抬下山为好。那张可怕的脸和骨白色的牙齿让他们感到害怕,于是他们用夹克的帽子盖住了遗体的頭部。
生命的“暗黑里程碑”
这位逝者名叫古塔姆·高希,是一名警察,来自加尔各答。最后一次有人看到他是在2016年5月21日傍晚。
当年,他参加了一个八人登山队,由四名来自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登山者和四名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向导组成。快到峰顶时,他们却不幸耗尽了氧气。最终,四名登山者中有三人死亡,只有一人和向导幸存了下来,那是一名42岁的女子,名叫苏尼塔·哈斯拉。
悲剧发生时,攀登珠峰的最佳季节快结束了。接下来的两个晚上,当年最后20多名登山者在前往峰顶的路上看到了高希僵硬的遗体,位于一个岩石和冰层遍布的陡峭路段上。
和高希一起的印度登山者来自登山文化活跃的西孟加拉邦。他们将珠峰视为终极征服对象,这是一个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和声望的目标。
攀登珠峰代价不菲。为了确保得到最好的向导、服务和安全,一些人的花费高达10万美元。
这四名登山者的月薪只有几百美元。他们在西孟加拉邦的登山圈子里结识了彼此,相比友谊,共同的使命感让他们彼此联结。
他们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平民登山队。所有人都用了至少10年来攒钱,从而凑足了攀登珠峰的预算。他们还在西孟加拉找了一家有名的登山服务公司,尽管公司向每人收取的费用比其他同行低3万美元,但这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笔巨额开销。
这已是他们三年之内的第三次尝试。2014年,一场雪崩夺去了16名夏尔巴人的生命,也让即将开始的登山季告停。2015年,一场在尼泊尔让9000人丧生的地震再次引发雪崩,珠峰营地受到波及,致使18人死亡。这两次攀登计划都因此落空。
而现在,在营地和珠峰较低的斜坡中度过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进入了登顶地带。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会在24小时之内回到营地,踏上回家的路。在印度,攀登珠峰的人被尊称为征服者英雄——“珠峰人”。
天黑以后,他们出现在帐篷外,戴着氧气面罩,穿着颜色鲜艳、厚重的羽绒防雪服。四个人每人有一个向导,出发的时间比原计划稍晚。天空清澈,月亮正圆,一排前头灯照亮了他们面前的路。
从4号营地出发的往返路程,有些人不到12小时就可以走完,而有经验的向导和登山者都知道最多不能超过18小时——12小时上山,6小时下山。大多数人都遵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长时间在外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根据后来从保罗身上拿到的相机显示,保罗在下午1:45登顶珠峰。根据高希用自己的相机拍下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显示,他下午1:57时正在南峰。他戴着氧气面罩,手里拿着旗帜和横幅,脖子上挂着一台摄像机。
虽然摄像机的麦克风被风吹得轰轰作响,但我们还是能听出高希急促的呼吸声。高希似乎在照镜子,他光着手把太阳镜移到额头上,眼睛里满是血丝,又将氧气面罩拉到下巴,露出牙齿和肌肉。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影像。此后这几个人或是半途失踪,或是耗尽体力,倒在离4号营地数十步开外的雪中。
我仍然相信他还活着
自丹增·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在1953年首次登上海拔29029英尺(约合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以来,已有大约5000人至少登顶过一次。据喜马拉雅数据库显示,在此期间近300人在这座山上丧命。尼泊尔官方估计,珠峰上仍散布着大约200具遗体。
大部分遗体远离人们的视线。一些遗体已经按照家人的意愿或尼泊尔官方的指示被转移、扔下悬崖或扔进冰川裂隙里了。家人担心自己的亲人成为他人的“里程碑”,而尼泊尔官方则担心尸体会影响该国旅游业的发展。
然而,遇难者的家人及朋友越来越希望遗体能被送回家。因此,他们向政府提出请求。但取回遗体的过程,远远要比探险更加危险和昂贵。
这其中有现实的考虑,包括是否要去搜寻已被认定失踪或死亡人员的遗体,并且要考虑是将遗体带回,还是让它永远地留在原地。还有情感方面的考虑,或许出于文化和宗教情感,人们往往追求一种“了结”。
此外,还有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包括危险性、花销、当地习俗以及国际法律。有时候,在一些地区,找回遗体不只是一个念想,还是一种需要。死亡一经证明,急需经济支持的家人就可以获得提供的补助。
2016年,当三名印度男子的遗体散落在珠峰高处时,渺茫的救援希望逐渐成为寻回遗体的呼声,搜寻工作由西孟加拉政府主导。
从本次登山季最后一次登顶尝试到夏季季风来临,中间只有短短几天的窗口期。在这几天内,由雇来的六名夏尔巴人组成的一支搜寻队,试图找到逝者,并将遗体带下山去。
搜寻队第一个找到的是保罗,他离4号营地最近。曾经,他和妻子及10岁大的女儿住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班库拉小县城里,如今,他的遗体面部朝天,唯有靴子的鞋尖没有被雪覆盖。搜寻队花了4个小时又凿又撬,才把他从“冰墓”中挖出来,而将他拖到2号营地又花费了12小时。在那里,一辆直升机会把遗体运往基地。
珠峰上,在比挖出保罗的遗体更高的地方,两个夏尔巴人走向了4号营地。那里海拔大约2.6万英尺(约合7925米)。该营地坐落于氧气稀薄的死亡区边缘,也是登山者们向山顶发起最后冲击之前的最后一个休息站。
夏尔巴人搜寻着被遗弃的帐篷,有些帐篷被风撕成了条缕状,在这里,他们又发现了另一个印度登山者裁缝纳特的遗体。
肆虐的狂风使得搜寻队被召回,无法再登上更高的地方寻找第三个人——高希。夏季季风即将到来,登山季就要结束,高希和纳特都没在这一次搜救中“回家”。
可是在印度,高希的妻子尚达娜还留着头发上那抹赤色的发际红,右手手腕上还佩戴着红白色的手镯——这表示她是一个已婚女性。在确定自己是寡妇之前,她不会摘下它们。卧房内,她的挂历还翻在2016年5月那一页。在她心里,这是时间停止的地方。
“我仍然相信他还活着,”她说道,“除非我看到他,再将他火化,否则我不会变。”
在加尔各答西北100英里处的杜尔加布尔钢铁城,纳特的妻子莎比塔在试着遗忘。她没有钱可以将遗体带回家。她和丈夫之间也从未讨论过他死后怎么办,但她现在已经说服自己相信他是想要留在山上的。
死亡原因“不明确”
一年后,在2017年登山季开始的第二天,第一批由绳索修复人员拍摄的尸体照片到达了。
照片中,一具穿着褪色黄色登山服的遗体蜷缩成U形,半埋在雪里。他的脸已经看不清了,但靴子和裝备跟高希一年前穿的一样。
所有人一致认为,那是高希的遗体。
西孟加拉邦政府立刻派了三名男子赶赴加德满都,很快与加德满都一家喜马拉雅探险公司达成协议。政府会为找回这两具遗体支付9万美元。
莎比塔·纳特和尚达娜·高希接到了一名政府官员的电话,要求她们签署一份“无异议”证明,允许找回遗体。她们同意了。
负责监管尼泊尔登山业的尼泊尔旅游局只对这次行动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在数百名登山者往上爬时往下运遗体。
5月底,在珠峰登山季的尾声,5名受雇的夏尔巴人在凌晨1点悄悄离开了2号营地。
在离开2号营地1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所谓的“钉鞋点”,把氧气调到了低档。
夏尔巴人通常只在死亡区使用氧气,也就是4号营地以上。
领队是29岁的向导达瓦·菲乔克·夏尔巴,他曾5次登顶珠峰。
上午11点左右,搜索队到达了4号营地。在登山季的尾声,这里空无一人,只有废弃的帐篷和装备。而在几小时后,另外6名夏尔巴人,沿着同样的路线,离开了2号营地,前往4号营地。他们的任务是找回纳特。
当地时间下午1点39分,搜寻高希的小队找到了他的遗体。
这些夏尔巴人把高希连接到一根新绳子上,并将它固定在一块高约30英尺的岩石上,用冰镐从雪中取出遗体,遗体移动时是整块移动,而非扭动,四肢、肌肉和关节都冻住了。据达瓦·菲乔克·夏尔巴估计,遗体的重量超过300磅,是高希活着时体重的两倍,要三人才能勉强应付。
拂晓时,高希的遗体被运到了“钉鞋点”。负责找出他的遗体的这些夏尔巴人连续工作了近28小时,不过高希的遗体是暂时放在这里,等找到纳特后,会有直升机来把他们从山上运走。
2017年5月25日下午2点左右,纳特的遗体也被运到了“钉鞋点”,身上还穿着他自己缝制的红黑色风雪服。一个可伸缩的塑料担架把他的遗体裹了起来。
高希搜索队从2号营地往上走了一小段路,用简易雪橇巧妙地把两具遗体往山下运。1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直升机降落点。
可当这些夏尔巴人呼叫大本营时,却被告知直升机当天不会来。他们还在等待另一名印度登山者的遗体,那个人刚在几天前死去。Seven Summits公司想把三具遗体一起运下去,以降低成本。
最后,在5月28日,一架直升机绕着山谷盘旋,降落了下来。
而在最后的报告中,医生将高希死亡的原因列为“不明确”。对纳特的类似检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在高希的家中,他的遗孀尚达娜换了衣服。色彩斑斓的纱丽被印着浅色小花的白色纱丽取代。她的发际线上没有表明已婚的朱砂,额头眉心间也没有红点。戴在手腕上的红白色手镯也不见了,丈夫的遗体火化时,她打碎了它们。丈夫在珠峰上死去一年后,她成了一名寡妇。
她卧室墙上的日历依然显示的是201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