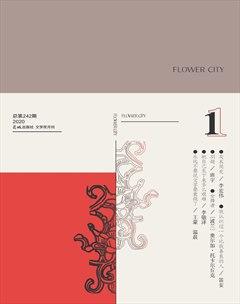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
李敬泽
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了2018年和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地利的彼得·汉德克。
这两位,汉德克我们比较熟悉,他2016年来过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九卷之多,洋洋大观。托卡尔丘克呢,我感觉大家都不太熟,反正我不熟,这几天总是把她说成“邦达尔丘克”,一边说着一边知道我说错了,邦达尔丘克我熟啊,那是苏联的大导演,我看过他导的《战争与和平》。然后一边想着一边说:波兰女作家邦达尔丘克……
一个文学奖评出来,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别的什么奖,只要这个奖有影响力,大家关注它,就一定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相比之下,比如诺贝尔化学奖或物理学奖就没什么争议,国际数学界还有一个奖,叫菲尔兹奖,那就更没争议,评出来我们只能膜拜。为什么无争议?原因很简单,那都是最强大脑啊,哪儿轮到我们插嘴,我们都不懂啊。物理学、化学、数学,搞到那个段位,都不在常识范围之内,公众不能也不必参与。文学就不一样了,很少有人会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文学事关人类生活、事关经验和情感,提供想象和言说,人是什么样、人应该和可能是什么样,这几乎不存在什么唯一的真理,大家都有发言权,大家的感受和想法和判断肯定千差万别,在千差万别的对话中逐步形成相对的公论。所以,关于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很难有绝对的答案。比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瑞典学院那些女士们先生们,他们把这个奖都颁给了托卡尔丘克,偏不肯颁给阿特伍德。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我紧急补课看了一本,《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的感觉是,阿特伍德是女巨人,托卡尔丘克相比之下还是个文艺青年。
当然,我的看法也可能是偏见,我很羡慕那种人,他们把自己搞成小宇宙,他们的偏见就是他们的真理和科学。这很好,但我做不到。当我们确认谁是好作家、哪一部小说是好小说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有限性做出判断。什么是有限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禀赋,有自己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你的趣味和偏好。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就喜欢《三国》《水浒》,受不了《红楼梦》,有问题吗?没问题,你喜欢就好。但另一方面,文學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和认出我们自己,它还是我们住宅之外的一条街道、村子之外的一片原野,让我们去结识陌生的人,见识那些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事,让我们领会他人的内心、他人的真理,由此,我们才不会成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囚徒,我们去探索和想象世界和生活的更广阔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能性。什么叫不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小宇宙里你认为这不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现在,你打开这本书,看着不可能的事物,如何被想象、被确切地展现出来。
所以,现在,就谈谈汉德克。本来还应该谈谈托卡尔丘克,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她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性”,她是令人厌倦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我读上几十页就知道大致如此、不过如此,而读小说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希望能靠它抵御人生的厌倦。
汉德克是奥地利人,生于1942年,今年77岁了。关于他的生平,这些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介绍,我就不细说了。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奖,说该奖的价值不过是六个版的新闻报道。现在呢,他自己也变成了刷屏两三天的新闻人物。在突然激增的关于汉德克的知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他的身份。
身份政治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的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中,“我是谁”成了一个很纠结、很尖锐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启蒙话语中个人的自我意识问题,它还涉及族群、政治、权力关系。对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来说,身份政治尤为重要,比如女性、女权。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一个焦点,就是要有女作家。有没有女作家,不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政治正确”,这个压力很大,所以瑞典方面赌咒发誓,昭告天下,一定要评一个女作家出来,结果就是托卡尔丘克。而汉德克,他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个敏感的、边缘的身份问题,他是白人男性,奥地利是欧洲和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按说他应该很知道自己是谁,不会为此而焦虑。但其实,他的生父和继父是德国人,至于他怎么就成了奥地利人我也懒得追究,反正德国和奥地利搞成一家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我要说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大部分在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在奥地利,汉德克的母亲就属于这一小部分,所以才认识他父亲。那么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啊?就在奥地利南边,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十几年前的民族主义狂热,把南斯拉夫打成了一片血海。这件事对汉德克的身份意识、对他的创作乃至对其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关于汉德克,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除了剧作家、小说家,他还是“世界蘑菇大王”。据他自己说,他是世界上蘑菇知识最丰富的那个人,是不是吹牛我也不知道。蘑菇还不是可吃的蘑菇,茶树菇、猴头菇、平菇、松茸什么的,不是,汉德克并不是专精蘑菇的吃货,他感兴趣的是不能吃的、吃了要发疯死人的毒蘑菇。据他说,世上的毒蘑菇有二百多种,他都认识。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带点儿自传性的《试论蘑菇痴儿》,一个人痴迷于蘑菇,寻找蘑菇的故事。顺便说一句,除了蘑菇这一篇,他还写了《试论疲倦》《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试论寂静之地》,这个“寂静之地”就是厕所,我读的书不多也不少,很多年前在《荫翳礼赞》里读过谷畸润一郎写厕所,然后就是汉德克这一篇。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博物学兴趣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中外皆有,比如纳博科夫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不研究蘑菇,他研究蝴蝶。写作这件事,上班下班没法分得清楚,作家整个的生命都会放进去,蝴蝶蘑菇也会不知不觉地进去。纳博科夫的小说就有蝴蝶之美,汉德克呢,他的写作也有毒蘑菇的风格。毒蘑菇艳丽、妖冶,一点也不低调,这艳丽和妖冶是危险的,它是诱惑,也是攻击,骗取你的注意,抵达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中枢神经啊,麻醉、致幻、休克等等。所以,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的影响。——前几天,我正这么聊得起劲,有个家伙在旁边嘀咕:那个,毒蘑菇也有不艳丽的。我一下子就熄火了,啊?是吗?那好吧,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影响,比如毒蘑菇的低调、家常,它不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它欺骗我们,潜入我们的神经,控制我们的意识,就好比语言…… 这时,又有一个小家伙在旁嘀咕:汉德克说的是二百多种蘑菇,不是二百多种毒蘑菇。——好吧,算我没说,下次他来我请他吃云南菜。
瑞典学院对汉德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关键词是“语言”。语言问题是我们理解汉德克的那把钥匙。汉德克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奥地利同乡: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启动了哲学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关于人、关于人的存在,两千年来众多哲学家苦思冥想,提出无数说法,到维特根斯坦这里,他说,你们都想多了,都没想到点子上,关键在语言,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他的论述很艰深,这里不必细说,总之,他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如在汉德克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汉德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骂观众》。2016年他来中国,所到之处,大家跟他也不是很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说,所以,一搭话就是请您谈谈《骂观众》。老头儿后来都有点烦了,说我1966年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骂观众》,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又写了那么多东西,你们老提《骂观众》,这么些年我不是白活了吗?
但《骂观众》确实重要,从《骂观众》入手,我们可以理解汉德克的根本想法和根本姿态、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那时起,他已经写了四十多年了,他的风格当然有变化,但是,这个根本似乎没有变。
《骂观众》很简单,但是惊世骇俗。这是一个剧本,和我们所熟悉的戏剧完全相反,它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舞台上也没有布景,甚至就没有传统的舞台与观众的区分。从头到尾,就是四个人,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夹枪带棒地骂观众。你们这些蠢货,你们要看的所谓戏剧,不过是“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将他们引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愚弄,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判断”。
《骂观众》骂的仅仅是戏剧吗?不是的,从根本上说,汉德克是在骂语言。汉德克的创作起于对人类语言的质疑和批判。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人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学习了、使用了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但由此也帶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言是外在于我们的,是异化之物。语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你发明的,是我们学来的,是一整套社会的和文化的知识、传统、能力,强制性地传给你、教给你,你不学行不行?当然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都受语言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根本的,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越意识不到越根本,我们都以为是“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大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话说我”,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意识不到。
所以,就要“骂观众”,就要通过这样的冒犯性行动,迫使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汉德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灵魂深处在哪里?就在语言里。语言绝不仅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也绝不仅仅是指涉及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不是中立的、透明的,它自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语言,它都积累、生成着复杂的意义,正是语言所携带的这些意义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经谈到,恋爱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它植根于一套恋爱话语,不是指向生殖的,而是指向精神的、隐喻的、游戏的这么一套话语。《阿Q正传》里,阿Q面对吴妈,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要和你困觉!这就不是恋爱,这是生殖和找打。阿Q不是五四青年,他没有一套恋爱话语,他如果说,我想和你度过每一个夜晚,那会怎么样?也许不会挨打,没准还能谈下去。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凡恋爱言情,必须是普通话,用地方方言一定笑场,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恋爱话语本身就是用白话、普通话、书面语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语言提供的现成剧本中演戏。
如果仅仅是谈恋爱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语言的力量,它会变为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它会从生命的根部驯服人,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就认为女人就是低男人一等,穷人就该永远受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汉德克的作品,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都是从对语言的这种警觉和批判出发的,由对语言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到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最初的小说《大黄蜂》开始,他就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西方文学,认为那些小说,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理所当然的、骗人的世界图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方式、话语方式,是虚构的,但渐渐的,这种虚构入侵乃至支配和替换了现实。在汉德克看来,要造反、要革命,就是要从语言干起。
语言是如此重要和基本,它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和根基,也是文学的条件和根基,在这个问题上干革命,肯定会带来很复杂、很严重的后果。
首先一个后果,就是汉德克认为,所有那些我们以为是小说的小说,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命运等等,都是骗人的,都体现着语言造就的统治秩序。那么现在,你为了让人们觉醒过来而写小说,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写不像小说的小说、不像戏剧的戏剧。所以,读汉德克,你得准备好,你如果是一个19世纪小说爱好者,那你肯定会很生气,你倒不一定觉得他在骂你,但你肯定会觉得他在浪费你的时间。
另外一个后果更为根本,就是,你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牢笼,使我们既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认识世界,但同时,人又不得不在语言中存在,汉德克还得用德语写小说,那么怎么办呢?这不是无解的悖论吗?
在汉德克看来,这正是人的悲剧所在。在他的另一部戏剧《卡斯帕》中,一个人生下来,喘气儿,活着,当然这还不行,他得“通过语言真正地生下来”,于是就开始学语言,但是,“当我学会第一个词,我便掉进了陷阱”。卡斯帕这种进退维谷的命运就是人类命运的象征。可以说,汉德克的写作就是为了应对、反抗这个命运,把人从作为一种统治秩序的语言中被解救出来,让人身上、人心里那个沉默的、无言的“我”活过来,发出声音,获得语言,不是“话说我”,而是“我说话”。
但是,“我说话”何其难啊,一个人去掉现成话语的遮蔽和支配,把自己、把这个所谓的“主体”呈现出来,这是很难的事。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现在忽然发了疯,“惟陈言之务去”,排除所有现成的话,看见今晚的月亮你不要想李白苏轼、不要想嫦娥玉兔,你只把今晚的这一轮月亮说出来,赤条条无牵挂地说出来;然后同样的,关于你的生活、关于你自己,你不要小说化、鸡汤化,你排除所有现成的意义话语,你说吧——我估计绝大部分人就无话可说了,反正我是无话可说,一台电脑卸载了系统,那还怎么运行?
这既是逃避和反抗,反抗语言的规训,同时,也是探索、发现,你不得不最直接地注视自己和世界,并找到、发明相应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要有光,靠自己的光照出自己、创造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生出来、长起来。在生活中,真要这么干,跟疯了也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没必要这么干,我们读汉德克的书就行了。
但汉德克的书真难读啊。说老实话吧,我把他的九卷本摆在那儿,一本一本翻,每一本都没翻完,读不下去。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深刻地接受了语言规训的人,而汉德克是“骂观众”的,是“骂”我的,他的小说不是回音壁,不是音乐会,他一点儿都没打算让我舒服,我舒服了他就失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好奇,想看看他如何通过语言把自己生出来,但在这里,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瑞典学院所夸的语言当然是汉德克的德语,而我读的是翻译过来的汉语,从德语到汉语,等于过了一遍筛子,故事、情节、人物、命运,那还可能剩下不少,而这些在汉德克那里本来也没有多少,他有的是“语言”,但偏就是这个语言,过完筛子就基本不剩下什么了。我读汉德克,总觉得结结巴巴、不知所云。 咱也不敢说翻译有问题,而且我相信,汉德克的德语原文很可能也是结巴的、缭绕的,不会那么流畅,他本来就是要表现意识和主体的原初的生成,这种生成肯定是不熟练的,不可能顺口。这种语言瑞典人能看出好,看出创造性,汉语读者能不能看出来我就不敢说了。从译本来看,我读得最舒服的是《骂观众》,精确、流畅,是好汉语,但是我多少又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翻得太好了,少了一点原本的狂乱、粗暴?总而言之,我不能对你说我喜欢汉德克的作品,由此而来的一个教训是,人还是应该学语言,除了汉语,最好还要学外语。
事情就是这样,我认为我理解汉德克的理念,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他的作品。而且,就理念来说,虽然看上去很本质、很尖锐,但我总觉得那近于屠龙之技,杀龙的技术,技术很高很新,但龙在哪里?或者说,在欧洲语境下,他的批判缺乏真正的政治性。我就是爱看个传统戏,虽然照你这么说,确实也有问题,但说到底是多大的事呢?值得你这么撒着泼地骂?来都来了,看你骂了半天了,那就鼓个掌呗,又是多大的事呢?人固然是生存于语言,一竿子插到语言上去,能搞出五花八门精致的理论,也能搞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当代艺术,但也很可能回避了现实的和结构性的社会政治疑难,沦为无关痛痒的撒娇。这不仅是汉德克的问题,也是欧洲、特别是西欧文学的问题。我在别的场合说过,西欧小说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它的意识封闭掉了,自以为“真理在握”,它不再能面对真正的问题,不再经受人类生活严峻复杂局面的考验。
然后,考验来了,正好掉在汉德克头上。我一开始说了,他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属于奥地利这边,但毕竟斯洛文尼亚民族的主体是在南斯拉夫。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南斯拉夫土崩瓦解,发生残酷的内战,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发生的唯一一场战争,而斯洛文尼亚率先宣告独立,投向西方阵营,为这场战争拉开了序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造成了世界上很多人在身份上的纠结、危机,忽然南斯拉夫打起来了,换了别人也就是看新闻看热闹,而汉德克,他妈妈也是斯洛文尼亚人啊,能说没关系吗?没关系也有关系了。由此,我们也看到身份问题的复杂性,身份可不是身份证上的照片和号码那么简单,人有层层叠叠的身份和认同,比如我,是中国人,是山西人,是山西运城人,是山西运城芮城人,像个俄罗斯套娃,但我要是碰见河北人,我又马上变成了河北人、河北保定人、河北保定完县人,因为那是我母亲的家乡。我的认同可能随境遇而变化和变换,认同与认同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很多时候并行不悖,你是个山西人一点不妨碍你同时是个司机、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是个中国人,但有时会发生冲突,会撕裂和断裂,特别是,在严峻的社会历史局面中,人很可能会陷入身份危机,某些自然的、休眠的身份可能被唤醒,人甚至会脱胎换骨,为自己发明新的身份、建构新的认同。比如汉德克,他身上流着斯洛文尼亚人的血、斯拉夫人的血,对他来说这未必是多大的事,但现在,在眼前的这场悲剧中,他忽然意识到他不是看戏的人,他不是新闻的看客,他的批判性理念,过去是运行在语言层面、个人的日常经验层面,现在,他面对着大规模的杀戮、仇恨,面对历史和现实矛盾的总爆发,他身在其外,心在其中,他觉得斯洛文尼亚的事、南斯拉夫的事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事。
于是,他来到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一路走过去,写了三篇文章:《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有《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这三篇文章在中文版中收入了《痛苦的中国人》,据说这本书卖得不错,因为大家看书名觉得和咱们有点关系,实际上没什么关系。这三篇我认真读了,对我来说,汉德克此前的作品如果是飘着的,那么这三篇就是他的锚,扎到了泥泞的、迫在眉睫的人类的困境和苦难中去,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里艰难地探索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正义。
南斯拉夫问题,确实极其复杂,上千年的一团乱麻,如果在这里说清楚,就不是谈文学,变成讲历史了,而我对此也毫无准备。简单地说吧,在当时,在西方舆论中,在西方知识界、文学界,关于南斯拉夫的内战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剧本,牢不可破,在这个剧本中,塞尔维亞是邪恶的,是进行种族屠杀的一方,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几乎就是一个小号的希特勒,美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西欧人、德国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知道,汉德克对这种写好了的剧本根本不信任,那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的产物,而就南斯拉夫来说,这套剧本显然是冷战的延续,不仅因为南斯拉夫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因为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是“斯拉夫”,北边还有一个“斯拉夫”,就是俄罗斯。现在,汉德克来到昔日的战场,从冬日到夏日,他面对着阴郁、沉默的人们,那些塞族人,那些被指认的罪人。给我的感觉,他的行文、他笔下的人依然是迟疑、艰难、不连贯的,但我想,这未必完全是翻译的问题,这也不仅是从空无中自我生成的艰难,这是一种被专横的话语暴力压制着、压制到沉默之后的艰难,是面对世界无话可说、知道说了也白说的无望和凄凉。在这里,汉德克对语言和文学的批判落到了土地上、落到了焦土和废墟上,扩展到对媒体语言、信息语言的政治批判,他发现西方媒体围绕南斯拉夫发生的事制作了一套远离真实、漠视真实的非黑即白的图景,深刻地控制着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控制和改造了现实。在这里,虚构就是这样变成现实的,语言就是这样抹去声音的。汉德克面对着这片土地上活生生的悲剧,他忍不住想象,一切本来可以不这样,原来的南斯拉夫或许能够构成第三条道路,各民族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但是,在西方的推波助澜下,南斯拉夫被毁掉了,他说: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进而,他站出来说:我们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塞尔维亚人的正义。
也就是说,汉德克并没有简单地站在斯洛文尼亚这边,实际上,就像刚才说的,斯洛文尼亚率先独立,迅速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转换,不再是“斯拉夫”,而是属于中欧、向着西欧。我的感觉是,汉德克对于这个民族如此轻率地转身是痛惜的,在他的眼里和笔下,这个新的国家如此轻佻,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化的斯洛文尼亚。他的认同经由斯洛文尼亚转向了原来的南斯拉夫,这使他的批判意识获得了一个支点:人们站在审判者和成功者一边,为什么不听听被审判者和失败者的声音?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正的、追求真实的法庭?
然后,汉德克就闯祸了,就被骂惨了。在大街上骂观众是要付出代价的,背叛他的西方精英身份和认同的结果是,汉德克成为西方文学界和知识界公认的“混蛋”。这厮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气炸了:你们怎么能把奖给了这么一个家伙,他说塞尔维亚也有正义,他甚至参加了米洛舍维奇的葬礼!
在这件事上,我佩服瑞典学院。他们艺高人胆大,他们敢于发一回疯,以此证明他们没有失去语言和精神的弹性。虽然以我的知识,无法对南斯拉夫问题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但这样一个作家,他一直力图自己把自己生下来,离群索居,艰难地让沉默化为语言,然后,在命运(对不起,他不喜欢这个词)来临时,他忽然发现,所谓“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在越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常经验之后原来竟是不可触碰的,他走过去了,决意把自己放到困境中去,走进被放逐的人群之中,至此,被他生下来的那个自己,才真正走进世界。这个欧洲老炮儿,他让我想起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加缪,我因此喜欢汉德克,尽管他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混蛋,尽管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其实看不下去。
汉德克,他也是吉姆文德斯的著名电影《柏林苍穹下》的主要编剧,在那部影片里,有一首诗一直回响: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幻想小溪是河流,河流是大川,而水坑就是大海。
当孩子还是孩子时,不知自己是孩子,以为万物皆有灵魂,所有灵魂都一样,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2019年10月14日初稿
11月23日改定。
11月27日再改定。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