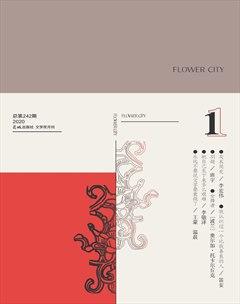先生,先生
听到宁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是初春时节,我在北方的家里,室内开着两扇窗,窗外是强劲的西风穿空的声音,这样的风声已经持续了两周。
彼时,我的妻子新得了一幅油画像,是我的师弟为她画的,作为我们的新婚礼物。她很喜爱那幅画,画中的她,发如墨色,恬澹笑容,素色的婚戒戴在无名指上。我想起宁先生,二十多年前,宁先生也得过这样的油画像,是她的先生为她画的。
宁先生去世时刚刚61岁,很突然,也很平静。虽然她独居,但有相互关照的女性挚友每日都会联系,彼此也留了住处钥匙。发现不妥后,对方立刻去查看了,所以处理得很早。这些,是师弟参加先生葬礼后告诉我的。医生说,宁先生的那种死亡方式是没有痛苦的,心脏骤然停止工作,肌体停歇运作,一切发生在瞬间,脑部几乎无法作出反射,去感受到衰弱或者恐惧。我只是不能去推想那一刻如何发生在我的先生身上,几乎不近人情地并未参加葬礼。
我依旧一般生活,晨起与妻子步行到地铁口,转两次车到研究所上班,下午去兼职的文化公司处理事务,傍晚再乘地铁回到我们温暖的蜗居。睡前有时喝一些妻子自制的梅酒,带一点微醺等待睡眠。只是,那段时间会做醒来不记得全貌的梦,在深夜惊起。
生活刻板地推进,会庆幸那种平庸的平静。真实的失去在夜深时逼近我,却总在白昼到来时随日光散去,似乎内心自可以巧妙避开创痛,以求平安。在北方的那几年,我接触了以前全未想过的世界。融合与越界成为大势所趋,我的专业突然从边缘角色变得被主流需要和认可。因为我年纪较轻,一些新型的合作项目,公司多让我去洽谈完成。一个红酒的品牌希望我能选择合适的古诗词,竖排印刷成长长卷轴,环贴在瓶身上成为标贴,每一瓶酒有不同的编号,对应不同的诗词。某品牌的春季成衣发布,同我洽谈的年轻女性全程使用英文,她与我谈商品与消费主义,谈城市与资本主义。她说我们不仅仅是谈服装,服装可以成为一种思想,她的理想是在博物馆或者图书馆开新一季的早春发布会。一个高端餐饮的品牌,推出适合忙碌中产的半成品煲,可以限时送达家中,只要放在炉灶上,即可完成搭配合理材质精良的家庭供餐。展台设计预期如下:每一种煲都有一个古典的名字,走近会有语音说明,其材质的运用,每种材质在典籍中如何被记载,以及其构成与搭配。如烧鸭腊味煲一例:利苑的烧米鸭和煎海虾放在上位,中层有秘制不传的中药滋补食材包,底层是从银座的Akomeya订购的米,根据甜度、黏度、软硬程度提供不同的选项。展区的背景音乐是粤剧《梁祝》,虽则文辞古怪,念白难听,却别有一种风致,似白乐天说的“呕哑嘲哳难为听”。亦有拍摄Vlog的视频公司期待合作,要求我为视频制作的文化内容提供无误的资料支持,他们推出的精准定位的网络红人获得的不仅有惊人流量,还有文化传人的至高荣誉。这个世界在先生离开之后,似乎變化更快,我看起来也能恰如其分地跟随,顺时应势。先生去世半年有余,母校要为先生做纪录片,专业的老师推荐我为主笔,接了这份工作后,我自然地从文化公司辞去了职位,未必没有感到释然。
回去那个南方城市的火车上,道旁树木有节奏规律地退离视线,窗外风景像渐次展开的平淡画卷,深深浅浅的苍灰色调的北方天空之后,渐入雨境,车窗玻璃上雨线斑驳,许多不重要的记忆碎片浮起。我想起我的母校和祖父的母校之间陶谷新村那条小路,我和挚友S君在那条路上消磨过许多时光。那里有三家古书店并列,有彼此不属的相似名字。某个午后,骤雨急至,我们推门避雨,门外笼中的黑色鸟雀扑扇翅膀,室内破旧的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我们走到书架间,翻看一册《清代学者象传》,互相赌注翻到哪一页我们以后就成为哪个学者。我打开就是钱谦益,让他大笑,亦让我受伤。某个雨夜,同学几人看完电影从山西路的剧场穿过颐和路一带走回学校,潮湿的空气中幽幽浮着无花果树的香气,一行人的身影映在淡黄色石灰墙壁上游走,尤似电影中的画面:空空儿,精精儿,化作红幡子、白幡子相斗,矫如俊鹘,轻若游蜂。雨云洇湿的月光里,转首看到学姐H君曲线优美的侧颜,她丰盈的乌发完全向后梳拢,盘作发髻,露出的额头和耳朵,皆有玉一般的质感和光泽。一路向南,记忆在潮湿中苏醒。
12年前,正是在这个南方城市,甫入大学的我认识了宁先生。那年,有一个新闻事件,历史专业的一个天才少年,为抑郁症所困自杀,留下万言的遗书道出迷惘。可很长时间我看不到窗外,并不知道阴影,内心一片茫茫是因为简净,平心静气地愿意奉献一种劳作耕耘,呵护衷心以为珍贵的事物。
由祖父养育长大的我,幼时由他教授记诵尚不能懂的古文和诗句,回忆起来祖父既受儒家载道的影响,教授我如《谏太宗十思疏》,亦教授我美文如《赤壁赋》,那些诗句在我身上落下种子,生根抽芽,与稚嫩的体魄精神一体地生长。祖父与我说起他早年的大学,他告诉我,六十年前,在那所以满是爬山虎的塔楼为地标的大学,在窗外可眺望紫金山的校舍,他曾跟随他的老师诵读这些文章。他后来去了更南方的蕉风椰雨中再继学业,年迈回到北方的故乡,心中却一直念念不忘度过两年青春时光的南方城市。他讲起过,在他离开那个南方城市的前一年春天,后来成为我的母校,当时还是其前身的女子文理学院,举办庆祝五朔节的舞会。正当好年纪的女孩子们,在100号楼前的大草坪上尽情欢舞,他跟随母校影音部的老师去拍摄,他说那时他见到过一目入魂后来却音尘相隔的面孔。多年以后,我逆流南下来到这个城市读书,多少因为祖父。
认识先生的那一年,我18岁,先生49岁,先生身体状况不好,中文系指派我做先生的课代表。我早听闻宁先生,母校的古代文学以谭先生为首,而宁先生是谭先生最得意的女弟子,36岁的年纪做了教授,清诗的研究更是业内翘楚。先前因家事去了国外的宁先生,重返母校,而我又能受教于她席下,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幸事。
彼时,国学中兴方有迹象,在古典文学的传授领域一时百态,有在教席上讲求字句解说的前辈,有在大众传媒以现代话术包装古典诗词的闻人。宁先生与他们都不同,多年以后的一日,与妻子观看大卫洛维的电影A ghost story,电影讲生人与亡灵的同在与感应,我想起先生的课堂。宁先生不是为了讲求阐释或者唤起共情,她与古人有情,与学生有情,她让往去的和新鲜的灵,在这个空间相遇。连接时间与万物使人易感又孤勇,妄想以一己之身抵达真理。我感受到智识的强烈吸引,先生让我看到最接近理想的那种可能,想成为先生,强烈的贪恋如此被唤起。
先生身量不很高,腰板总是直的,因此总觉得要比实际高一些。她的气质与她的声望并不相称,少有锋芒,也不是那种玲珑的一团和气,先生有她自在的世界与始终的醒惕。下课后,学生会围着提问,她总认真听,想一想再缓慢作答,她不会长时间看着人说话,若对话久了,她会看到别处去。这样的问答结束,我陪先生走回她的研究室,她比平常显得疲态。先生的研究室在中文系主楼最高的一层,与古籍研究所相邻,而中文系主楼本就建于山腰,透过紫红色雕花的窗棂,可见不远处的清凉山的葱郁树木,隐现其中白色山墙和屋宇亭台。先生研究室内的书远没有想象的多,常用的书放在书桌和近旁书柜里。她用的不是一般的书桌,是宽大的巴花木条形桌,覆盖浅茶色的亚麻布,边缘垂须打穗。同學说先生有时会写字,我没有亲见过。我只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来拜访先生,大家团坐于桌前,先生一贯温和地微笑着。某年初雪,先生微微敞开窗户,遥遥可见窗外银杏和鹅掌楸金黄色的叶片还在枝头,清凉山书院的飞檐细瓦已覆上薄雪,冷冽的空气穿窗而入,寒意制造凝住万物的寂静,在先生这里却是另一种安宁。她用带来的英国茶茶包给我们泡茶,热水滚开,气味芬芳。大家说话聊天,热气和话语升腾交织,融开冬日的清颓。先生的研究室不备茶杯、不备多余的椅子,大家每每从隔壁会议室携椅子来,走时再归还。喝茶,用的是印有中文系logo的纸杯,先生也一样。大家离开后,那个房间恢复了那种轻简,几乎不见个人生活的印记。
路先生说宁先生的葬礼他参加了的,其时他在国外开会,一时买不到直飞,转机花费了十个小时赶回来送先生。路老师是宁先生本科和研究所时期的同学,亦是同乡,成为我首先访问的对象。他说,宁先生走得太突然。她躺在簇拥的花束中尤其瘦小,厚重的妆容凝滞住生机,他随着瞻看的人流缓缓走过觉得那不是她,说着,他拿下眼镜拭泪,迈向老年的浑浊泪水悬落松弛的眼目四周,悲伤真切。他说,我们入学那年百废待兴,学生的年纪参差不齐。宁先生在我们班是最小的,她却先走了,我们这些成天还忙着全世界开会的,不觉得自己老,总觉得好时光才刚开始,宁先生一走,却像敲醒了我们。
路先生的回忆,将我带去的是四十年前的我的母校。学生得到升学的机会不易,蹉跎岁月里经历过辛苦,惰性未生,兼以年纪尚轻,不知倦怠,读书可谓如饥似渴。看到曾处困厄多年的先生们,重获生机,渐向老迈也不愿停歇工作,更对专业心存理想,以为承继传统的职责在身。宁先生是有家学根底的,经年富庶的江南小镇民风淳朴,她的家族在当地根基甚深,在动荡的人世未受太大冲击,她接受父亲的指引念书,她曾说起少年时如何细细揭开书橱的封条,拿出书再封上。如此喧嚣中被护佑了一份安宁,又适时地得到升学的机缘,这是宁先生的幸运。
路先生和宁先生同为谭先生的弟子,得到他的亲授。谭先生要求研究生每周须见面谈话一个小时,指导念书和文章,并带着他们做诗选,修订文学史,做些实践工作。这些教导,多是在谭先生家中完成。现在谭先生的住所已经被钉上了黑底银字的铭牌成了故居,我读书时亦探访过,宁夏路的黑色的小门推开进去,是细巧庭院,灰黑砂石小路通向褚黄色的二层小楼,道旁的苦苣已经结成果实,冠毛白色,风吹即散。宁夏路、颐和路、江苏路那一带靠近学校,读书时我们常常流连,那些小路最绕人也最迷人。黄墙黑瓦,藤蔓爬壁,蔷薇科的花木杂生其间,花时必奋力怒放,引路人停留注目。时有猫悄然潜行在落满松叶的屋顶或围墙上,又突然隐没。
一楼的书房是师生彼时的聚集地。夏日,谭先生坐在藤椅上与学生说话也是说课,师母送瓜果来,也坐在一旁听。午后暑热,他们边扇扇子边说话。谭先生常用一把羽毛扇,其他人多用寻常蒲扇。宁先生的扇子与众人的都不同,是绣制团扇,细考可能是出自哪位名手。宁先生穿用考究却不自知,有次被古典文献的一位老师打趣了以后,她过一日竟穿了男式的亚麻西服过来听谭先生谈课,据说是她父亲的旧衣改的,也很让同学惊讶了一番。谭先生的小女儿,他们的小师妹当时在读高中,偶尔也会下楼来。她扇扇子的方法很有趣,总是倒着扇,扇面向下,几分顽相,这位师妹后来嫁给了谭先生最后带的学生。
天下的美人多矣,读中文系的人,是读着《洛神赋》心生眷恋,经由文学娇养了挑剔的审美,语言构建的想象更无边际,宁先生却诚如《玉台新咏序》中所言“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大家对她偶像之心既生,因此也不敢冒犯,不过镌成青春的美好回忆。大三的时候,美术系的展览,有一幅画是宁先生做的模特,众人就纷纷传说了这罕有的事,后来果然画画的人成了宁先生的丈夫。也听说,她和她先生是少年时就认识的,不过在大学时重逢。她天性纯良,为学专注,留下来读研究所已经小有成绩,大概她那时候天赋既好,年纪最轻,心性沉静,确实很早就现出了未来的开阔气象。
日头转,黄昏至,与路先生告别,走至暮色四合,路灯亮起,身影跟随步履沉默不语。在这个城市我度过了七年的光阴,始终有幸在先生身畔,对先生的眷恋景仰,也影响了自己的很多选择。本科论文我写了《谢朓诗研究》,是因为宁先生本科论文做的是谢灵运的研究。如此在和先生同样的年纪,宁先生做“大谢”,我做“小谢”,以为也是致敬。记得也是差不多的黄昏,我把厚厚的一叠打印稿拿去给宁先生,她仔细看了目录,收好放在包里。我跟随着宁先生走出研究室,走下紫红色木质扶手的楼梯,从中文系主楼面东的正门走出来,走过长长的中轴通道,雨后湿润的空气里早桂的暗香浮动,潮湿的路面落满黄山栾树的细小花朵,沿着台阶一步步走下去,直下山走到主路,道边草地几株红花石蒜在暮色中亦见色浓,是所谓的花叶不相见的不祥之花。正是秋分时节,阴阳之气浮沉交替,日月晨昏长短更迭,我与宁先生道别,她乌发蓬松,脸庞轮廓秀挺,有神驻的荣光,只是我目光落到先生拿着包的手上,看到她极瘦削的、疲态尽显的手,方觉察光阴原来也追逐着我的先生。也是那天,宁先生告诉我,做一位学者,要一辈子的努力,会有很长一段辛苦的路,可也是快乐的路要走。
后来如愿跟随宁先生读研,宁先生让我去做钱牧斋的研究。她最早和我说到的是绛云楼失火一事。钱牧斋在《赖古堂文选序》中写道:顺治七年,初冬之夜,他与柳如是的小女儿和乳母在楼上嬉戏,不慎打翻烛火,酿成大火,付诸一炬的有他苦心收集的史料及《明史》手稿。钱牧斋说这本书稿是他“忘食废寝,穷岁月而告成”,他说这一场火是“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
想起和S君在旧书店的那次偶然,是所谓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我一开始诚然是看不上钱谦益的,是因为宁先生,我开始去读他的诗作,并由此承继了宁先生的清诗研究的道路,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了那一刻我是被宁先生选中的人。在研读之后,钱牧斋的海纳鲸吞与沉郁博丽吸引了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城市满街的公交车站牌都是电影《柳如是》的海报。人们谈论的钱牧斋是以年迈之躯迎娶年轻歌妓柳如是的钱牧斋,却不知两人“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的和鸣,人们谈论钱牧斋是谈论因为水太冷而不肯自杀殉国的钱牧斋,却不知他一生“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的憾悔。出演钱牧斋的是耳顺之年依然长着多情面孔的秦汉,更让钱牧斋与传说中的形象重叠。可是他其实是一代文宗,黄道周被清军杀死前,说钱牧斋没死,国史就没亡,世人曾经如此深重地寄望他。我曾不齿于他的降清,后来我知道人生在于选择,而选择后的痛苦更逾于选择前。降清后暗中支持反清义举,却屡屡失败,入清后修《明史》,却遇绛云楼失火。如此再读“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是非常凄然的。
我读了他的诗文,并且也懂了他的斯文之时,也是该和宁先生告别的时候,为了方便照顾祖父,我选择了回北方读博,自此和宁先生分别。我们分别五年后,她离开了人世。
先生的形貌在我头脑中如此明晰,最鲜明是她的眉目,先生有古典式的长入鬓角的秀眉,眼神沉郁,像藏月落星的深湖。这五年聚少离多,我本性又是一贯敏感克己,很少主动与先生联系,除了新年亲手写下卡片寄出,在手机联络很方便的时代,我也几乎不去打扰先生。记得祖父患病,犹豫着去同她说,想要回北方读书,先生只点头说她理解。可我心内总觉得惭愧,当初一腔热望跟随先生,现在却好像是背离。后来几年跟着先生推荐的老师读博士,做了一些有影响的发表,也因此得到了去研究所的机会,看起来勤奋,心里念念不忘的不过是不想辜负先生。
初到研究所,我年纪尚轻,专业不错,看起来会有光辉前程,但常觉不安。刚去时,经常陪着一大群教授高才生喝酒,看着他们大谈道德仁义,互相吹捧,每次吃饭都是坐着煎熬。忍不住一次写信给宁先生倾诉,过了几日,收到一个快递,打开是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布裱盒子,外观像古书,再打开里面并列着一对镶嵌在红木上的竹雕对联,红木和竹的表面,有微微隆起的弧度,保持了竹的天然外观,对联写着“尚有清才对风月,便同《尔雅》注蟲鱼”。那是宁先生的字迹。按《庄子·天下篇》的说法,每一门学科都有“方术”,而在其背后都有一个“道术”,即是真理。世人常常在乎方术,因方术易得,也容易兑换成现实利益。玩弄方术者多矣,而道术才是一个学科的秘密。谭先生当年受困,18年的光阴,安于陋室,做了仅正集就有八十五卷的诗稿校注,并将诗文中的典故、人物、地理等等一一注释。追索秘密的人,亦是怀抱希望的人,在个体所能专注的微小空间,宿命性地投浸,书写的是给自己的答案。
从中文系拿回来的资料里,我看到宁先生55岁生日时,中文系给她做庆祝会的录像光盘。因为宁先生生日前夕得到一个重要的政府奖项,系里给她开表彰会,在表彰会结束的宴会现场安排了学生推出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把表彰会变成生日庆祝会。那场活动我也在场的。看到屏幕上宁先生出现,再听到她的声音,一贯的低沉和婉,心里有物理性的痛感。蛋糕推出来时,宁先生少有的表情失色,但只是一小会儿,一贯的教养让她很快恢复了常态,她体贴地拥抱送花的学生,得体地致谢。一切完毕下台,她回到座席,身边是她亲近的一个女性,是她早年好友的女儿,也在中文系工作,一直陪在她左右。在录像里,我看到了当时没有看到的情形,宁先生,我体面文雅的先生,喜怒不形于色的先生,身体微微倾斜靠在那個女性的肩畔,脸转过去,蓬松的发遮住了面孔,瘦削的背脊颤动着,俨然在落泪的,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足以被影像记录。
彼时的宁先生,在业内已经获得了至高荣誉,达到名望的巅峰,亦是桃李天下。可是,16年前谭先生就已别她而去,6年前韩先生就已别她而去。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粹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人的形体既不能比山川自然,总易消亡,所求的是否是精神的传递呢?留下仁爱学养,留下美好的名誉,影响更多人,这些,是我的先生做到的。做学生,宁先生是好的学生,她继承谭先生的衣钵,保护他的研究和志愿;做妻子,宁先生是好的妻子,她因韩先生的病,放下所有,陪侍三年;做母亲,宁先生是好的母亲,一双儿女都很出色,与她平等而亲密。她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没有逃离她的角色,极力完成。但现在,她只有一个人。
谭先生去世后,中文系在主楼前的草坪为谭先生做了立像,出自美术系吴先生之手。谭先生旁边是五年前就立在那里的唐先生的像,像造得精微,两位先生姿态之间有所呼应,似信步于此,驻足闲谈。草叶之间,植着几株山麦冬,春日纤细花葶上绽着细小的淡紫花朵,秋日花落成果,圆润结实,一扫柔姿,春华秋实,年年如是。
这以后宁先生花了两年时间,整理谭先生的遗稿,将他的诗作和研究文章按卷分列,做成全集,从誊录到校对一人完成。宁先生为谭先生画过一幅画像,那幅画也被收在文集里。画布上,谭先生目光沉静,表情宁和,手臂和额头的老人斑清晰。看着画像,也好像跟随着宁先生的眼睛,看着恩师,由壮年而年暮,看着生死之墙,在珍重的人面前逐渐变得稀薄,变成一道门,而他随时会穿越过去,走向那不可逆的旅程。宁先生自青年时代跟随谭先生读书,承其衣钵,既得全力爱护,亦以坚韧未有辜负,师生同志,未曾有隔。而生死无量,未知生性敏微的宁先生,如何堪受。
十年之后宁先生离开学校,去国外照顾生病的丈夫,亲送他离开,三年后回到国内,恰我与她相识。记得深秋的一日,晨课,我们在教室等候宁先生,她却少有地迟到。我离开北楼的教室,去往主楼的研究室找她。潮湿的空气凝成清冷白雾,周遭一切皆不真切,我步上主道的台阶,匆匆地走,却不经意瞥见浓雾中的草坪上一团身影。我走过去,看到正是宁先生,她伫立在谭先生的像前,额发已经被雾水濡湿,面容怆然,不知道她已经在那儿站了多久。一起走回教室的路上,她说,今日是谭先生的忌日。
教养拘着我们的举止规范里,种种克制,唯死亡一项,没有正确的方式可以指导。在我遇到先生时,正是先生最艰难时,她依然分出一点又一点光给我们,纤细而饱满。可是作为只懂得仰视先生的年轻学生,怕妄断、怕冒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更不能帮助先生的。
夜不能寐,妻子觉察,起身伴我,看着城市永夜不落的灯光在窗帘上游走。妻子说,你知道我最早什么时候喜欢古文的吗?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早晨的课,语文老师给我们读《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觉得太喜欢,那时候的生命正像那新生的月,于潮波中升起,皎光铺洒,无限可期,诗里就是自己,有愁也是少年愁。再年长些,读“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已能懂得生命的暮光晚景。我们生命的四时原来早已写在了诗句里。
我的妻子也是读古代文学的学生,她硕士毕业后在某古籍出版社的北方分部工作,与研究所有些往来,我们于是相识。我们第一次一起吃饭,坐下闲聊,却谈到了谱系。我的老师是宁先生,宁先生的老师是谭先生,谭先生的老师是著名的周先生。我妻子的太老师是和谭先生同拜在周门的一位老先生,谭先生在专业颇有成就,得到大名,而他这位同门在东北教书,不太喜欢写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名气。可他的学生成了我妻子的老师。我在这张神奇的图谱上找到了我和她小小的坐标。对于第一次见面来说是迂腐的对话吧,可是我们认真的讨论多少有其真心。妻子是灵心丰富的人,毕业后放着通途未走,选择这个职业,日常工作多是在各种图书馆影印珍本,让它们再现,让它们被传递。
那些年,在北方的城市,虽蜗居斗室,心内的乾坤自如自在,似与现世无涉,总能有一些平静。我们各自走过很长的路才相遇,彼此都是独居也能安排好自己生活的人。我向她提出婚姻的请求,意外顺利地获得应允。结婚后,我们换租了一套大些的房子住在一起,房子里一半是我们俩的书。没有婚礼没有新婚旅行,我的师弟为她画了一幅画像,她线条温润的手指上,有我给她戴上的戒指。
记得求婚前不久,她一次出差去外地图书馆影印材料回来,我去火车站接她,她背着有半人高的背包,身量却不高,形容瘦削,显得这个包尤其硕大。她背包里,有所有的工作材料,洗漱用品。回去地铁上,她很平常地和我说起她的旅程,乘过夜的火车,下火车后去旅馆开小时房,洗澡整理,换上得体的衣服,寄存行李,去图书馆处理事务,再返回旅馆,换上方便的衣物,回到火车站,乘过夜火车回来。她总能把困难的事做得从容体面,毫不狼狈。乘了一夜火车在我面前的人,在清晨的日光下,尤其清洁的气质和清澄的眼睛,是我心内热望开启的源头,若有一生一世,希望是和这样的人一起度过。
我的妻子每年都会应时泡果酒,再分成小瓶装,仔细封口,用泡沫纸包好,寄出一箱给她的导师。我有时逗她,这样烦琐不如买昂贵名酒送达导师。她说这门功夫也是老师教的,泡酒是老师和师母的每年乐事,只是他们年岁大了,不一定方便,自己泡好送去,总是一点惦念心意。说起来,她的太老师和谭老师都系出名门,却自成逍遥一派,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得到一种道术去为学,和得到一种道术去生活,道理上却也并无二致,是不能言清道明的内容使我们彼此得到确认。
宁先生去世以后,北方的天空疏阔,季节的流转鲜明,人世间的万千场景再与我的先生无涉固然使我伤感,最让我难过的一刻,却是一日看到“寿限无”这三个字,眼泪滚滚而落,我的伤感,我的软弱,都无法再抵御。寿限无,无限寿,多美好又多天真的愿景。死神携着镰刀在路的尽头等待收割,路的长短无法知道是所谓的寿无量。寿限无不属于我的先生,也不属于我先生的先生,也不属于我和妻子,它是對人世之路的无限延续的祈愿。有生之年走过的时日,像捡起粒粒细石铺就的道路,日月星辰之下有了作为人的痕迹,可最后一粒石子总会悄然落下。
宁先生那位好友的女儿是我后来访问的第二人,也知道她们是亲如母女的关系。宁先生的一双儿女都在国外工作,生前在国内这几年,宁先生与她更亲近。
她说,我的母亲是那种很大气的人,很爱结交朋友,本城几乎半数名人都来过我家客厅。宁老师是母亲的挚友,虽然两人性格迥异。我是很喜欢宁老师的,那种想法从小孩子时就有,比如说,会想如果我是宁老师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从小孩子的虚荣心来讲,是因为宁老师比较好看也比较温柔,我的母亲个性就比较爽朗直接,甚至不拘小节。她边说边要笑起来。
她说,两家住得很近,都住在教职工的公寓。爸妈忙起来双双不在,我和哥哥常常也会去宁老师家吃饭的,她做饭很好吃,且很有科学精神。我们那会读书就知道华罗庚的时间统筹法,她就是践行者。我有时去她家时,她还在书房工作,戴着眼镜出来迎接我们,很快她的一双儿女也回家了,她的儿子比我还小一岁,却能自己去幼儿园接妹妹一起回家,从小就很独立的。她去到厨房,同时做好几个菜,每个灶头各有分工,一会儿就能吃上饭。菜的色彩、餐具都好看,小孩都能感受到的,她过得很细致,非常吸引人。
宁先生在这个城市独居的十年时光,她从宁先生处听到很多过往。坦然把生命的碎片逐一交出,也是人在老去,在生命和死亡犬牙交错的时光里常常的选择。
宁先生和她的先生是少年相识,韩先生其实是宁先生嫂子的表弟,是看海吃饭的渔民家的小儿子。他们相识于宁先生大哥的婚礼,那是少年的韩先生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踏上铺着地毯的礼堂,婚礼的宴会,宁先生和韩先生第一次见到。再见面已是5年后,他们在同一所大学重逢,宁先生是出身不俗的天之骄女,韩先生是前途未知的寒门青年。宁先生的父母怕她会因这婚姻受苦,后来宁先生带着韩先生去拜访了恩师,谭先生与宁先生的父母说:“我看这个年轻人,除了穷点,没什么不好。”才使良缘得成。
23岁的宁先生,大学毕业读研究所,跟随谭先生做清诗研究。23岁的宁先生,嫁给了韩先生,直到韩先生去世,两人延续了26年的婚姻。宁先生生下小女儿第二年,有出国访学一年的机会,宁先生本已拒绝,韩先生却和她说:“你当然要去,出去看看对你总是好的,你现在不去,以后孩子大了更难。”于是,宁先生第一次去国离家。
在外访学的那一年,韩先生在国内照顾两个幼儿,宁先生却踏出了人生的新途。她修炼经史的功夫已经纯然,此时是连接外物,打通脉络。她接触最新的海外汉学研究,知道仅仅章句训诂,碎义逃难,会使中文研究成为现代学术的化外之地。她纠正以前研究的徽实有余,游刃不足,讲中西哲学会通,移用西方文学理论来丰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诠释。差不多十年后,两个孩子又先后面临申请出国读书事,从语言预科,到递送申请,事务烦琐,多是韩先生操心,后来,到底牵挂孩童,韩先生办理移居,出国陪伴儿女读书,自此夫妇两人聚少离多,直到生命终点前的几年才团聚一起。青年时的韩先生在毕业的画展上颇受瞩目,他以点彩笔法描摹的渔村晚景很多年后都被同学记得。他后来的创作,停在一个小小的世界。他为宁先生的每一本书作封面和插画,为孩子们留下大量记录家庭生活的画作。他去世后,宁先生为他做的小型画展里,有一幅母亲抱着孩子的绘画,以他最擅长的水墨与碳笔绘成,深深浅浅的灰白色调和晕染的柔光里,水墨线条勾勒的女性怀抱纯白襁褓内的婴孩,不见眉目,唯脖颈低下、脸颊贴近婴孩的温存与眷恋。
所谓夫妻,是互相陪伴的人,宁先生和韩先生皆不是善于交际的人,格外相互倚赖。宁先生每每在书房工作至深夜,韩先生和孩子已经在床上睡得酣然,几乎占满床铺,宁先生在韩先生脚边,靠近床尾的地方蜷睡。夜里朦胧触碰到那个温热的身躯,心下于是安然。很多年后,韩先生去世之前几日,身体似有好转,不用护工帮助,亦能独立行走,她原以为是好的迹象。一日他晨起去卫生间刷牙,她到底不安,跟随过去,帮他拿毛巾杂物,从他的身边经过,手指无意轻轻拂过触碰到他的背脊,几日之后,韩先生就故去了。宁先生与友人说,那触感,好像一直停在指尖上,从未离开。
26年,平常来说尚且谈不上半生,却因为生命的短暂,成就了韩先生承诺给宁先生的一生一世。韩先生去世后,宁先生一直随身携带一个古董鼻烟壶,里面放着他的一把骨灰。她独处的漫长时岁,并非总是朗朗乾坤、友伴围拥,而是有独处,有夜晚,有病痛,有衰老。按照世俗的规制仪礼,送走至亲至爱之人,流合适的泪水、道合适的话语,手指尖停栖着最末的身体记忆,亦揉化入骨血,是为共生。录像上,宁先生背过身体,微微颤动的肩胛,总在我面前。
今日,我的先生也赴了死亡的邀約,多少不忍不愿我也不能重新书写那一刻,挽住时光,去留下我的先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一个人来过又离开,这个世界轻轻晃动一下,什么永远失去了,什么又留下了?人能在什么地方留下痕迹,能证明孜孜的一生不全然是徒劳,不全然是荒诞?
寿限无,它在我心内属于我的先生,它在我先生的心内属于她的先生。在此刻死亡的诡计被终结,人作为注定的失败者,有的不再是等待审判的恐惧。所以我的先生,可以细腻地画下她的先生脸上的老人斑,可以把她的先生的骨灰携带身旁,死亡以物理的方式无限接近她,而她选择领受。
再一次,从中文系主楼的台阶下,拾步而上,经过草坪经过谭先生的像,走到中文系的正门前,仰望赤色匾额上谭先生手书的题字。夜天澄碧,秋草欲萎,虫声哀诉,我再不能遇到我的先生,是记忆把她生命的部分留下来,与我共存。佛教的唯识学讲阿赖耶识,埋藏着一切种子,末那识通过它生起种种“境”。我想起我的18岁,宁先生的课堂,是先生牵动了我内心埋藏的种子,领我走到这里,开启我的可能,注定我的局限。我既不怕迂,更不怕腐,我希望我的宿命也成为我的骨血,腐更彻底,直到骨体消解与岁月同化。我身边有妻子,我的前路有先生,我却不觉得很寂寞。
责任编辑 许泽红
朱婧,青年作家,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江苏文艺“名师带徒”计划签约作家。出版有小说集多部,2019年出版小说集《譬若檐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