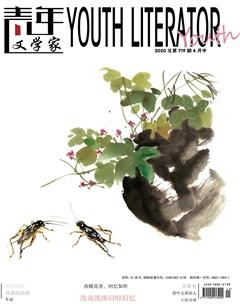浅析《岛》和《面纱》对生命的诠释
裘庭 潘雯 陈轶 倪风玲
一、引言
疾病的产生与发展是自然界的生存与毁灭永恒的话题,人类对它的认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疾病是人类永不可逃避的问题,它牵动着人类的喜怒哀乐以及悲欢离合,人们在治愈与不可治愈之间会呈现出复杂的情感变化以及社会关系变化。而从文学的角度看,作家们似乎很喜欢以此为引叙述故事,它是社会风貌的载体,能够让读者重回那个时代,是激荡人类情感的重要途径。在20世紀80年代,人们开始对疾病叙事进行研究。随着人们对卫生健康的认识不断提高,文学中的疾病叙事也越来越受学界关注,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的特征之一。疾病题材的文学数不胜数,本文所选取的两部文学《岛》与《面纱》均是疾病题材中为人熟知的作品。《岛》采用的疾病背景为麻风病,而《面纱》是以霍乱为疾病背景,两部作品中情节的起承转合几乎都与它们自身的疾病背景相关联。本文将以疾病叙事为视角,浅析疾病叙事手法在《岛》与《面纱》中的作用,探究作者是如何运用疾病叙事达到对生命主题的深层诠释。
二、疾病叙事的类型和背景
亚瑟·克兰曼( Kleinman,1988: 3)指出: “疾病叙述就是与疾病相关的描述或陈述。狭义上的疾病叙述仅指病人对于自身疾病的描述或陈述; 广义上的疾病叙述则泛指文学作品中与疾病相关的描述或陈述,这种描述或陈述不仅仅止于疾病本身,还包括病人、与病人相关的医疗服务、家庭成员、人们对于病人的反应等方面”[6]。本文正是聚焦于其广义含义之上。
小说《岛》以麻风病为线索,讲述了希腊一座死亡之岛―斯皮纳龙格岛上发生的故事。原本它也和布拉卡岛一样,有温暖的海风和湛蓝的海水,有开满鲜花的山坡。它之所以让人闻风丧胆,是因为二战期间被设置成为麻风病隔离区。由于当时医疗技术的落后,政府只能对麻风病人采取强制隔离措施,来自希腊各个地方的麻风病人都要被迫遣送到这接受隔离。吉奥吉斯就是靠运送货物到斯皮纳龙格为生,有时候也需要运送病人。吉奥吉斯妻子伊莲妮原本是一个受人尊敬、兢兢业业,深受学生喜欢的教师,也正是因为她有种磁力把孩子吸引在她身边,才染上麻风病。命运似乎总是捉弄人,吉奥吉斯心善的小女儿玛莉亚也不幸患上麻风病,面临着和母亲一样的命运。作者通过描述这一家族遭遇麻风病的困境,来引发读者对生命的思考,揭示生命的意义。
与麻风病一样,霍乱也是战争期间较为流行的传染病。《面纱》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霍乱盛行的地方―梅潭府,男主人公沃尔特是一位医学博士,也是细菌学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但妻子凯蒂的私情让他十分恼火,他决定带上妻子一起去湄潭府工作。这里的城市街巷空空荡荡,路人也都像鬼魂一样,没精打采。绝望和恐惧笼罩着这个地方,唯有医护人员奋斗在最前线。修道院也被征用为救治病人的地方,医疗室里挤满了垂死的病人,凯蒂脑子里一直忘不掉医疗室里传来的那凄厉恐怖的惨叫。在湄潭府待了一段时间,凯蒂渐渐地开始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修女们和丈夫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关爱让她开始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从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到加入修女们的护理工作,那个生活在舒适区不思进取、嫌弃丈夫、屡次偷情的她,在梅潭府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思想转变了,心智也更成熟了。作者以霍乱为背景,通过描写凯蒂心境以及行为的变化来剖析生命的涵义。
三、疾病叙事方式
疾病叙事方式包含了叙事人称、叙事视角、叙事顺序以及疾病叙事特有的疾病隐喻。在疾病叙事中,作家所选用的叙事人称和叙事视角对于故事疾病叙写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着叙事的效果。
《面纱》中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叙事视角,例如女主角凯蒂在睡梦中被敲门声吵醒,她以为是沃尔特在敲门进而产生的一段心理活动以及她后来被告知沃尔特感染上了霍乱的心理活动。在这段描写中,我们会跟着凯蒂的视角进行想象空间的视觉与场景切换,并且体会到凯蒂的整个心理变化过程。正是因为第三人称有限叙事视角的有限性,使其强化了此片段的紧张氛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增加了疾病续写的真实感。而《岛》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一使用也是与其作品内容有关,《岛》讲述了一个家族几代人对抗麻风病最后战胜疾病重获新生的故事,这也就意味着它有多位主人公,同时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使用,作者可以从全方位展现各个人物形象以及设计故事情节,这使作者可以更好地掌控疾病叙写的方向与整体发展。
在这两部小说里,作者都使用了多样的叙事顺序来进行疾病叙事。小说《岛》中作者通过佛提妮向阿丽克西斯讲述阿丽克西斯家族的过去引出故事主要情节,就是采用插叙的方法来进入故事主线。反观《面纱》,其故事的开头是凯蒂与查理在凯蒂的房间里偷情,凯蒂因为听到门有动静而受惊吓,在知道开门的人正是她的丈夫沃尔特时,故事随着她的回忆回到过去。这一段倒叙介绍了凯蒂所处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以及她与沃尔特相识结婚的过程,既解释了故事开头凯蒂之所以会出轨的原因,也为后文二人婚姻破裂一起前往湄潭府埋下伏笔。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都使用了预叙手法。预叙指在事件发生前就对事件进行叙述。在《岛》的结尾处,“现在一切真相大白,伤口暴露在空气里,但最后有可能治愈”[2]预示着索菲娅将不会再逃避家族的麻风病历史与伤痛,获得她自己的新生。而《面纱》里凯蒂决定陪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在故事最后提到“是一条通向安宁的路”[1],预示着凯蒂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崭新人生之路。这样的预叙手法使这两部作品的疾病叙事达到了它们对生命涵义的深度剖析,也能给人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事物,在英语文学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深受广大学者的喜爱。作者以此形式,感知、探索、理解、讨论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文学领域中的疾病,不仅仅指的是疾病本身或其病症,还具有其他特殊的意义,隐喻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便是疾病叙事中特有的疾病隐喻功能。例如,在《彩色的面纱》中霍乱隐喻人心的迷茫、折磨和挣扎。文章中曾多次描述到患了霍乱的病人们的呻吟声、喊叫声,“仿佛不是人发出的痛苦的声音”[1]。其实人们内心的感受和变化也是如此。女主人公凯蒂刚来到湄潭府,内心也是痛苦的,既有对查理为了前途拒绝和她结婚的伤痛,还有对霍乱的恐惧但又无地可去只能来这的无奈。在韦丁顿第一次来沃尔特家做客时,对凯蒂在这个极为敏感时期仍然吃生食沙拉感到十分的诧异,并告诉她吃生食可是湄潭府的禁忌,可凯蒂依旧平静地吃着。“我觉得你把那几片生菜叶看得太严重了” [1]以及“你看着我的脸,告诉我是不是我的鼻子有点偏长”[1],凯蒂通过幽默的话语以及自嘲的方式转移话题,但由此也可以体现其内心复杂的情绪,吃生食时的冷静不仅是想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沃尔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盖自己对霍乱的恐惧。与此同时,男主人公沃尔特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他深爱着妻子,但也因她的背叛,想利用麻风病夺走她的生命。就这样他在“善”与“恶”中苦苦挣扎,尤其是在得知凯蒂怀孕以后,这种折磨和挣扎更加明显。
《岛》中的麻风病则隐喻人性的两面。当马洛里得知未婚妻玛丽娅患上麻风病后,一时间并不是在乎未婚妻的身体状况,而是在乎自己是否受到了感染,并且在玛丽娅去了斯皮纳龙格道以后和她断了联系。玛丽娅的姐姐安娜得知这件事后,想到的却是“如果妹妹没有得麻风病,就会嫁给马洛里”[2]、“如果玛丽娅的确得了麻风病,就会立即影响她在范多拉基价的地位”[2]以及有些暴徒们甚至企图乘船带着汽油洗劫斯皮纳荣格岛,这都体现了人性的自私与丑恶。将视线移往另一方,玛丽娅的父亲、朋友、医生一直陪在玛丽娅的身边,甚至还到玛丽娅在斯皮纳龙格的新家中做客,他们并非不畏惧麻风病,只是他们对玛丽娅的爱克服了这一切,这无疑在歌颂着人性的善良与真诚。
四、疾病叙事:死亡的对立面是生命
一部小说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对人物的刻画,特别是在人物性格上突出的善良与丑恶才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兴趣。如在《岛》中,伊莲妮善良伟大的形象植根在读者心里。伊莲妮是布拉卡岛上的一名小学教师,她关心爱护每一个学生,也深爱着她的丈夫与女儿们。她几乎具备完美女性身上的所有气质,然而这一切都被当时所为人厌恶和惧怕的麻风病毁了。伊莲妮不得不离开这个家,去往斯皮纳龙格岛,一个几乎没有希望与亲人们再见的地方。她独自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承受着与家人离别的孤独感,可见她是多么顾全大局。即使是最后她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再也无法离开这个岛,她依旧不忍看丈夫难过,只是说:“我的喉咙有点疼,可我相信只是感冒了。”[2]读到这里怎么能不让人为之感动与不舍呢。就如《面纱》中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她曾经是一名贵族小姐,她本来只需安稳待在家里,与母亲学好礼仪,无忧无虑地过这一生。可她选择皈依宗教,愿意来到一个霍乱肆虐的地方,照顾一群与她毫无关系的人。特别是当她看着昔日与自己一起来到这儿的姐妹们相继死去,她也没有退缩,仍然选择坚守,继续照顾患病和被抛弃的孩子。她的这种大爱让小说的女主人公凯蒂找到心灵的归属,得到心灵救赎,也让这本带有悲情色彩的作品焕发出一丝人性的光辉。
不过,能让读者引发共鸣的是阅读一些丑恶的面孔,从而揭发社会的丑陋,批判人性,达到警醒的效果。通过分析《岛》与《面纱》两部作品,其中更多篇幅描写的是人们对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的恐惧和对患病者的疏离与冷漠。而这种情感在这两部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首先,拿人们对待传染性疾病的不同态度来看,《岛》中描写的麻风病人都将送往斯皮纳龙格岛,这是一个充满孤独与死亡感的地方。克里特岛上其他的正常人对这个岛充满了畏惧与憎恶,甚至想直接将这个岛摧毁。他们被麻风病人经受过病痛的可怕傷疤所吓倒,认为这种疾病是很容易传播的。这样的谣言愈演愈烈,“暴徒们计划驾着手头上所以渔船,在夜幕下登陆斯皮纳龙格。”[2]他们打算冲上岛烧死那些麻风病人。但据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麻风病是低发病率的,且其病毒具有潜伏期,可能感染十年后才会发病。但霍乱不同,霍乱的传播途径广、速度快、死亡率高。这一点可以从《面纱》描写一家人都因霍乱死去以及路上时不时就会有抬棺的人的情节中体现。但在湄潭府驻守的官员没有离开,修道院的女修士们没有离开,甚至连害怕死亡的凯蒂也不想离开。从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高下立现。
生命是高贵的,人都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命运有时恰恰喜欢捉弄人,在这两部作品中,命运让凯蒂来到霍乱肆虐的湄潭府,麻风病使玛丽娅不得不登上斯皮纳龙格岛。凯蒂的偷情事件被沃尔特发现,他处于报复心理将凯蒂带去湄潭府,这对凯蒂来说无疑是绝望的。来到一个毫不熟悉且传染病蔓延的地方,并且带她来这的人对她只有恨意。她恐惧,绝望。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真正认识到自己以前的行为以及品质是多么的令人不齿。慢慢的,她感受到周遭的环境如此,却依旧有人为之做出贡献,渴望改变,认为自己也应该为之尽一份力。对玛丽娅来说,斯皮纳龙格岛是曾经母亲待过的地方,她从这能感受到母亲曾经生活的样子,找到母亲的影子。在这里,她感受到那些虽受麻风病折磨但依旧乐观向上岛民们的热情以及他们积极地找寻治愈方法,并且将斯皮纳龙格岛建设成一个民主文明的城市的坚定信念。正如“理查与朱蒂”电视俱乐部里所说:“即使在那个污秽荒凉的不祥之地,也总能寻找到灿烂的鲜花。”看似绝望的背后酝酿着希望和向上的力量,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思索,给予人们正能量。
五、结语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生命是一条艰险的峡谷,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通过。”生命是脆弱的,在疾病面前更加不堪一击。本文选取疾病叙事的独特视角,结合两部作品中都与疾病脱不开关系的主人公,分析其人物性格,从中引申对生命的感悟。在《面纱》中凯蒂对生命真谛的感悟就像揭开生活一层一层的面纱,她从无知愚昧慢慢成长为一个为人考虑的女人。她懂得了沃尔特的爱是默默的,虽不热烈但却深情。《岛》中的玛莉亚从来就知道生命是可贵的,却又很脆弱。所以她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她为家庭的和睦发展努力着,她为自己能够活下去奋斗着。她们是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历程。她们都经历过令人丧生的可怕传染病,她们都目睹亲人离世,她们都遭遇爱情的背叛,最后她们都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各种磨难,或大或小,或喜或悲,有些人活一世也找不到生命的价值。生命需要人体会,需要人的真正经历,才能懂得它的真谛。《面纱》与《岛》中的人物大多经历过可怕的疾病,所以他们更能懂生命之可贵。
参考文献:
[1]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面纱[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2]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岛[M].陈新宇,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9.
[3]魏玉杰.英国小说与疾病[J].外国文学评论,1994(02):135-136.
[4]金琼.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疾病叙事及其伦理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18,40(05):72-84.
[5]杨梅.浅析毛姆小说《面纱》中的叙事时间[J].青年文学家,2018,(36):153.
[6]郭棲庆,蒋桂红.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研究——以《夜色温柔》为例[J].外国语文.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