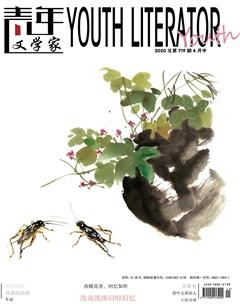宇文所安《典论?论文》的突破与局限
田文瀚
摘 要:宇文所安所著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一部结合中国文论英译与跨文化研究的著作。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文论研究,宇文所安将西方的文本解读方法运用到了中国文论的解读与研究中,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宇文所安着眼中国文论中体现的问题意识与作者的内在思路,提出了迥异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观点。并从曹丕的王子身份入手,还原其写作时的心理活动。从曹丕本身王子的身份入手,其在写作时的心理被得以还原。但从另一方面看,因为宇文所安的异文化背景,并且与中国的文学传统以及学术传统存在一定的距离 ,因而难免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宇文所安;中国文论;《典论·论文》;曹丕
对于中国文论的研究是宇文所安的主要研究分野。从对于文论的解读方法来看,不同于中国学界对于文学“外部”的研究,宇文氏主要从中国文论的作家“内部”入手,着重对于文论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相应的解读。相对于中国学界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宇文氏所关心的问题是抽象的。远离中国的学术傳统使得宇文氏可以脱离中国学者的许多桎梏,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作品,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中国文论对于宇文氏来讲只是佐证自己观点的论据而已。《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首篇独立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是中国古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开端。同时,这部著作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多角度论述的文学理论著作,是中国文论的经典文献。
宇文所安的观点中,个体的局限性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基本主题。这种个体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文非一体”的文学观点,文学中有诸多题材,大多数写作者很难做到齐备。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写作者都是只具有一技之长的,很难做到“通才”的水平。而正是写作者人自身的这种局限性,使得文人群体具有一种偏颇的观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即“文人相轻”的文学现象。宇文氏对于曹丕提出了质疑,这位王子慨然评论当世之文人,将自己视作通才,这种缺乏自省的批评精神也恰恰可以证明,作为当时文坛翘楚的曹丕把自己视为“通才”抑或是“君子”。宇文氏认为,曹丕对于自己的认知明显具有自我想象的色彩,带着一种王子的自信。出身决定了曹丕生来便是一个“君子”,因而在文章开篇他便可以用一种自视甚高的角度,发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的品评。作为未来的君王,它具有绝对的权威带着帝王的傲慢,理直气壮地发表有关文章写作的宏论。
其次,宇文所安指出,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一观点。“文以气为主”的提出证明了对于文章写作来说“气”具有的重要作用,而“不可力强而致”则是阐明了对于一般写作者而言,“气”并不是能够很容易获得的。甚至这种“气”也不能够在血缘中进行传递,表示这种根本性缺陷,几乎是无法弥补的。曹丕认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这种现象的存在,削弱了文学作家进一步克服自身局限的可能性。
最后,曹丕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明自传于后。”在曹丕创作《典论·论文》的过程之中,他一开始便具有帝王君子的姿态,然而随着文章的不断推进,曹丕陷入到了自己创设的文字之中,并受到了触动。宇文所安认为,“论文以一种轻视文人的调子开始,瞧不起他们为争得帝王的宠爱而相互贬低;可文章却以敬畏文人所取得的成就作结,政治的力量最终让位给写作的力量了。”导致这种让位的,到底是什么,宇文氏给出了他的答案——死亡的恐惧。曹丕作为未来的帝王,权力是它能够握在手中的,然而人的寿命却是有限的,这是历代君王都无法避免的焦虑。曹丕不可避免地产生疑问,世间的东西自己已经尽有,然而死亡消解了个体所拥有的一切东西。最终他抓住了“文章”这一救命稻草,用文章流传后世的“不朽”消解这种死亡带来的深深恐惧。
可见,宇文所安不同于中国学界对于细部以及“外部”的研究,他深入到了作者的内心。为什么曹丕具有品评当世文人的自信于自觉,宇文氏从曹丕的出身着眼,指出这种王子的独特身份,以及与生俱来的“君子”身份给予了曹丕这种自觉地意识;而随着文章地推进,宇文氏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这一观点地提出与曹丕畏惧死亡的心理息息相关,因为畏惧死亡地降临会剥夺个体地价值,曹丕将人生地价值归结到不朽的文章之中,借此来消解自身对于死亡所产生的局限性。这种细腻的心理揣摩使宇文氏获得了不同于以往学界的视角,为当今学界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发。笔者认为,对于文本进行心理解读的方法,不失为宇文氏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突破。
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远离导致了宇文氏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局限。首先,宇文所安在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之中忽略了曹丕本人的另一重身份,曹丕不仅是未来的政治元首,同时也与父兄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其自身的文学素养十分深厚。笔者认为,曹丕在品评当世之文人时所体现出的自信甚至自负,与其自身的文坛地位与文学修养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关联。是政治地位、文坛地位加之对于自身文学修养的自信使他充满了自信,慨然相评。
此外,关于写作的动机,宇文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曹丕对写作的动机做了修改,从他的话中我们尚不能断定,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希望自己为人所知(例如仅仅为了成名,或希望他的才能为人认可,或希望他人在某个更深层的意义上了解他这个人),但可以确定的是,希望为人所知就是一种强大的动机。在曹丕看来,这个动机是危险的,它容易使人堕落。曹丕是王子,作家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可他看到的偏偏不是任何天才或特质,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为人所知的欲望,以及这强烈的欲望如何使作家丧失了公正的判断。”笔者认为这段叙述表明了宇文氏在中国文学素养上存在的欠缺,其一,对于语句的理解宇文氏存在一定的偏差,曹丕在谈及写作动机时只是用了“患”这一词语,所谓“患”,最直接的意思时隐患、祸患,进一步可以引申为“为某事所危害”。而宇文所安却运用了一个更加生硬负面的词语——“堕落”。这个词语的运用使得文本的文意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将这种“局限”进行了过分夸张的放大,笔者认为这与原文存在一定的偏颇,值得进一步商榷。笔者认为,宇文所安在对于中国文论的翻译过程中受限于本身的汉文学水平,存在着利用现代汉语对译文言汉语的缺陷,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对于“君子”这一概念的解读,宇文所安将“君子”解释为“国君之子”明显与中国的汉语传统存在偏离。
宇文氏的另一个局限性体现在其对于中国文论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中国文论的英译版本大多只是以材料论据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对于文本进行细读式的肢解与分割使得文章从整体变得破碎。笔者认为这样人为的割裂文章的整体架构,一味对于文本进行过分的细读,势必会造成部分的过度解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文学作品的本意。在以往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主要对其论点做四重划分:作家论——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之关系;文体论——四科八体;文气论——文以气为主;文章论——关于文章价值的论述。宇文所安对于文本的研读与心理分析虽然大致遵循了这三部分,但又在这三部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了拆解,并逐句进行踹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宇文所安在对中国文论的译介与研究时存在一定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将西方文本解读的方法融入到了中国文论的研究之中,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与突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