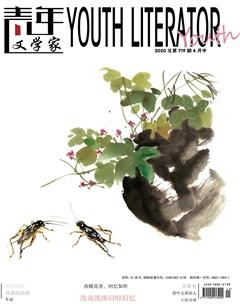生活往事忆小姑
璩存峰
今天,一个人独处,感受着周围侵入肌肤的冷气,俯瞰地面还未融化的积雪,抬头仰望蓝天碧宇下流动的白云。这时,我仿佛看到小姑驾一片祥云向我走来。原谅我不避长者讳,她的乳名就叫“云”,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小姑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她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有时也出现在梦中。距离她去世的时间越久,对她的思念越深,这种思念如根,深深扎进我的心田。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打针打怕了。只要从窗户看到进院子的赤脚医生,我就赶紧顶住房门,插上门闩,哭着,不断地央求着:“爷爷,我病好了,不用打针了。”小姑也哭,安慰着我:“就打这最后一次,打完就好了。”每一次,敲门与插门僵持的时间有长有短,最后都以我的嚎啕大哭而告终。小姑就会抱起还在抽泣的我,去看院外的杏树。看花褪残红的小小青杏,看躲在叶子底下、与叶子同色、不仔细看就难以分辨的拇指肚大的杏子。麦子泛黄,杏子也黄了。这时节,小姑就要去割麦,收麦了,看我的,换成了奶奶。
农村的树,也是拴马桩。今天,骡马仰头扯下片叶子;明天,黄牛啃下快树皮;后天,毛驴往树上蹭蹭痒:几年的光景,这株伴我度过童年的杏树,变成了真正的拴马桩。遮风挡雨的时候,牲口们不念杏树的好;风吹雨淋之时,牲口们恐怕也有悔之晚矣的内疚。
冬季是农闲时节,可公社也不让老百姓闲着,时髦地喊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深挖沟渠,兴修水库,大搞水利会战。个头不高的小姑也跟着队里的壮劳力,到工地干重活。常常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回来走上十几里地,也不觉累。晚上洗脚,皲裂的口子疼得她直吸冷气。奶奶心疼,也没办法。
印象中,小姑就打过我一次。一天中午,我看她从外面捎回两个凤梨给奶奶。奶奶没舍得吃,就暂时放在了柜子里。下午,我趁她们不备,就偷吃了一个。小姑察觉后,我还装傻充愣地不承认。她来气了,说:“你偷什么偷,你奶奶吃好东西,哪次没有你的份?”在我背上拍了两下,奶奶赶忙阻止。那也是唯一一次见她凶巴巴的。
我要上学了,该起啥名呢?暑气渐退的夏末,晚饭后,一家人席“炕”而坐。小姑说:“我看叫‘锋(后来改为‘峰)就很好。你看人家‘雷锋、‘华国锋,一个是名人,一个是领袖。多好?!”父亲、探亲的叔叔都没吭声,大概他们心里觉得也有道理。奶奶和母亲自然更没意见了。我的名字,是不识字的小姑起的。
家里穷,买不起供销社卖的本子。小姑就把冬季封窗棂用的白纸给我裁开,用线缝成32K或16K大小的样子。有时候也用灰色的纸,用铅笔写上去,几乎分辨不出字迹。我可能也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每当小姑晚上看不真切,裁剪得不够整齐时,我就气恼地喊她的乳名。她哭不得,笑不得,打不得,反倒是奶奶批评我几句。
本子金贵到什么程度呢?冬天早上,到外村上学。为避凛冽的西北风,我们常常猫腰躲在沟底走,碰到结冰的水面,也欢快地滑冰而行。大概觉得离村远了,一个高一级的男孩子就会拦下我们,让我们每人给他撕几张纸。否则,他就分化瓦解,让我们乖乖就范。
四年级下学期开学之初,班里转来一个城市女孩,她给过我一个蓝实线的方格本。本地只见过红格或绿格的,就觉得这个本子简直是天外来客,珍藏了很长时间。直至现在,碰到漂亮的笔记本,尤其是印着某某大学字样的,我还会买上几本留念,不管路途多远,行李哪怕再多。
农活的劳累,物质的贫乏,挡不住农村男女老少渴求精神食粮的脚步。只要是四邻八村放电影,小姑就会带上我,和伙伴们一起,走过沟坎,涉过溪水,越过阡陌,去看屏幕上的外乡人是如何生活的。去的时候,走得匆忙,是怕晚场;结束的时候,走得匆忙,是因为天色已晚,怕耽误第二天早起干农活。我现在还喜欢看电影,习惯恐怕就是小姑给养成的。
我上初中,小姑嫁到了邻村。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过。我在他们家吃住过一段时间。经常会见到一位比我奶奶年龄还大的老人,在那吃住。那是姑父的奶奶,她的老婆婆。不知为何,老人不愿意和她的儿子、儿媳一起过活,也不愿意到她大孙子那去,就愿意在她二孙子和孙媳妇这里。姑父和小姑就怕怠慢了老人,好生伺候。
初三时,有一天傍晚,回家后,母亲让我去接小姑回来。我问为什么这么晚还去接,母亲说小姑生下不足百天的孩子夭折了。我见过那个小孩,长得很漂亮。我明白母亲是怕小姑受不了,接她回来住几天。见到我,小姑就哭了,我也掉泪。我忽然觉得我长大了,生平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小心地骑着自行车,生怕把小姑再摔坏了。记忆中,那晚走得格外漫长。长大之后才明白,死了亲骨肉,做母亲的,死了的心都有。我非常感谢母亲,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作为女人,她知道小姑的苦。
父亲在潍坊打工,奶奶去了北京二大爷家,两个弟弟还小,母亲忙里忙外,听力还时好时坏。我是小姑唯一的倾诉对象,那夜,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印象最深的是奶奶叮嘱过她的一项任务。
这项任务跟大姑有关。大姑嫁人后,接连生了两个女孩。这让思想保守、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公公、婆婆接受不了,他们不是指桑骂槐,就是怂恿小女儿去闹事。作为家中独苗的大姑父就拿大姑出气,甚至大打出手。这成了奶奶的心病,她就让小姑每逢赶集,去跟大姑村上的人打听,大姑近期又挨打了没。小姑其时还未出嫁,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只好抛头露面。为了不引人注目,她穿一身黑衣服,用头巾包着头,就像地下黨员似的,去完成奶奶交给她的光荣任务。赶集次数多,也就习惯了。大姑近期没有遭受家暴还好说,如果是坏消息,小姑就犯难了,一路上搜肠刮肚,琢磨来琢磨去,想好说辞,她不想让奶奶难过,只能自己躲到一边去落泪。有时,奶奶多少也能猜出个大概。
可怜天下父母心。奶奶、大姑、小姑,她们母女连心,都宁肯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也不想另外两人受委屈。我内心真不是滋味,可又能怎样呢?我去替大姑出气,狠狠地教训姑父一顿吗?当初父亲弟兄几人都没有了断的心结,我又怎能圆满解决呢?那一刻,我为她们母女三人的命运而伤悲。“隐忍”是我们这个家族继承得很好的一个传统。
小姑家的耕地在我们村附近。大学暑假的一个下午,小姑干完农活来家,我正好在大门口迎着她。喷农药是农村最苦最累最脏的活之一,稍不留神,还会带来生命危险。小姑满头大汗,衣服也湿透了。闲聊了几句,小姑就要回去。我有点纳闷,平常至少洗几遍手、擦擦汗,甚至吃块西瓜再走的。她转身的那一刻,我明白了小姑为什么执意要走。只见肩背上的喷雾器将她勒得又瘦小了几圈,让她尴尬的是来了例假,一条裤腿已溽染得通红。汗水、药水、血水已让她变成了一个水淋淋的“苦”命人。我流泪了,为她,为普天下普普通通、任劳任怨的农村妇女、母亲。为了从土地里讨生计,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她们早早放弃了多少属于女性的自尊和权利。挺着瘦弱之躯,干着甚至比男人还累的农活。要之甚少,得之甚少,却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工作成家后,她偷偷地告诉我,以后给孩子起名,不要叫“赛”,因为这是奶奶的名字。我生了女儿后,她像是安慰,又像是欣慰,说依我的比较绵软的性格,生个女儿好,生个男孩我可能管教不了。我工作十幾年后,她也像她那个年龄的农村妇女一样,当起了奶奶,享受天伦之乐了。节假日,走亲访友,有时碰到她在街上,领着孩子,和街坊邻居说说话,唠唠家常。为了子女,为了生活得体面一点,操劳一辈子,现在也该享享清福了。我这样想,也希望这样的景象地久天长。
四年之前某一个秋末冬初的半夜时分,一阵电话铃声让我猝然惊醒。这几年,考虑到父母年龄大了,我一天24小时开机。难道?电话是大姑打来的,说小姑9点多钟住院了。大姑语气平静,听上去小姑好像也没什么大碍。应该没有什么大事,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因为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我还和小姑通过电话,还和她开过玩笑,劝她注意休息,她心情还很不错。
早上我赶往学校的路上,大姑问我走开了没有,她已经掩饰不住她的悲伤了。我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眼泪已不受我的控制,仿佛内心深处有一潭千年泉水。问题最终还是出在“累”上。原由是,小姑家地里种植的树木成材了,买方只要树干,树墩和树枝都顺便给留在地里。我村的一个妇女跟她说:“姑,您如果不要,我们就拉回来当木柴。”这让小姑感到紧张,三天时间,她泡在地里,既没有好好吃饭,也没有好好休息。弯腰,低头,抬头,直腰,就是这些简单的、连续重复近三天的动作促使她的血压慢慢地上升。
小姑原先就血压高,生病前谁也不知道。这次因为急着往回拉树墩和树枝,她忘了自己还是一位高血压病人。第三天傍晚,总算收工了,她又去给帮忙的伙计们张罗下酒菜。估计当酒菜准备妥当的当儿,我恰好给她打电话,亲侄子打来电话,她自然非常开心,就和我开心地聊了几句。9点左右,她感到疲劳了,跟小姑父说到床上歇一歇。估计这时,她的脑干开始出血,让她陷入头晕、昏迷中。再叫,她就不醒了。等11点送到医院,出血面积就扩散开了,极度昏迷,类似于植物人。闻讯后,她的散落在北京、吉林和黑龙江的亲人都回来了,遗憾的是,小姑再也感知不到亲人们对她的爱了。
小姑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了一周后,还是去了。生前,她从没有与之红过脸的儿媳、女邻居个个都哭得很悲伤。生前,她曾经跟我认真地说,她没有了时,不要为她而哭泣。是的,以前我也天真地认为,只要在长辈健在时,好好地孝敬他们,让他们颐养天年,在他们百年之时,本人可能就会心情好受一些,悲凉也不至于浓得化不开。现在看,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俗话说,血浓于水。我们和他们是一脉相承,早已经休戚相关,骨肉相连,心灵感应,魂魄同在。
我们常常说,如果有来生……不要来生,因为来生太过虚幻。我们就要把握住现在,珍惜当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有时间,我们多陪陪老人和孩子,不要找借口,不要说没有时间。更何况生活中常常有意外发生,就像这一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状病毒肺炎,又让多少家庭顷刻间变得不再完整,让多少老人生命终结于这个寒冷的冬天。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这一刻,再去“赋得永久的悔”。
就像奶奶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我们仍旧记着她的好;小姑离开我们四年有余,我们仍旧想着她:她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就是平凡人追求的永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