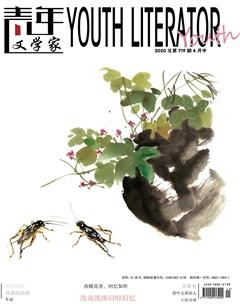你好,旧时光
作者简介:曾培(1992.11-),汉,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人,硕士,四川工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儿童文学、幼儿游戏。
作为90后一代,我们曾经被认为是出生在歌舞升平年代,有强烈自我表达欲望,脑筋活跃,追求快速高效,爱闹爱玩,有梦想和理想,喜爱前方和远方,不愿停下自己追逐脚步的一群人。然而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我们就“奔三”了,我们不再那么叛逆,不再那么青春热血,我们开始变得安静,变得沉稳,也学会了在注视远方繁华世界的同时转过身来回望我们的来处。毕业工作一年多,逐渐捋清楚工作流程之后有了一些闲暇,开始回顾自己过去的时光,发现在家乡度过的那些年,是藏在我脑海最深处,最简单、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我的家乡在四川盆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庄和大多数的农村村庄一样,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很贫穷,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就在这个平凡的小村庄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
温柔娴静的小河
一条清澈碧绿的小河缓缓地流过我居住的村庄,将村庄一分为二,它是那么的安静,听不见流水声,如一位远离俗世喧嚣温顺的少女,和寂静无名的村庄一样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安宁。是河都有源头,但河水天天流,却没有人见过小河的源头,据说,有人曾循着河水的踪迹逆流而上去探寻它的发源地,可最后都無功而返。传统的河岸人家都知道河水养人,这条小河用它甘甜的河水养活了河两岸的村民。在农村,姑娘嫁人,河边的人家都是首选,我的母亲就是因为这条河而嫁给我父亲的。河水除了可以作农人灌溉洗涤之用,渔人还可以养鱼,鱼不需要人工照料,在开春气温升高之后将鱼苗放进河里,等一两年鱼长到两三斤重就可以打捞了,如果想等鱼长大一些,可以再等上一年。河里的鱼都是自然生长的,没有放鱼料,鱼肉鲜美可口,每到打鱼的时候,河两岸都挤满了买鱼的村民。记得有一年天大旱,村子里有许多水井都枯竭了,河里也没剩下多少水了,来不及细致的规划,渔人慌慌张张将河里的大鱼打捞上来就划船去其他河流抢鱼去了,留下许多漏网之鱼。等到河水见底时,这些漏网之鱼在泥坑里活蹦乱跳,吸引了一群大人和小孩提着鱼网结伴去捞鱼,大人在前面用网打鱼,小孩子背着背篓跟在大人后面去捡鱼。河里的淤泥软绵绵,自然禁不住人们的踩踏,一个人踩到河里的淤泥陷进去,一大群人都跑去拉,于是一大群人都陷进淤泥里面挣扎,场面热闹而又壮观。
肥沃丰饶的田地
田地是农人的希望,农民们在田地上得到的恩赐是数不胜数的。人们吃的五谷杂粮,家禽动物吃的野菜瓜果,药用的名贵药材无不受到田地的滋养。我家有几亩田地,有一小块专门种蔬菜的自留地以及种庄稼的耕地,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田地是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童年时代不知道田地的诸般好处,只知道耕地的诸般艰辛以及消耗玩耍时间,因此极度厌恶下地劳作。春天地里种大豆,总是“草盛豆苗稀”,母亲常常会让我和她一起去地里锄草,刚开始兴致盎然,晨起就跑地里拔草去,可拔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嫌烦了,于是就越来越磨蹭,想要离开,母亲比较严厉,要求不拔完不准离开,这个时候心里憋着火气,嘴上不停地自言自语嘀咕,为什么要分给我家这么多的地。有一年九月份,母亲因为刚生了弟弟坐月子不能出门,父亲又肩负着一家人的生计,必须外出打工,收割地里两亩即将成熟的玉米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身上。那个时候我正读初二,周一到周五留宿学校没办法收玉米,只能周末的时候收,周五回到家匆匆忙忙做完作业,周六周天就到地里收玉米去,用一个周末收完玉米,再用一个周末把玉米秆杆割掉。那几天每天早上很早出门,忙到傍晚日落西山,而地里的活儿看起来始终不见少,心底里就很烦躁,又开始抱怨为什么自己家要有这么多的田地。近几年,家乡的田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庄稼地被征用,修成了宽阔的乡村公路,现代化的养猪场,休闲娱乐的广场,还有一部分田地因人们外出务工而变成了荒地。村庄里的人们对田地的感情日渐淡漠,大部分的人都不再指望着这块地的粮食养活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单纯简朴的生活也渐渐远去了。
住着鬼怪的树林
小孩总是爱幻想的,童年的我也有许许多多的幻想。在我家耕地旁边有一片树林,里面长着许多大树、灌木和杂草,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见人进去过,自己也不敢进去瞧一瞧,于是对它充满了好奇。比我们年长的哥哥姐姐对我们说里面除了有蛇、老鼠之外,还有鬼呢,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鬼,尤其是中午一两点或者天黑以后,地里面没人的时候,鬼就出来了,专门吃小孩。哥哥姐姐们的诳骗,再加上看了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聊斋》,于是对树林里面住着吃人的鬼这件事深信不疑,对这片神秘的树林更加充满了向往,自己就想去看看鬼到底长什么样。一个夏日的午后,下定决心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探险,我们背着自己画的几道“灵符”,手里拿着大木棍,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树林边上,正想进去的时候,从树林里传出了乌鸦的叫声,我们吓了一跳,停下了脚步,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说话,就这样僵持了好久,一个小伙伴鼓足勇气建议谁胆子大一点,谁先进,大家推推嚷嚷着还是不敢走进去,最终我们放弃了。这一放弃,就再也没有了下文。等到再次走到树林边上,我已经毕业工作了,树林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生气,大树也老了,不再像个威武的战士耸立着,而是被风吹着东倒西歪,叶子也掉光了;灌木丛被农人砍了当柴烧了,草也枯黄了;站在树林边上就能看到林子的尽头,神秘感荡然无存。本来打算进去看看,但是现在知道里面是没有鬼的,也就再一次地停下了脚步,对于之前没有鼓起勇气走进这片树林始终有一种遗憾。
偷东西的小孩
相信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偷”过别人的东西。“偷”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或是没有成熟的地瓜,或是快要红的番茄,或是绿皮的橘子,或是黄了的柿子……“偷”东西是孩子之间的一种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农村物质缺乏,小孩子几乎是没有零食吃的,“偷”来的东西可以满足小孩的口腹之欲;此外“偷”东西是要冒险的,正好激活了孩子的冒险精神。首先,不能让大人们知道,所以只能在大人们午睡或者天快黑了的时候进行。地瓜和番茄一般是七八月份成熟,柿子是十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大人们一般都会午睡,所以这些时候的下午一点之后我们就会行动起来,一般三四个小孩一起,人太多了容易被发现,人太少了又不敢去,三四个小孩正合适,一个小孩把风,一两个小孩摘果实,一个装果实。橘子一般是冬天才会成熟,一年冬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一起去偷红橘,天快黑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成功地把红橘偷回来了,但不知道藏在哪里,这时候发现地里堆在一起晾晒的棉花秆,一摞摞的放得很整齐,我们可以在它们中间拨开一个洞,那就是藏匿战利品的好地方。于是赶紧把橘子往棉花秆里放,没想到我刚放完橘子一转身一不小心就跪在了一堆人的粪便上,原来这也是农村人在野外上厕所的好地方,瞬间忘记自己的小偷角色大哭起来,最终引来了大人,偷橘子的事情也暴露了,不仅没得到安慰,还被骂了一顿。如今,人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孩子们有很多零食可以选择,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冒险,不需要“偷”东西了。
柔情的大舅
我的大舅出生农村,一生生活贫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读完初中就外出务工,三十岁结婚,结婚不到三年就丧偶,独自养育一个孩子,没过几年外公又去世了,还要帮着外婆照顾五个弟弟妹妹。苦难的生活使得大舅丧失了脸上的笑容,用独断强势以及近乎不近人情的语言来武装自己,撑起一个家。没有笑容的面孔以及尖酸刻薄的语言使得孩童非常怕他,不愿意接近他,但与之接触多了,慢慢发现在他坚硬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柔软细腻的心。大舅喜欢种果树,在他家的院子里种有好些果树,大门前有两颗鸭梨树,院子左边有一颗秋月梨树,院子的右边有两颗水蜜桃树,院子中间有些李子树,橘子树。每年到了水果成熟的季节,大舅家的果树都被沉甸甸的水果压弯了腰,这么多的水果,他重来不卖,除了自己和孩子吃,全部都送人了,村民走路渴了就去院子里摘两个果子吃,与友人聊完天摘几篮子水果相送,哪家小孩馋了也任由他们自己摘,至于自己的亲戚更不用说了,每年都用背篓装最好的水果送到家里,我家每年都会收到大舅送来的水果。我小的时候,农民们经常自己制作猎枪去山上猎野兔,大舅也会打猎,记得有一次,大舅在山上呆了好几个晚上才打到两只野兔,他没舍得吃,走了二十几里路送了一只兔子到我家,我第一次吃上了野兔肉,后来再吃兔肉,都没有大舅猎的兔子好吃。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和母亲都外出务工了,我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比较忙,我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上学放学,而别的同学的父母经常到学校接送孩子,我特别羡慕。一天下午,大舅来学校了,说是顺路来看看我,在学校的小卖部给我买了一些零食,临走时还不顾与他同行的人的阻拦给了我一些钱,这在当时对三年级的小孩来说是一笔巨款,我瞬间觉得自己在同学们面前很有面子,也不再羡慕其他的小孩了。现在想想,大舅在我家这边除了我,也没有熟人和亲人,也没有要办的事,怎么可能顺路要绕二十多里路呢,他分明就是来看我的。民间有一句歇后语“刀子嘴豆腐心”形容大舅再贴切不过了,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爱着身边的人。
童年和家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人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即使人们离开故土,走向远方,人们的心绪也会飞过千山万水,回到这最初的地方。我爱家乡的一草一木,我爱家乡的父老乡亲,我爱我那温馨与酸楚相交织的童年时光,就算时间过去了十年,我都是那个扎着麻花辫,在田野间蹦蹦跳跳的孩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