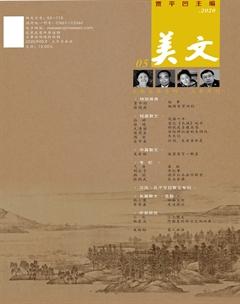沿江而行
李育善
六
丹江冲积,两岸形成了较大的平地,特别是从商州黑龙口到丹凤的竹林关。河水舒緩平稳,地势开阔肥沃,是有名的商丹盆地,素有商洛的“鱼米之乡”之美誉。
每到夏季,丹江两岸是成片成片的水稻。那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正是这里真真切切的感受。
为了能多打粮食填饱肚子,为浇好稻田,沿岸的不少村庄都发生过抢水的冲突。
1991年谷雨过后,商州市(现在商州区)三贤乡郭涧村和西间乡的郭村,因抢水浇地发生群体性打架斗殴事件,双方参与的群众达300多人,打伤村民上十人,推倒多处围墙,烧毁不少麦秸垛。
2017年7月22日上午,我们路过丹江边的紫荆村来到郭涧村。紫荆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就在紫荆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考古发现,文物大都收藏到省博物馆。遗址文化表明,这里是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豫西一带的河洛地区和鄂西北地区等不同地域原始文化相互交汇的地区。找到郭村原来支书郭民的老房子,因修高速路早已拆掉。十六年前,我在刘湾街道办工作过,这里各村家家户户,都跑过不止一次。如今来变得连路都找不到了。这儿已经成为商洛高新区,宽广的亚迪大道从原来的稻田穿过。郭涧村子涧下面的稻地也变成了一排排徽式民居,三层楼。从南朝北第三排,找到了郭民家。他正要和妻子一块进城给女儿送蔬菜,见到我们,他让妻子赶忙搬凳子,烧水沏茶。等我们坐定边喝茶,边说话,他才让妻子先去乘公交进城,他陪我们。
说到那次抢水的事,他说:“妈妈爷呀,连鬼子进村了一样,从山上黑压压一片扑下来。到村里又是烧麦秸,又是推墙,又是打人。”他还留有当时的照片,从柜里翻出来让我们看:麦秸烧的狼藉不堪,老人打的惨不忍睹。
事发的前一天下午,郭涧村人和郭村人都到丹江河边堵水浇秧苗。郭涧村在上游,郭村在下游。郭涧村人让郭村引水从河堤练外面走,郭村人却偏要走里头,这样就要占郭涧村的地,郭涧人自然不答应。连夜晚郭村人就密谋着上郭涧村打架的事儿。
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太阳出的红红的,郭村人一溜带串从东面小山上冲下来。郭涧村与郭村只隔一个小山包。这些人进村见人就打,放火烧场里的麦秸垛,还推倒了郭民家的院墙。那次郭民的母亲受伤较重,主要是把人先吓坏了,多数人吓得躲起来。
“我听到门外喊喊叫叫,出去一看,大事不好了,人把我院子都包围了。一伙人喊‘掀了支书的院墙,看他狗日的还张狂不了,那伙人一哄而上,喊着一、二,就把土院墙掀倒了。我妈看见了,吓得浑身哆嗦。”郭民如今说起那天的事儿,都心有余悸。
郭民赶紧派人到沙河子区公所和三贤乡报案。区公所在丹江北岸,乡政府就在村西边。等区上和乡上人到了,闹事的人都跑完了。村里群众气得骂区上领导,还给人家脸上吐唾沫,郭民把领导往屋里拉,被人从后面踢了一脚。事情没处理成,区上领导就住院了。他随后到医院看望,被领导痛骂了一顿。后来因工作不力,郭民被开除党籍。两年后,社教团驻村没人管事,又让他入了党,第一年当村长,第二年就又当支书。
原商州市农工部、水电局、信访局等单位派人驻村一个月,调查处理此事。我作为政府办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调查。记得群众见到我们,开始也是围攻谩骂。知道我们是来处理事情的,这才配合我们开展工作。郭涧村被打受伤的人住了几天院回来了。只有郭民他妈受伤带惊吓住了十几天医院,老人当时六十二岁(2015年老人过世)。派出所把带头打砸抢的人拘留了好几个。
郭村又是郭民的舅舅家所在的村子,堂舅表兄弟也不少。郭民也很理解地说:“那时都是为了集体,亲戚也不顾了。后来,河床下降了,稻子也不种了。两个村子关系也好了。现在建开发区、修高速路,地也征的不剩啥了,人均不到一分的菜地。”
我在这里工作时,郭民才四十五六,很能干,能吃苦,也很会算计。记得一次组织全地区地膜洋芋现场会,光地膜他就为村上多要了不少。想想都是为了这个村集体。现在郭涧村、寨坡村、生王村三个村合成了郭王村。郭民也不当支书了,他笑着说:“无官一身轻了,过去那场闹事,其实伤的也不重,只是影响不好。想想都是为了村上的事情,个人之间没有啥,都是亲戚朋友哩么。区上那位老领导也退休了,见了,还骂我说郭民这贼怂,把人就淘咋了。”
和郭民分手,我们又跑到郭村,想见见那位当年带头闹事的人。如今也应该五十多了。联系到郭村一位朋友,还在外地,说那人也在新疆打工,常年不回来。人也变好了,日子也不错。
丹江两岸稻花香的那些日子里,浇秧苗为水而争的事,过去是时常发生,不同的争执,不同的冲突,都有不同的故事。只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因水稻产量低,加之河床下切,几十万亩的稻地全部起旱了,成了麦田。
七
丹江从源头奔流90多里到商州区的张村,在这里流成向东北倾斜的大写倒“U”字型,王山底河就从U字的底部流入丹江。
张村土地平展,山坡多是土塬。过去人们种地,从河边一直要种到坡顶。现在25度以上坡地退耕还林,人们也改套种中药材。种桔梗、牡丹、黄芩、丹参等,啥赚钱种啥。种药、收药、贩药成了气候,在张村街上隔一两家就有一家药材收购门市部,你收黄芩,我就收桔梗,生意上相互关注,互不打架,这就叫有钱了大家挣。
也是仲夏的上午,我们来到张村街,这儿也叫瓷(祠,当地人叫成了瓷)里。同事小陈家就在街上。他爸算农村的历练人,过去靠贩药材养活一家老小,从商州到西安药材市场几乎天天雇车跑。生意好,来钱快,可很劳人。突然脑梗,成了半身不遂。人病了,脾气也大,见人只流泪,说话也不太清楚。当年走南闯北的厉害人,如今却成了个废人,自己心里那个坎先过不去。小陈他妈是个爽快人,说话嗓门高,说说笑笑,说到老伴,又是眼泪汪汪。楼房客厅东侧麻袋堆成山,全是中药材。看着老陈恓惶的样子,让人心发沉。好在小陈那会儿跑前跑后把啥都弄得很顺当,他妈就一个劲儿说儿子的好。
到王山底村,也建成了新农村,房屋红顶白墙,花园、鱼塘、游泳池,跟城里没二样。好几家农家乐门口,停了许多小轿车,陕A打头的也不少,看来西安来的客人多。河里也有橡皮坝,水里装了彩灯,水清清的,还能看见小鱼游来游去。小陈的岳父就在路边,他叫上老人陪我们看水库去。他岳父姓董,六十来岁,个子不高,精瘦,说话有点结巴,却很能说。他自豪地说:“别看这水库小,它却是商洛最早的,它是有户口的,在国务院上过的,二龙山水库大大的,它都没排上。”
老董也是贩中药材的。这生意也做了一二十年,啥人都见过,啥事都经过。他也是给韩国卖鲜桔梗商洛第一人。他通过看资料,知道韩国人的爱好,需要啥样的货,啥成色,都严格按标准收购。韩国商人只要一听说是西安的货,是老董的货,都会点头说:“OK!OK!”在他带动下,商洛的优质鲜桔梗大量销往韩国。用老董的话说,当时山东那个加工厂生产的鲜桔梗占韩国市场的百分之四十,这些大多是商洛的货。他笑着说:“韩国人也从桔梗中尝到了丹江水的香甜了。”他三女儿在那个厂子打工,一说是老董的女儿,大家都很器重。跟日本人也打了十几年交道。青岛的华中公司是中日合资企业,他给供柴胡、桃仁。一次还闹过一回笑话。他给发去8吨野生桃仁,对方一抽检说农残超标,先给退回4吨。老董心里犯叽咕:都收购的是野生的,咋能农残超标呢?根本没有用农药一说呀。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对方,不要了就全退回来也无所谓。过了一段时间,对方说弄错了,抽的不是他这批货。2004年、2007年日本人先后两次来商洛,他都接待过。老董说:“鬼子办事很认真,也很懂礼。”到2013年中日关系有些变化,中药材生意也不好做了。最后一回日本人来在二龙山水库农家乐招待。老董和那位日本药材博士就谝了4个钟头,他对商洛中药材习性的了解,让日本人直称他董老师。现在老董主要给市里一家医药企业供黄芩等中药材。一年下来也有三四十吨货,也值上百万哩。
王山底村边的河堤是1975年修的。过去上面碾子凹人到城里,都走河滩。那里出锑矿,当时人用担子担到河滩,再用架子车拉的转到公路边装车。小时候人常说山里人担的光子下来了,两疙瘩东西明光光,那就是锑矿。水库东边的山叫王山,这个山陡,也高,西边是园岭。农村人常说王山高王山高,王山搭到园岭半山腰。水库是1958年修的,蓄水不多,总库容才一百多万立方,坝高有30米,坝长160多米是土石混合的,属于小(一)型水库,重要是修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灌溉、调洪、涵养水源做了不少贡献。如今经过除险加固,水库也在安全地发挥着作用。
老董说,这河里的水是从石瓮沟流下来的。修水库时这上下村里都住满了人。当时全靠人力,架子车都是很现代化了。
碾子凹原来也是个乡,在水库上游,先是合到张村镇,现在统一都成了沙河子镇。上游还有团结村、钟峰村,现在也都合到王山底村。几年前孙见喜先生还带企业给钟峰小学捐过桌凳。在钟锋原村委会见到几位支教的大学生,说支教一个月,这里现在还有六十多名学生。
中午在老董家吃浆水面。他家院子很大,靠南边还有假山水池,养了各种鱼。院里还种有辣椒、黄瓜、西红柿。老董笑笑,说:“算吃算摘,生态有机没污染。让你城里人眼红吧。”看来他还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天气热,老董又是挪电扇,又是开空调。在家里他始终是家长那样自豪得意。农村人只要勤快,善动脑子,日子一定会过得像老董一样有滋有味的。
八
在商洛这块版图上,如果说秦岭是父亲山的话,那蟒岭和流岭就是它的左臂右膀。流岭在丹江南边,蟒岭在丹江北边,它们与丹江一样自西向东延伸着。这两岭孕育着丹江无数支流,丹江水里涌动的有它们的精灵。流岭槽是流岭山脉中最高的一个村子,海拔在1500米以上。村子南边翻山过去是山阳县的王庄。沟里的小河顺势北流40多里,在口前村汇入丹江。这里的集市在历史上多少还是有点小名气的。虽说是露水集(指开集到收集时间很短之意),也有上百年了,当时的人流物流不比一些老集镇差。
夏日知了叫的最欢的一天上午,我们从夜村镇口前村顺着两水寺河溯流而上。河面较窄,水声却大。小贾介绍,当地人常说看你灵性的,你是流岭槽人,看你外瓷的是姜庙人,过桥(指独木桥)拽住桥板都掉水里了。进到半沟里,路遇两位男人,他们是贾庄村人。志书上说这里是塔寺沟,一位老人却说叫塔子沟,也就是堡子沟。那山顶尖尖的像塔么。塔子沟的水和西沟的水汇合的地方,就叫成了两水寺,因为这儿还有个寺院。问流岭槽,说还有五六里路,那儿有个露水集还在,逢阴历的二五八为集日。贾庄村合到庙坪村。一位微胖的男人说拉网线到这里了,一天给80块。一直打电话,他没去,嫌那人没良心。他一天放一轱辘电缆没问题,早早就收工了。另一个瘦点的男人说:“你来了,记着把龙潭弄个啥叫开发一下么。”他说的是金鸡窝山下不远处两水寺河里的那个黑龙潭。大约有二十几个平方,水深有两米多,清澈见底,连小鱼游来游去的姿势也看得一清二楚。城里来游泳的人也不少。水从大青石上流下来,长年累月冲击形成了一个深潭。老喻一见水就激动,感动地说:“这么干净的水,不下去游太可惜了。”说着他三下两下就脱了个精光,“哧溜”一下就钻进水里。
村后堡子山上的石头是青麻石,能打石磨子。还有个金鸡窝,成群结队的红锦鸡在那里。太阳出山时飞出去觅食,太阳下山时回窝。这锦鸡是吉祥鸟,被老百姓叫金鸡,神奇的很,金鸡窝常年有水,干旱时,只要把窝里的水撩出来,天就下雨了。
1974年大队里搞副业打石磨子,放炮把金鸡吓跑了。那时一合石磨子卖40块,相当一个人两个月工资。金鸡跑了,水却一直流着。这二位男人,一个郭栓民,一个叫张存怀。老郭说是存怀他爷发现金鸡窝的。他爷活到九十多哩。张存怀说:“野猪把人害的没治呀,我两块子地苞谷叫一黑来给糟蹋光了。”郭栓民还说:“我在路上走哩,大中午热得野猪跑到河里喝水,也不怕人么。政府叫生态保护哩,害人却没深浅呀。”
从神龙潭沿河继续上行,到了木子沟和两水寺河交匯处,这里有一座老戏楼。从戏台上仰望,能清晰地看到檩上写着“清光绪五年建”的字样,距今也在130多年。戏楼对面就是爷庙,旧庙也是那时建的,早都不在了。近几年村民又筹资新修了。戏楼对爷庙是过去建筑的一大特色。戏楼房上雕梁画栋很细致,檐牙交错也肃穆。戏台上堆着苞谷杆,东边墙上黑板上是当年扫盲用的,还有粉笔写的教文化课的字样。又一片知了叫得很凶。戏楼边上住的小伙子说:“想申请保护哩,不知咋弄哩么。老来人哩,只是转一匝就走了。”小贾给留了电话,他和文物部门人熟,能给帮上忙。提到土地一事,老爷庙对面74岁老人杜忠全说,他是流岭槽二组人,这沟里河两岸的平地大多是农业学大寨时修的,庙前面这一带有上百亩,一人能分一亩地。有地了,吃饭也没问题。那时候的干部带群众一块修地,亲的连一家子人一样。说到流岭槽集,老人眼睛一亮,说:“现在没人了,过去人多的很很,山阳的,商县的,周围三四十路外的人都担着担子来,街里搁不下,河里人都挤疙瘩哩,人多的没样样么。”
我们乘车到了沟垴。见一位老年妇女坐在路旁的石头上,那女的看着蔫蔫的,她慢腾腾地说:“这儿是仰天池,翻梁过去就是山阳的南宽坪。”边上小桥上站着一位男人,他说话有点娘娘腔,他说:“集在下面两边盖一排排房那儿,中间窄窄一道子,现在也没啥集了。”我问啥时候集萧条的,他说:“木材不让上市后,就慢慢没人赶集了,也有二十多年了。”他接着说:“那时卖木材的人多的太太,岭南岭北的都来卖。有檩有椽还有担子哩,材方板也多。”
仰天池是两水寺河最大的源头,这河也是丹江南边一个支流,我掏出手机,没信号,却能查出海拔,这里海拔在1530米左右。山顶自然形成一个盆地,过去人放牛在那里喝水。下雨后,这里就像个水盆子,形成了仰天池,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的水一直都没有干过,现在放牛割草的人少了,池子里也长满了野草,水还是清清的。
那男的叫孙正民,61岁,他说,他们原先住在张村王那村,因缺吃的,老祖先才搬到仰天池来落户。开荒种地,种玉米洋芋,才能吃饱肚子了。仰天池下几条沟,过去住着170多户人,现在西边的孙家沟只剩18户,仰天池下也只有30来户,有搬到西安的,有搬到县城、镇上的。他两个儿子都在西安,一个在洪庆上门了,一个在那儿打工。老孙说:“娃叫去哩,不惯,还是咱这儿美,空气好,水好,熟人多么。”
我們返回来找那露水集,见一辆通村班车在停车场等人。车是白色依维柯,能拉二十多个人。说是停车场,其实也就是一片河滩地。司机叫王建波,四十五六,人也精干。他说:“到城里四十多公里,10块钱。按说应该收13块,到丹凤路好,差不多的路程,人家票价都15块。”他是商州区运输公司职工,问工资收入,他叹息说:“哪儿有工资哩,公司把车接回来,上好牌子,卖给私人经营,公司监管。国家给一个车一年油补贴3万元。这里的线路没人要,我还有个旧车,加上这个成本价50多万哩,挣不回来了。”老喻说当时应该调查一下市场,他说:“2009年买的,那时沟里人大多在家,到2012、2013年以后,人都外出打工了,没多少人了。”他说一天好了毛收入三四百,也刚刚包住工资,想转让没人上手。他在城里才住上廉租房,很无奈地说:“有一趟才坐三四个人,城里只要有一个人都得拉。四十分钟一趟不变。空放的时候也不少呀。”说到提票价的事,他摇摇头说:“2009年到现在了,不敢提价,一提怕没人坐了。”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走到车跟前,王师傅很热情迎上去。
在流岭槽卫生所前下车,打听集市在哪儿?坐在一家商店门口的一位老人笑嘻嘻地说:“现在不叫流岭槽村了,叫流岭槽市了,市长都选了几个了,有正的还有副的。我这门面开了30来年了,挣的钱还不够穿一条裤子哩。”旁边一位老大娘笑着骂道:“看你这老不死的,跟人家客胡说啥哩么。”老人笑着从店里搬出马扎凳,叫坐。
我们先沿街道走了一圈,街面只能开过去一辆大卡车,长也就是小伙子一泡尿从街南尿到街北。两边房子前檐都是一排木板做的墙。逢集时卸下来,用板凳支起来就是货摊子了。靠东北有一家“供销合作社”,是原先的乡供销社,也叫私人给承包了,今天没开门。东边中间后排房子一律是石头墙,也砌的四棱见线。在一个小巷子口上,有个小木门,面向南,门上是一把金黄色锁子锁着,上面用毛笔写着:早晚不误,全日营业,买东西,请叫门。字也很有劲,能看出是有点功底的,边上墙也是小石头砌成的。
返回来跟老人聊天。老人叫唐栓劳,76岁,在这街上做生意也有50多年,和一个朋友合伙在街口盖了这三间门面房。过去经营的还行,后来慢慢就不行了,把房子一人间半分开,各做各的。现在店里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百货,遇集日子了,来店里看着卖一点,等卖完了就关门呀。老人点了一支烟,幽默而有自信地说起流岭槽集的过去。流岭槽集在清朝时就很兴盛。当时,交通不便,四周的人都来赶集,把这房都挤得格摇哩(摇晃),集上卖啥的都有,木料、生漆、木炭、蜡、香表、背篓、镢头、铁锨、扫帚、衣服、布料、网套等等。小吃店买饭都要排队,有热豆腐、豌豆凉粉、红薯面饸烙、萝卜丝包子、红烧肉,主食有面条、锅盔。旅社天天都住的是满满。还有外省来的人。老人用手弹掉烟灰,说:“旧社会单片的,耍钱的,从来都没断过。”老喻明白单片的意思,是比放账的还要硬,能处理事情,也能放账。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意都好做着哩。后来,水泥路修通了,农村人盖楼房也不用木料了,加上国家不准乱砍滥伐,生意也就冷清了。现在逢二五八还开集,生意差远了。老年人闲的没事了,到集上走走转转,见熟人了谝谝闲传,回去都高兴几天哩。
说到石头房,老唐说那是财东家的,墙厚超过五十公分,枪都打不透。财东死后,儿子孙子都出去打工了,多年也没回来过。
这时又来了一个老汉,叫孙忠善。老唐笑着说:“孙子来了,有啥快问他。”老孙说:“这老怂没正经。哎,共产党现在好尽了,像我这老东西都拿上高龄补贴了。”老唐说:“高龄补贴谁都拿不去,保险也是硬的,谁也拿不去。孙子老汉唩球跟我这一样。”孙老汉反骂道:“你唩球跟谁的不一样么。”说的我们都哈哈笑了。又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问:“买本子呀,有没有?”唐老汉笑着说:“这儿有斧头,没有锛子。”女的又问:“要滚子哩,啥本子,滚墙的外么。”老唐说:“有碌碡哩,没滚子。”女的也开玩笑说:“那你拿来,我要哩。”老唐说:“叫几个男人来抬来么。”女人骂道:“把你这老怂,一辈子没个正经。”老唐说:“咋不正经了,摸你来么。”女人边骂边笑边走开了。
又过来一个小伙子,叫刘志强。大学毕业,回乡创业却遇到困难。小刘说:“你给上头反映一下我这香菇吧。区上2017年4号文件鼓励大学生带动贫困户创业哩。我做了三年了,一年2万袋,只领了一年的补贴一万元。现在一年不如一年了,赔的厉害。找区上领导,找农业局都没人管。”小刘原来在外面打工,卖电脑耗材,在网上看到国家提倡回乡创业,就回来了。这一创一下子投入十六七万。现在这状况,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出去打工还债。政策是扶大户,把小户拒之门外。第一年赔了一万,去年一万袋又没出菇,让他进退两难呀。小伙是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的计算机应用专业。我们也只有好言相劝,记下他的电话,尽力相助。小伙子连连给我们鞠躬,说:“要真能行,你们就是我的救命菩萨了。”
离开流岭槽街市,心里留下了些许伤感,想想那人声,那叫卖声,那热气腾腾刚出锅就卖的蒸馍,依然怀念那流岭槽昔日的辉煌。
九
夏日下午,我们赶到北宽坪镇广东坪村。这天深山也一样热,村里不多的人,在路边树下乘凉。有一家在路上和水泥打楼顶,一位老人給我们指了要找的颜家贤老人家。也在路边,楼门朝西开着,进门院子窄长,靠南边还有一丛竹子,靠楼门是厦房,连着正房。老人正在客厅吹电扇,后墙上挂着一米长的玻璃框镶着“世界客家大会”照片。老人84岁了,大个子,方脸庞。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高兴地指着照片说:“我在这儿哩,会三年开一次,这照片都13年了。”老太太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一说是记者,这才露出些许笑意,说:“来的人不少了,有中央的、省里的,还有画家哩。”颜老还知道他们是颜回的后人,唐代有个颜真卿也是他的本家。
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一沟两岭位州东,借问贵名何所故,只缘粤客居此中”,说的就是在这蟒岭山中,溪水边上有个自然村,迁住了一批广东人。这地方因此得名广东坪。过去还是个广东坪乡,现在撤并到北宽坪镇,成了一个大村子了。迁居到这里的客家人,少说也有两个多世纪。
这个村子离商洛市区有40多里。村子是南北走向的沟,有十来里长,沟有小溪,溪里有鱼,两边是农田,沟东西有两条山岭,山很近,站在这个山头能听见那个山头人说话。
村子过去叫杨家街,河叫杨家河,还有个露水集,河道两边还有商铺。乾隆35年(1770),颜、赖、叶、刁、罗等姓氏从广东平远县为躲避兵役迁徙到这里,颜、赖为大姓。来这儿开荒种地,建屋造房,过上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广东坪组、八亩坪组、板岔沟组,有上百户,500多人。他们各自祭祖方式不同。叶氏为南阳堂,赖氏为西川堂,颜氏为鲁国堂,刁氏为农红堂,罗氏为天地君亲师。
颜姓祖先原来住在平远县小拓乡韩坑庄,康熙己巳年(1689)分族迁徙湖南长沙府浏阳县东乡老鸦暇,住了81年后,一支三兄弟,从乾隆庚寅年至戊戌年(1770——1778)分三批离开东乡迁入这里。
颜老人说,听父辈讲过,好像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有一支广东部队进驻商州,这儿人叫“老毛海”。一天,有几十个兵跑到北宽坪执行任务,到了这里。村民听说队伍来了,吓得跑到山里躲藏。队伍进沟乱放了几枪,就没影了。乡亲们以为队伍走了,在山上喊话,问情况哩。这两边山岭上的一问一答,被休息的广东兵听得一清二楚。这熟悉的乡音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也用广东话喊叫。“我们也是客家人,咱们都是乡党,别怕。”一场惊吓被乡音刹那化成了一场惊喜。
颜老说,他们是颜回的82代子孙,祖先第一代叫颜怀赞,迁到这里也10多代了。老人收集有颜世家谱11本。排行在全世界都没乱过。在颜家堂屋祖宗牌位上,有祖先名号,牌位下端写“簋”“簠”,意思是祭器。他们祖先迁来时,带不了沉重的青铜器,就写个字表明敬重的意思。现在村里姓颜的17户。
老人还能说一些简单的客家话,大多数都不会说多少广东话了。如把“1”读作“鸦”;“吃早饭午饭晚饭”分别读作“食朝、食昼、食夜”,很有意思的。见面问候“路项(上)辛苦哩”、“食知饭么”。称呼上辈子为“阿公”、“阿婆”、“阿爸”、“阿姆”。饮食习惯也变了,在南方多吃米,现在以吃面食为主。用面粉做油炸“馓子”,就是把面条拉的盘起来干炸,出来金黄金黄,吃着酥而脆。还有“云云子”,名字也蛮有诗意的。客家人娶媳妇,是用花轿接,快到门口时,把犁地用的铁犁烧红,绕花轿转两圈,叫燎轿,是给新人驱邪避灾。到家门口,婆婆要站在大门口,手拿擀面杖为新媳妇揭盖头。
老人年事高了,说话却一字一板,也很淡定。他18岁当兵,在部队8年,在甘南、西藏参加过平叛战斗,后来从兰州又到朝鲜,干过报务员。无线电发报、汽车摩托、各类枪支,都很熟练。1957年到1959年,先后在青藏路、川藏路参加建设,因身体原因转业回到家乡。在区工商所退休。文化程度不高,编写过《工商志》。两个儿子一个干检察,一个打工,女儿嫁到渭南了。老两口把屋里拾掇得整齐干净。
老人又给我们添了水,说,逢年过节办庙会,唱大戏,把南方的地方小戏也搬过来了。这里也是民歌之乡,唱的《拜年》《马马歌》《张二女吵嫁妆》都很吸引人。耍社火也是歌伴舞。像唱孝歌号子《颠倒话》,什么“对门的坡上草吃牛,花园里的萝卜吃了猴,姐在房中脚抱手。门上来了个客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起来咬了狗”。 幽默有趣,叫人听了没有悲伤感,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新民歌像《团结歌》《妇女盘哨歌》《生产歌》等,演绎着爱党爱国的热情。群众还有自发组成的锣鼓队,随时都能表演。
村上也把教育娃娃当成大事,一百多年前就办有学堂。解放后,出了10多名大学生,还有博士。重视伦理,遵规守法,五六十年了没出过一起刑事案子。
小贾开玩笑说:“颜回脑子灵,人也好学,孔子老人家最喜欢。”老人也多少有点自豪地说:“颜家祖上把贤把仁很当事儿的。”说到镇安,还有商州三岔河的姓颜的,老人说都是从这儿搬出去的。
这里也是“客家灯彩之乡”。灯彩表演是客家山乡的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也是陕西第一批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坪人把中原华夏文化和南方古越文化巧妙有机地融为一体,又集音乐舞蹈于一身。通过乐器声音、人物舞蹈和灯具光彩的流动变幻,以文传声,以灯抒情,表达了客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灯具制作风格也独特,以竹子或木头为框架,外表先前用剪纸贴画,后来改用丝绸彩布。灯具的照明也由油灯、蜡烛,换成了手电筒。有传统的龙灯、采茶灯,还有多人共舞的桥板灯,婚姻民俗的麒麟送子灯,祈祷丰收的荷叶灯、稻谷灯、酒杯灯、烟叶灯、蚌壳灯等30多种。最惊奇的是稻草灯,灯彩由表演队用稻草扎把而成,制作简易,也不好看,却是灯中之“龙”。主要寄托着客家人迎春接福,祈求来年五谷丰登之意。灯队相遇,都得给稻草灯让道。灯彩队到谁家门口,人们高兴地放最长最响的鞭炮。
村里的“戏迷”还组成了“泥腿子”农民业余剧团,利用晚上和农闲时节学弹唱、练吹拉,排练节目。年关前走村串户,巡回演出。彩排的古装戏有《胡公子上青龙山》《秦香莲》《寿诞记》等,自编自导的还有《客家人的好日子》《新村新貌》《老支书》《专业户的故事》等,深受群众的喜爱。自创的《莲妹绣莲赞公仆》大型彩灯戏,在市里还拿了个二等奖。
老人送我们出门时,还说:“常来哦,客家人日子过得滋润,也给外面宣传宣传,夏天来避暑哦。”和老人握别,感觉老人的手劲很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