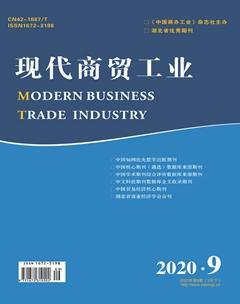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进展、挑战与建议
秦泽昊
摘 要:南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必经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历经三十余年努力,我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我国可以借助现有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抓住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契机与周边国家合作,实现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更好保护。
关键词: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9.014
南海是古代重要海上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海运繁忙,但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天气多变、科技水平有限等,不少船只葬身海底。据估计,南海有超过2000艘沉船。南海水下文化遗产(文遗)由水下文物、古港口、古航道、岛礁古代遗存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文化线路遗存等组成,不仅具有考古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各地先民在此活动的历史见证。三十多年来,我国南海水下文遗保护工作逐步推进。
1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进展
1.1 机制保护
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高,组织机构逐渐健全。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及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与澳大利亚合作培养出我国首批水下考古队员。2002年,国内首个水下考古科研培训基地在广东阳江建立。2005年,广东省文保部门举办了国内首个由地方举办的培训班。2014年6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该中心前身是2009年设立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批成立。2017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海口召开南海和水下考古工作会。9月,中心在阳江基地举办首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2018年1月,中心与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所)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成立。4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馆。11月,中心南海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海南琼海举行(信息来自国家文物局网站)。
1.2 专业保护
水下文遗发掘及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从抢救性发掘向主动性调查转变。“南海Ⅰ号”于1987年在广东川岛海域发现,2002-2004年进行了四次水下探摸和局部试掘,2007年整体打捞并保存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4年开始系统性保护发掘,2019年船货清理取得阶段性成果。“南澳I号”于2007年在广东南澳海域发现,2010-2012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华光礁I号”于1996年在西沙群岛华光礁海域发现,1998-1999年进行调查与试掘,2007-2008年开展了两次抢救性发掘。由我国自行设计的首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于2014年1月在重庆下水,2015年4-5月首次在南海进行水下文遗调查。2018年3-4月,中心与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开展年度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随后,六位水下考古人员借助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顺利完成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2019年3月,中心、深海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合作共建动态水下考古展厅签约仪式暨专题展开展仪式在南海博物馆举行(信息来自国家文物局、人民网、海南日报、中科院等网站)。
1.3 法律保护
国内立法日渐完善,执法力度不断加强。立法方面,我国《宪法》第22条、《文物保护法》第5条及《海上交通安全法》第41条都对水下文遗保护作了规定。《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条例》)作为唯一一部相关专门法规,对水下文物的概念、管辖范围、保护及管理机构、发现和上缴、考古勘探和发掘、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201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部署水下文遗保护工作。2018年7月,国家文物局召开《条例》修订草案专家论证会。2019年3月,司法部就《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文物学会召开座谈会研讨(信息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政府网、司法部等网站)。南海周边省份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则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第26、27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第15条,《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台湾地区《文化资产保存法》第46条。
执法方面,2011年及次年4-5月,国家博物馆与海南省相关部门组成执法巡查工作队,开展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遗保护状况巡查和文物执法督查。2011年8月,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我国管辖海域内文化遗产联合执法工作的通知》,决定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12月,两局联合举办我国管辖海域内文遗联合执法工作会。2012年3-4月,两局举行西沙群岛海域文遗联合巡航执法专项活动(信息来自中国政府网)。
2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挑战
2.1 基本情况了解不足,相关技术不够完善
保护的前提是发掘和研究,但我国对南海水下文遗基本情况的调查起步较晚、人员和装备较为短缺,目前对文遗资源数量、分布等情况的调查依然不足。国内相关文献如航海记录记载较少,国外档案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航行记录相对详细,但档案获取、整理难度较大。另外,我国水下文遗保护的修复技术仍需完善。虽然我国在出水陶瓷器、铁器保护修复方面已有经验,但出水陶瓷器数量巨大、破损程度各异,修复工作量及难度较大。其他出水文物的修复也面临挑战,如海洋出水木质沉船的铁硫化合物控制是世界难题,目前尚无可供借鉴的成熟方法。
2.2 水下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
破坏主要来自私人盗掘活动和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南海海域私人盗掘活动十分严重,主要参与者包括国际商业盗宝公司、私人探险队、海盗、渔民等。哈彻盗捞“泰兴号”时,为获巨额利润故意砸碎船上60多万件瓷器。“華光礁I号”自被渔民发现以来多次被盗掘,考古人员发现时人为破坏痕迹明显。西沙群岛部分海域水下文遗出现不同程度的盗掘和破坏,有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被盗掘一空。此外,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如经济建设、旅游开发等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1995年广东汕头广澳港港口疏浚中曾发现一艘明代沉船,但文保部门未及时采取措施,沉船在工程结束后销声匿迹。在渔捞作业中,很多渔船采用大型底部拖网捕鱼的方式,破坏了遗址原貌。当前海南省正大力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西沙邮轮旅游航线已经开通。南海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日益频繁,如不加管控将破坏水下文遗保护工作。
2.3 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完善,执法效果不佳
关于“水下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我国法律多采用“水下文物”,而国际公约和不少外国法律采用的“水下文化遗产”的内涵更丰富,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具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关于水下文遗的归属,我国法律关注的是文物来源,而非按照海域划分管辖,缺乏可操作性。在地方规范方面,广东、广西、海南及台湾地区都没有专门用于水下文遗保护的法规规章,相关规定仍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在执法方面,国家、地方规定都不够具体,机构改革后也面临职责重新划分,需要时间调整。同时,目前我国对南海水下文遗情况仍不够了解,很难及时定位并迅速做出有效反应,执法难度增加,执法效果也大打折扣。
2.4 南海地区局势复杂
南海是全球政治敏感度最高的水域之一,存在着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南海问题声索国众多。争端成为南海水下文遗保护的障碍。由于复杂、敏感的局势,任何单方行动都可能加重彼此间的猜忌,可能被认为是国家主张权利的行为。并且,在属于国际航道的水域外国船舶享有航行自由的权利,中国的勘查工作会受影响。南海沿岸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采取的是与公司合作的模式,允许商业打捞,这在争议海域会破坏、盗捞本属于我国的水下文遗。
3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对于我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学者多建议从法律制度入手进行保护。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修订国内法或是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需要权衡较多利弊得失,有赖长期努力。周边国家现有的合作框架或共同加入的国际公约并不主要解决水下文遗保护问题,依托这些机制的保护力度有限。而借助专门保护文遗的机制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利于南海水下文遗的保护,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恰逢其时。
海上丝绸之路东至日本,西达地中海西岸,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丝)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丝申遗源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全球文化遗产和文化线路寻访活动。2011年12月,七城签署海丝申遗《行动纲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6年5月,四城签订《海上丝绸之路保护与申遗中国城市联盟章程》,正式启动中国海丝项目的申遗工作。2017年4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会议调整申遗策略,由UNESCO世界遗产中心协调,与海丝沿线相关国家跨国联合申遗。5月,UNESCO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了首次国际专家会,海丝申遗的国际行动正式开始(信息来自人民网、海外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网站)。南海周边国家都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拥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了解遗产由此可得到的关注和保护,也深知自己在公约项下的义务及利用本国资源、进行国际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除缔约国自身保护措施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可以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22条),这有助于弥补国家自身保护措施的不足,使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保护。
无论是基于历史贡献还是现实经验,中国都有理由成为海丝申遗的主导者。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以来,中国在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申遗成功,积累了多国联合申遗及文化线路型遗产申遗的经验。未来,在考虑长远保护模式、做好持久努力准备的同时,我国应抓住海丝联合申遗契机,同周边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以加强保护,如:签订水下文遗保护合作协议或行为准则;共同举办相关研讨会、培训班,联合建立南海水下考古工作站;积极参加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培训项目,学习国际社会先进理论及实践;联合开展南海水下文遗普查工作,编制保护计划和管理规划;建立南海水下文遗数据库,共享相关信息;共建南海水下文遺保护示范区或博物馆等。
参考文献
[1]Qu Jinliang,Protecting Chinas Maritime Heritag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Policy[J].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2012,(1):47.
[2]蔺爱军,林桂兰,董卫卫,等.中国南海水下文化遗产的形成条件、探测与保护探讨[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7,(2):58-59,62.
[3]朱坚真,杨乐,徐小怡,等.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进程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4):145-148.
[4]赵亚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66-167.
[5]刘丽娜.中国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16-117.
[6]UNESCO,States Parties Ratification Status[EB/OL].https://whc.unesco.org/en/statespar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