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种死亡方式N

母亲又穿上了那条鲜红的、胸前绣着凤凰的旗袍,凤凰是用五彩棉线绣的,周围用金线钩边,整只凤凰在耀目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栩栩如生。
她散落着头发,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微微向左歪斜着头,然后一下又一下地梳理着就要垂落在地上的长发。
我喜欢母亲的头发,像黑色瀑布一样,有时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她,清脆的水声就会从那一根根发丝里流淌出来。阳光妥帖地抚过她的头顶,黑色或少数白色的银丝就会反射出耀眼的亮光,母亲不知道她的背影有多么美丽,母亲不知道她的儿子正默默地看着她,就像看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
这会儿母亲已经完全沉浸在那个只有她自己存在的世界里,那是一个无人能触及的地方。
那个地方将我、父亲还有兔子强硬地排除在外。
哐当——
大门被推开,兔子率先走了进来,它摇晃着尾巴,先是走到母亲身边蹭了两下,又来到我的脚下,它的嗓子里发出撒娇般的低吼声,用温热的舌头舔着我的手背。很快父亲也走进院子,他两手空空,先是瞟了母亲一眼,紧接着喉结在嗓子里转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说。
很显然兔子又没捉到兔子。
它看到父亲走进院子,整个身子都矮了半截。兔子离开我,夹着尾巴向墙角蹭过去,并且和父亲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兔子低垂着头,用黑如玛瑙的狗眼,向上偷偷瞟着父亲。
父亲黑着脸,低吼一声:“没用的狗东西!”
兔子就低伏着头,摇晃着尾巴跑到父亲脚下,它前腿着地,向前匍匐着往父亲的裤腿上蹭。
父亲踢了兔子一脚,兔子的腰板就直了起来。
兔子是一只越来越老的细猎犬,兔子是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它曾经一天为父亲捉住了十八只野兔,那些兔子父亲卖了将近五百块钱,那次父亲破天荒地给母亲买了一件俗气的红色毛衣。
“我早晚要把这没用的狗东西炖了。”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说,说完他还看了我一眼。
灰白的灯光下,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他曾经像树木一样笔直的腰板这会儿已经微驼,但他的眼神还是那样坚硬,像鹰一样。
我还记得十岁那年的情景。
父亲像只鹰一样,蹲坐在轻暖的阳光下,很认真但又极其不负责地给我讲了他死去时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和我很正式地谈他会如何死去,那也是他第一次说起话的时候,不再像他。
他说,他死的时候一定会死在田野上,就是那片围着小山的田野。
那会儿或许他正在忙碌,正忙着收割熟透的豆子,成熟的豆荚变得坚硬异常,像针一样扎着他厚实的手掌,可他已经连半点疼痛都感受不到了,因为他就要死了……
父亲说到这儿,我的脑海就浮现出一片半黄半绿的豆地,豆地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他说的那座小山——那个小得仿佛用手掌就能捧起来的土山包,山上长满笔直茂密的白桦树,树林向南北两侧延伸,越变越矮,直到被我踩在脚下。那时,天肯定会蓝得耀眼,父亲喜欢那样的天。
“天一定要蓝汪汪的,白云要亮闪闪的。”父亲果然这样说,“我忙着收割豆子,把小山下的这片豆子全部收割完,然后装满牛车。”
“可我们的牛车装不下那么多豆子。”我说的是实话。
“能,多少都能,因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我说能就能。”父亲的话没有丝毫逻辑,但我又不知如何反驳他,要死的人自然说什么就是什么。
“牛車装得像小山那样高,我爬上爬下地把它用绳子捆好,然后拍拍牛背说,老牛,把豆子拉回家。牛听了我的话就驮着豆子小山朝家的方向走去。”说到这里他看了我一眼,“儿子,你一定要在家门口等着老牛,哪里也不能去。”
那会儿,我才十岁,我相信父亲说的每一句话。我眼里含着泪,然后重重地点点头。
“牛车变得越来越小了,小成一团牛粪的时候,我就死了,”他怕我不相信,然后又重重说了一遍,“是真的死了,躺在收割完的豆地里,尖锐的豆秆茬子要戳进我的脊梁骨,潮湿的豆腥味盖住我的全身,野兔们爬出洞穴,看我是不是真死了,我知道它们恨我,而天上的鸟在我头上来回地飞,它们想要吃我的肉……”
“它们不是想吃你的肉,它们是想吃落在地里的豆粒。”
“我说是就是,不要和死人犟嘴。”父亲很生气。
我不敢说话了,就像父亲真的死了一样,我看到他躺在田野上一动不动,身体一动不动,手脚也一动不动,他的眼空洞得像头顶的蓝天,整片田野成了他的墓地,整个世界成了他的陪葬品,当然也包括我、母亲和兔子,真正的兔子,老牛,还有老牛车上那小山一样的豆子。
父亲比他活着的时候还要富有。
我那时候想,这可能就是父亲想要死在田野的原因。
但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还活得好好的,除了母亲、我,还有他的细猎犬——兔子。
“兔子老了,”说着我瞥了兔子一眼,它献媚般地摇晃着尾巴,“而且田野上的兔子比以前少多了。”我说着又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哐当”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大吼一声:“你知道什么,田野上的兔子不仅没少,还越来越多了,它们只是学贼了,顺着风老远就能闻到猎狗味儿……有些兔子竟然还会玩花样儿,耍得这只傻狗团团转,我早晚有一天端了它们的老窝!”
父亲说着又端起了酒杯,一仰脖把杯里的酒喝得精光。看得出来,父亲恨极了兔子,田野是他的战场,兔子们就是他的敌人。
“去,把你母亲拉进屋,让她吃饭。”父亲的脸开始泛红,像清晨慢慢铺满窗台的晨曦。
我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月光已经变成了白银,洒满院落,母亲仍旧坐在竹椅上,只是不再梳理长发。她愣愣地看着月亮,月光装满她的眼睛,艳红的旗袍上飘浮着一层薄薄的银光。于是,她整个人看上去变得不真实起来。
母亲犯病是无人能把她从那个世界里拉出来的。
从那天之后,父亲和兔子在田野里待的时间更长了,父亲说他们要捉光田野里的兔子,抢回他们失去的阵地,而母亲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她穿着旗袍坐在竹椅上,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
临上学的那个早上,我对母亲说:“我去上学了,要过两个月才回来……”
母亲没有回头,也没有应声。
新教室里宽敞明亮,这种明亮让我感到陌生而又缺少安全感,胸腔整日整夜空荡荡的,我只好不停地往里面塞大堆的英文字母、大堆的数学公式、大堆的第一次读到的文字……
秋日的天似乎总是晴朗的,教室里每个人都把腰板挺得笔直,这又让我想起了小山上那些茂密的白桦林。我想兔子说不定这会儿正在树林里奔跑,说不定小山上的兔子已经消失殆尽,那么猎犬就能保住它那条老命了……
我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的时候,她就像一阵风似的走进了教室。
她坐在我前面,看上去身材高挑而又单薄,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也想不起来她的样子,我从未仔细看过一个女生,但却记得她长及腰际的黑发。像瀑布一样的黑发,在阳光下可以发出水一样清脆响声的黑发,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胸腔就会被水声填满,那种久违的安全感就会回归。
那是和母亲一样美丽的长发啊!
父亲在一个周末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另一头呼呼地喘着粗气,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春藤啊春藤,你知道那场战争吗?”
我沉默不语。我知道父亲现在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他的身体里盛放的另一个灵魂又苏醒了,我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一喝多,就会不休不止地絮叨那场战争。我知道那不是他的战争,尽管他曾经也是个军人,但最后一场战争已经离父亲他们这代人很远了。
他说:“春藤啊,那场战争太惨烈了,四周都是炮火,到处弥漫着尸体烧焦的味道。远处、近处的森林在噼里啪啦地响,起初还有呐喊声,冲啊,杀啊,杀啊……”父亲说到这儿,声音就拔高了起来,“然后喊着喊着声音就没了,那会儿我小,像你这么大,十六七岁,那会儿我胆子小,害怕,怕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怕身边躺着的死人,怕鲜红的血……”
父亲许是说累了,他打了个嗝,停顿了一下,我想这会儿他一定躺在床上,没有脱鞋和外套,身上还带着田野的味道,眼神很明亮地望着屋顶,耳边的手机里传出他儿子细微的喘息声。
“一枚手榴弹在不远处炸开,我瞬间飞了出去,紧接着‘嘭一声撞在了树上,我还没来得及疼痛就晕了过去,”父亲又结结巴巴地说开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那是个美丽的早上,”父亲又停顿了下来,他似乎正在努力回忆着那个战火结束后的第一个清晨,然后用最恰当的词语向我表述出来,“我仿佛从梦里醒来一样,那片森林里升腾着一层雾气,我看到晨光一缕缕地落在草地上,有鸟叫,很好听的鸟叫,那密林里充满了鸟叫,我不由自主地顺着一条小路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就像在梦里一样,一切都美好得不像真的,所以那个身影突然从草丛里跳出来的时候,我完全惊呆了。他和我一样满身乌血,衣服已经看不出模样了。
“我愣在原地,他也愣在原地,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没杀过人,但是当我发现他的手向腰间摸过去的时候,我便下意识地端起枪,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那人倒了下去。鸟叫声消失了,清晨的阳光被震碎了……”
父亲说到这里就呜呜地哭起来,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终于收住了声:“春藤啊,我其实早已经死了,就死在了那场战争之中,我一次又一次死在那个人的枪下,一次又一次……”
“嘟嘟嘟”,电话另一头传来了一串冰冷的声音,父亲花光了手机里的全部余额。
我知道,这是父亲希望自己死亡的又一种方式,他似乎只有在一遍又一遍,幻想自己被敌人的枪打穿胸膛的时候才能解脱,才能成为一个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父亲是要做一个英雄的,一个捉光田野里的兔子的英雄,一个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英雄,而不久之后,父亲又向往着成为另一种英雄,并且将这一切付诸行动之中。
学校里的生活单调而又忙碌,那些之前还笔直的腰板现在已经随着冬天的来临开始慢慢垮下去,每张脸都是灰败的,似乎一张嘴就会吐出一筐又一筐的数字。
大家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他们走路快,说话快,吃饭快,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也快得让我无法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身体里仿佛装了加速器,而且加速器的齿轮越转越快,越转越快……
这种莫名的快让我常常产生幻觉,眼前的教室变了,变得无比鲜艳起来,就仿佛有人“哗”地泼上了一大盆油彩,然后无数种颜色慢慢融合,分离,又融合……直到那片空旷的田野钻进我的视线——翠绿、嫩黄、湛蓝……当所有的颜色明朗起来,我终于可以呼吸了。
再次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初冬了,田野变得荒芜焦黄,小山上的树林白茫茫一片,仿佛蒙上了一层雾气。母亲已经换下了红旗袍,她从那个世界里走了出来,但精神却更加萎靡不振。她的长发散落、蓬松着,眼睛也雾蒙蒙的,大部分时候只是靠在床角睡觉,偶尔也会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但晒着晒着就又睡着了。
有时我会忍不住喊醒她,让她回屋,于是她像个孩子一样懵懂而惊恐地环顾四周,看到我,她的眼睛会瞬间亮一下。我相信那一刻,她肯定认出了我,但大多时候,她是懵懂不自知的。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说,应该带母亲去医院看看,父亲使劲儿抽了一口指间的劣质香烟,然后忍不住咳了起来。咳着咳着,他的眉心就拧成了一团,然后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他说:“嗯,过几天我就帶她去。你不知道,这些日子太忙,我找到了兔子们聚集的老巢……”说完他把烟蒂扔在地上,兔子快速跑过来,嗅了嗅闪烁的火光,然后跳开了。
那天夜里,父亲和兔子又出去了,父亲还拖走了家里那个巨大的灰色四轮破行李箱,那是父亲当兵时用过的箱子。
父亲临出门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白天捉兔子。
父亲说:“现在田野没有庄稼,兔子白天出来会暴露自己,所以它们就改在晚上活动了,而且我有真空灯,灯一开,兔子们就往有亮光的地方跑……”
“那你拖着行李箱干吗?”
“装兔子啊,有时能装一行李箱呢。”父亲笑着,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
我疑惑地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黑漆漆的夜里。那晚,我突然觉得整间屋子,因为父亲和兔子的离开变得和田野一样空旷。
我不知道父亲晚上是不是又捉了一行李箱兔子,因为早上我起床离开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母亲仍在睡着,她的长发铺满肮脏的枕头,就像一团枯萎的干草。
从家到学校似乎只隔了一片田野,但又不仅仅是一片田野那么简单。
北风仿佛就是在那个夜晚从田野里吹过来的,风中挟裹着野兔的味道,但没人注意这些,所以在那个雪花飘起的清晨,我被簌簌的下雪声惊醒,其他人却呼呼睡得正香。
那声音可真大啊,就像猎犬兔子在长满庄稼的田野上奔跑,身体与粗糙的枝叶产生摩擦而发出的声响。这声响随着雪花的密集,也变得密集巨大起来。我不得不捂紧耳朵,直到我的同桌,那个胆小瘦弱的男孩儿,推了我一把:“春藤,你……你怎么了?”
“唰”一声,耳边的声音瞬间消失了。
从那天开始,我的耳朵就时不时冒进一些声音,水声、窃窃私语、香甜的鼾声、风吹树梢声,当然最多的就是来自教室那些藏在每个人身体里、用来加速的齿轮的声响。
北方的冬季呈现着一种坚硬的寒冷,连日不散的雾霾,似乎在等待一场从田野那边吹来的北风,各种嘈杂的声音常常充斥着我的耳膜。我需要阳光,一场雨一样密集的阳光。
终于,那个星期三的上午,天放晴了,随即铺天盖地炫目的蓝色,还有明亮耀眼的阳光一股脑儿地流淌进了教室。阳光爬上了桌面,爬上了那个女生黑如瀑布的长发,有那么一刻,我竟然恍惚觉得是她的头发点燃了阳光……
当流水般清脆的叮咚声击中耳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坠落进了那片熟悉的田野。
母亲、父亲、兔子,还有我,我们在那片没有边际的豆地里奔跑。母亲的红旗袍在绿色的田野上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她脑后的黑发便开始肆意地生长,越长越长,发梢一直飘到我的脸上……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同桌、那个胆小瘦弱的男孩儿后来告诉我的。
他说:“春藤,你真不记得了吗?你摸了那个女生的长发。你……你还吻了她的发梢……”男孩儿说到这里,脸突然“腾”一下红了,仿佛亲吻头发的那个人不是我,是他。
我没想到父亲来学校那么快,本来个把小时的路程,父亲竟然十分钟就到了。
我不知道他和老师说了什么,走出办公大楼的时候父亲突然说:“老师说让你在家反省一周,刚好你可以帮着照顾你母亲。”父亲笑得很开心,完全不问我被停课的原因。
我没应声,远远跟在他身后,于是父亲就停下来等我。他的肩膀微微耸着,旧棉衣的口袋有一边开了线,但父亲仍旧努力挺直他的腰板,用看兔子一样怜惜的目光看着我。
我不得不加快脚步。
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的旧电动车正靠在大门右侧的栏杆上,电动车的后座绑着一块木牌子,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几个大字——扫黑除恶,维护社会稳定!电动车的车把上绑着一面小红旗,红旗的颜色已经黯淡无光,看得出来,它已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风吹日晒。
“你今天在县城?”我问他,“在县城干什么?”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
他说,他正在县城执勤,做义工。电视上、网络上不是天天报道什么什么地方当街抢小孩了,什么什么地方有人冲入人群疯狂行凶了……说到这儿,父亲又一下严肃起来,说:“社会稳定要靠我们每一个公民来维持,何况……何况春藤你还在这里上学,对不对?”
我点点头,父亲之前做事是从来不征求我的意见的。
那天我执意要看父亲是如何执勤做义工的,父亲最后同意了。
他背着手站在路中间,用炯炯有神的两眼扫视着人群,仿佛他一个不留神,那些行凶的万恶分子就会跳出来。
我坐在父亲的电动车上,仰望着蓝得耀眼的天空,又看看那面暗红的小红旗,耳朵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一下就消失了。
就这样,我的幻听突然好了。
在家的日子,我认真收拾了屋子,帮母亲洗了头发,又给她换了干净的棉衣,母亲拉着我的手,她不说话,只是笑,笑得很美丽。
晚饭过后,父亲喊着兔子,拖着他的破行李箱又要出门。
“还有兔子吗?”我问了一句。
“兔子哪有捉完的时候。”父亲说着便吆喝了兔子一声,兔子摇摇尾巴,然后无精打采地跟了上去,完全没有平时出门时的兴奋劲儿。
半夜突然刮起了北风,风很大,它肆无忌惮地扫荡着院子里的一切,叮叮咚咚、噼里啪啦的响声不绝于耳。
过了很大一会儿,大门响了,然后是父亲低声训斥兔子的声音。我从床上爬起来,想看看父亲捉了多少兔子。我趴在冰凉的石灰窗台上,大风里的月光把院子照耀得雪亮。
兔子回了窝,父亲拖着四轮行李箱,走到院墙下,摸索出一只蛇皮袋,然后他打开行李箱。就着月光,我看清了箱子里的东西。
里面不是兔子,而是一箱金黄的玉米,我这才注意到院墙下不知何时已经垒满了装着玉米的蛇皮袋子,而之前那里只有一堵高高的院墙。
原来,父亲晚上不是去捉兔子,而是去偷玉米。
我没想到我會提前被学校叫回去上课。那天早上临走的时候,父亲突然说,他很快就攒够给母亲看病的钱了。
“钱都是你卖兔子的钱?”我突然问他。
父亲显然一愣,但很快他又直了直身子说:“那当然,要不然你以为我和兔子天天夜里出去干什么?”
我动了动嘴唇,看着正认真吃饭的母亲,却什么也不想说了。
父亲执意要骑电动车送我去学校,我没有反驳,反正他是要去县城里执勤做义工的。
我坐在电动车的后座上。
今天风小多了,但依旧很冷,我把手和脖子都缩进衣服里,然后把身体弓起来,身后是那块绑得结实的木牌,很硬。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先跟谁说的话了,反正最后说着说着,父亲就又开始用那种梦游般的语气说起了死亡,我只好住嘴,认真听他说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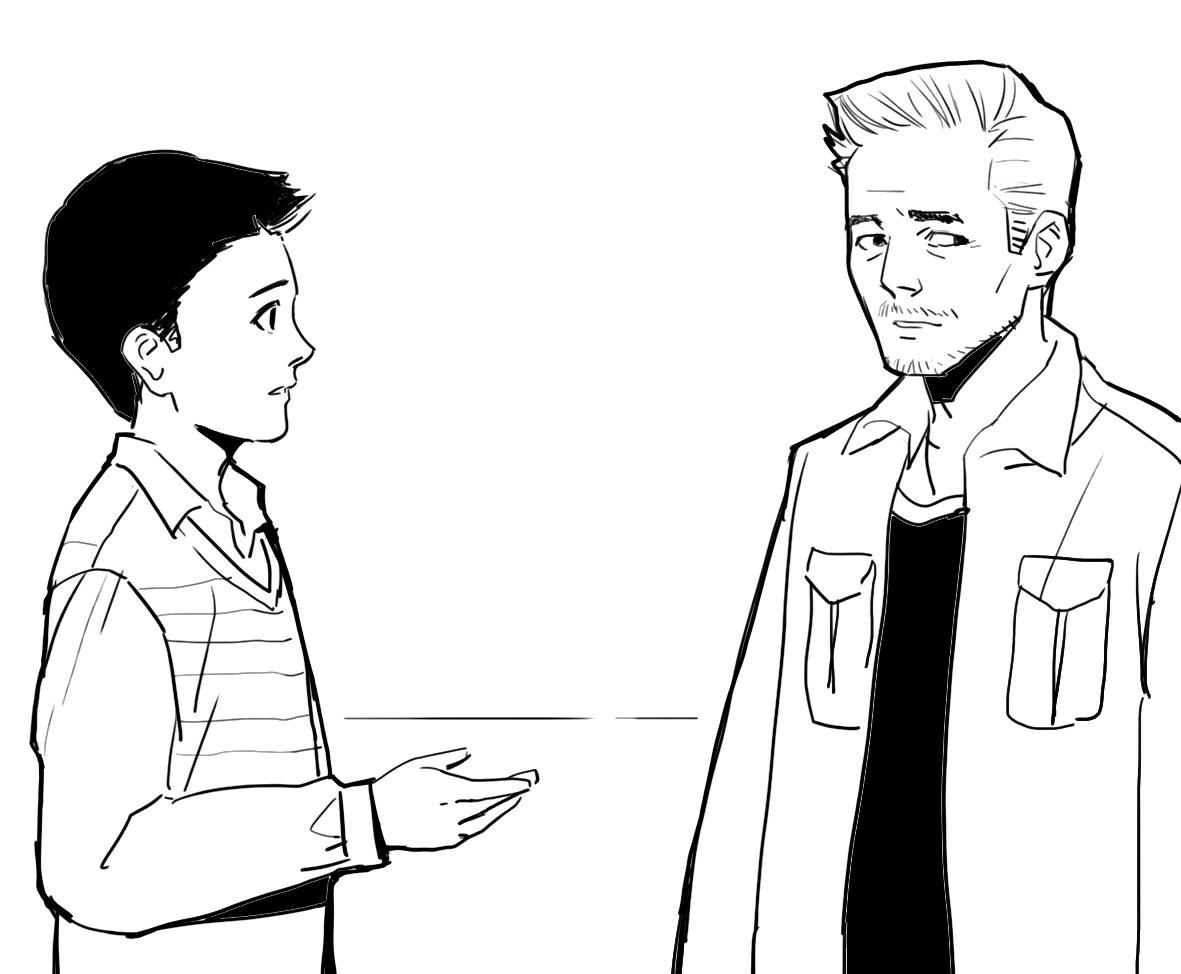
他说:“春藤啊,我想换一种死法了,一种真正死得其所的死法。我不想死在田野上,也不想默默地死在战场上。”父亲说到这儿,我想打断他,我想告诉他,他还活着,他没有死,从来都没有死过,但冷气却钻进了嘴里,我觉得牙齿就被冻住了。
父亲继续说,丝毫不顾及灌进嘴里的冷气,“我一直在寻找那样的机会,寻找一个舍己救人的机会,一个可以成为英雄的机会,这样你就会拥有一个英雄的父亲……”
冬日的清晨在父親的絮叨中慢慢亮起来,田野在我的视野里呈现着它最真实的本色,一望无际,无遮无拦……
我从父亲的后车座上跳下来,在心里翻腾了一路的那句话突然就冲了出来:“我不需要你当什么英雄,因为我将来会当一个英雄……”
我明显看到父亲一怔,然后眼里瞬间溢满愤怒:“放屁,你当什么英雄,好好当你的儿子,滚蛋,好好念书去……”说完他愤愤地离开了。父亲高高的身影瑟缩在冬日里,显得单薄而苍老。
回到学校的那天,我突然发现教室里有什么不一样了,仿佛少了什么,但又说不上来。我疑惑地看着所有人,熟悉而又陌生。
“春藤,你没发现?”同桌那个矮小瘦弱的男孩儿一脸神秘的笑容。
“头发。”说着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我仍旧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这时,恰巧一个短发女生推门走进了教室,她看上去身材高挑而单薄,大眼睛,眼角下有一颗黑痣,是一个陌生的女生。我以为她走错了教室,她却微笑着径直向我们走过来,然后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前面。
她说:“春藤,欢迎你的回归。”说完她对着我大方地眨眨眼。
那天我知道了,所有女生按学校的新规定剪了短发。
冬日仿佛就在那个女生的笑容中迅速溜走了。
在校园的树木开始泛出绿意的一个黄昏,我给她讲了母亲的故事。我告诉她我的母亲曾经也是这所中学的学生,她美丽而且成绩优异,高考后的第一天,她穿着红色旗袍参加了班里的毕业晚会,但那一天,却成了她人生当中最美的一天,因为她高考落榜了……
女孩儿没说话,什么也没说,只是仰着头看着头顶泛着绿意的树梢和春日的天空,她的短发在夕阳的余晖中闪闪发亮,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满蓬勃的春光。
那年女孩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那年家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父亲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查出肝癌晚期,但他却拒绝住院。回家后的父亲仍旧像个战士一样和他的猎犬兔子奔跑在冬日的田野上。
第二年,立春日,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他最不希望的死亡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个清晨,糊涂多日的母亲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她说:“清河,清河呢?怎么不做饭?儿子回来了。”
清河是我的父亲。
清河是我的英雄父亲。
选自《读友》(清雅版)2019年第12期
赵卯卯,本名赵静,80后青年作家,两个孩子的妈妈。自2012年起至今,创作多部备受孩子喜爱的童话、小说。出版有长篇幻想小说《我和银扣的奇幻之旅》《我们都来种星星》,中短篇幻想小说集《6点30分躲进屋子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