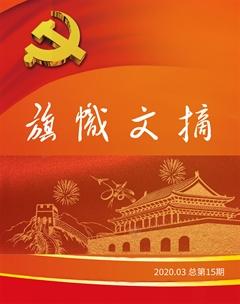档案母亲
赵钧海
一
父亲的档案袋里存放着一张母亲的登记表,填写有母亲的履历,这大约就算母亲的档案了。
六十多年前,母亲以随军家属身份,在新疆广袤的荒野、戈壁、碱滩、沟壑劳作生活了二十六年,之后又跟随转业的父亲回到了她的老家——华北平原。母亲的新疆经历从此就随风远逝了。宛若一片红里透黄的秋叶,母亲在碧空中旋转、翻飞、飘移,硕大苍黄的落日,徐徐下滑着,红光四射,给她镶上了一层金边,叶片的筋脉纹路通透清晰,炫亮中熠熠闪烁。
二
父亲已经去世十年,我时常有一个梦想,企图拿到父亲的档案,以便更精准地抚摸父亲的另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来自官方,来自另一个第三者的正面立场。费尽周折,我终于允准过目父亲的档案,但不能拿走。老干部档案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觊觎就如同有不良企图的窃贼。小心翼翼跟随档案保管员哈哧哈哧从一楼翻找到四楼,竟然没找到有父亲编号的档案袋。蹊跷?但不气馁,我坚信:父亲在。他肯定隐匿在那些曾经浴血奋战走过枪林弹雨的革命者中间;他肯定抬着头挺着胸迈着军人坚定的步履,哼着谐趣的小调;他肯定微笑着,慈眉善目的样子,混迹在一群白发老者的行列里……脚步,硝烟,钢盔,旗帜,信仰,鹅黄的军装,铜锈的奖章——父亲是我的榜样,我的神,我的瑰丽记忆啊!不甘心,拽着档案保管员我重又从四楼一个铁柜一个铁柜找回一楼,最终,还是在一楼密集的档案盒中翻找出了父亲的档案袋。
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父亲依然活着。档案资料太新了,以至于我无法辨别和判断,那些字迹果真是七十年前填写的吗?简直就像昨天刚刚写完一样,全新,鲜活,灵动,墨迹清晰,没有想象中的斑驳与黄旧,没有浮土,更没有蜘蛛网肆虐袭扰的痕迹。
这时,我发现了母亲。
厚薄不一的各色纸张中间,夹杂有一份母亲的个人登记表。我惊讶了,心跳加剧。一段深深掩埋的历史被打捞。这份表格是当年由父亲代笔填写的,母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农村女孩,战事,缭乱,生灵涂炭——母亲成为了文盲,不识字,她不可能填写。当然父亲同样也是文盲出身,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他刻苦学习,土地、沙丘、雪野都曾是他的稿纸,随便捡拾一根木棍,就成了他的如椽大笔。我曾见过父亲一个纸张粗糙的旧黄本,记有许多难辨的繁体字,字写得奇大,且歪歪扭扭,后来父亲又被送到解放军第一炮兵学校深造,知识储备来了个大跨越。他的文化知识全部来自军队。
盯着登记表,忽儿一股伤感涌上心头——母亲原来是一个没有档案的人。过去自己似乎从未在意过此事,也从未思考过此事,愧疚啊!无颜面对。可以肯定,母亲的大部分个人资料,也就是附录在父亲档案中的这些了。心潮翻涌,一股生命卑微又悲壮的氤氲之气弥漫过来,凛冽、喑哑、幽冥……好在,我亲眼目睹了它。
三
1957年早春,母亲从华北平原滹沱河边一个小村庄出发,一路向西,踏着田野蜃气去寻找她的未婚夫——我父亲。那年母亲二十岁,还是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如今依然住在老家村里的小舅多次在喝酒时告诉我,你妈那时是咱村的一枝花,大家公认漂亮、好看、利索、能干,还当着妇女队长哩!媒人们都踏破俺家门槛了,抢着给俺姐介绍对象。小舅好喝酒,我每次去村里看望他,他都会用新鲜五花肉、大白菜、豆腐炖一锅好菜,用老家的自酿烧酒招待我,醉意微醺。喝着、品着、说着,一说就说到了从前的一枝花,说到了母亲的妍丽、纯美、秀雅和光鲜。仿佛母亲跟了我父亲是下嫁,是扶贫。我至今存有母亲年轻时一张全身坐姿正面照片,面容白皙,表情淡定,长发到肩,双手抱膝,穿一件花格子外衣,露着醒目的白色小翻领,竟然也是当年最流行的列宁装的装束,只是款式更超前更时髦,双脚还穿有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背景幕布竟然是春意盎然的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大家闺秀风韵啊!完全可以视为面如凝脂,曲眉丰颊,珠圆玉润,容貌清丽。但是当年,母亲看完媒人拿来的父亲提亲照片后,动心了,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咬着嘴唇,羞涩地轻轻点了头。父亲一身戎装,头戴大盖帽,肩章是一杠三星,扎着宽腰带,勇武、英俊、潇洒,母亲没法不动心。母亲偷偷瞄了一眼,就向媒人轻轻点了头。于是,放下锄头,放下妇女队长的架子,母亲夹着一个花包袱上了西去的列车。父亲那时已经是新疆最西边一个边防团炮兵连长。边关,孤烟,冷月;邈远,苍茫,夐古。母亲长途跋涉四千多公里,走了十多天,才走到了一个叫尾亚的地方。母亲抿着嘴唇,固执地挤火车,蹲车厢旮旯角,睡座椅下面……她的花包袱在灰蓝和土黄的人群中,穿梭、游动,一路绽放,如一朵风雅香艳的牡丹花,极为耀眼。纷乱中,时常会有温热呵护的手,拉一把穿补丁衣服的母亲,但也会有贪婪的目光盯着母亲身上扫射,蓄写着歹意与淫念。母亲惧怕了,额头一阵阵冒冷汗,愈走愈胆战心惊,愈走愈没有底气,灵机一动,趁解手时用泥土在脸上涂抹,然后用灰头巾把头裹得严严实实。母亲化装成了一位土气又邋遢的中年妇女。
在尾亚,火车走不动了,铁路没了。黑压压的人头攒动着,拥挤着,她随大流跟着人群往西,往人多的地方走,那里有几间黄泥土屋说是临时接待站,专门收容支边的热血青年。那时满天都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口号,有志青年和无业盲流都向往边疆。母亲挤上一辆开往伊宁的大卡车。车厢里异味浓烈,酸汗味、烟草味、狐臭味交错,刺鼻、呛人、呼吸困难,她屏住呼吸,企图挤掉那些怪味。快吸,憋气,轻吐,再快吸,再憋气,再轻吐。重复一遍又一遍,可还是气力不够,努力都是徒劳,她终于憋不住了,不由自主嗷嗷喊出了声音。母亲害怕极了,就不再憋气,放弃了。吸吧吸吧,能死人吗?随着卡车的颠簸,母亲双腿麻木,不听使唤,脚尖鼓胀坚硬,疼痛难忍,但看着蛮荒的四野,满目的死寂,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以及飞旋呼啸的北风,一切都被淹没了,覆盖了。母亲忘却了那怪味和疼痛,终于睡着了。又辗转颠簸许多天,母亲才走到新疆最西边的边陲小镇——惠远。母亲说,一路上可把罪受够了,灰沙戈壁,灰沙戈壁,永远是灰沙戈壁!浩渺冷寂让她的心冰凉到了极点,她悄悄地流眼淚,一次又一次。她知道,只要去了,这辈子就不可能再回头了。觳觫、恐惧、后悔。母亲想,我为什么只看了一眼那个男人的照片,人都没有见,就鬼使神差被迷惑了呢?这是母亲后来常常对我复述的一句话。
母亲笑着对我说,你说你妈妈傻不傻?照片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第一眼看到你爸,不敢相信,傻眼了,你爸那个黑呀,就像锅底一样。我大哭一场,蒙着被子哭,哭了好几个小时。你爸见我不开心,就结结巴巴说:如果……如果不愿意,可、可、可以送你回家。你想想,那么远的路,怎么回呀?反悔都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更说不出回家的理由。母亲抽泣着,不断用手帕擦泪,一块绣着百合花的手帕都擦湿透了,可以拧出水。母亲调侃。哭了很久,母亲的举止让那些当小兵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头接耳好几天。后来就不哭了,咬牙扛住,不说话,脸上也始终没有笑容。母亲说,那几天你爸那个殷勤,那个体贴,忙上忙下,忙里忙外,什么沙木沙、薄皮包子、油馕、手抓饭,什么无籽葡萄、西瓜、甜瓜、无花果、青皮核桃,乱七八糟,花花绿绿,香气袭人,满嘴更是甜言蜜语,连你爸的战友们,也个个开心傻乐,嫂子长嫂子短的。——俺被俘虏了,像灌了迷魂汤,晕晕乎乎,只有转向,只有跟随,只有铁心,不能也不敢再动摇了。母亲侃侃而谈,像在叙述别人的经历,袒露出的是内心的温润和欢愉。
母亲成了一名随军家属,她踏实站在了洪荒与苍凉之上,站在了孤寂与混沌之上,质朴又凤仪,沉实而稳固,也接受了人生一次摧枯拉朽的洗礼。接着,她就一口气生下我们兄弟三人。死心了,笃实了,不再奢望与梦想。母亲成了地道的新疆人。
四
母亲的这份登记表,就是《党员登记表》。这张表显然只能独立存在,因为它代表了母亲本人的意愿和崇高又绚烂的精神追求与指向。虽然它蜗居在父亲的档案袋中,但它代表了母亲的独立人格。不过,父亲档案袋里还有母亲的另外两张表,填写也较为详细,但都附录在父亲的登记表格内,只是占了不小的篇幅。一张是父亲的《干部家属随军审批报告表》,另一张是《部队干部转业申请表》,在爱人一栏里,母亲是庞大的,坚实的,具体的。这三张表的跨度很大,纵横三十多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延续到父亲转业回老家的八十年代。母亲也從一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变成了风韵不再的中老年妇女,漠风、酷暑、沙暴、冰雪洗劫了她的肤色与容颜,也历练了她硬朗、傲骨、豪爽奔逸的内心。
母亲在新疆二十六年中,一直如一件附属品,只有一个称谓——随军家属。母亲异常辛苦,最终她以瘦弱的身躯、忙碌的移动、泼辣的呐喊和踏实能干,赢得了声誉,获得了掌声,也凸显了过人的膂力、机敏的融合力和铁腕般的领导力。母亲被推选为家属队长,她每天都带领一帮家属大妈、阿姨们开垦荒野,挖渠,翻地,打耙,锄草,担粪,施肥,浇水,捡苗,打药,种菜,还耕种了大片玉米地和麦田。母亲的肤色于是就被荒野的风和刺目的阳光捉弄得黑里透红。就像当年父亲的黑一样。有一年放暑假,我从外地上学回家,发现母亲竟如一个非洲黑人,额头还闪着贼亮的光。那时,我知道非洲有三个刚果,一个是刚果(布),一个是刚果(金),还有一个是刚果(利)。孩子们总会说,刚果黑。我以为母亲就是刚果黑。很奇怪,母亲天天戴一顶草帽,却还是没有遮挡住荒野紫外线的强烈辐射,以至于我一时懵了,没敢辨认。母亲婉丽姣好的形象逃遁了,消失了,无影无踪。那一刻,我鄙视母亲,我以为,别的同学母亲都白白净净,只有自己母亲黑瘦又丑陋。许多年后,我脑际还会忽然闪现当年自己那一刻的猥琐和阴暗。我悔恨不已。虽然当年自己只是在脑际闪了一下,并没有说出不满,但它毕竟是闪现过,闪念过。那时候有一句话很流行,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我知道这闪念的意味,也知道这闪念里隐藏着猥琐与阴暗,也让我知道了我的无耻和卑劣。
风风火火当家属队长实属不易。母亲早出晚归,满身污泥,面容变得黧黑,嗓音变得沙哑,一把铁锹随时扛在肩上,双手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母亲的手曾经是那种白皙细腻的纤纤玉指,然而,漠风与劳作使它变得粗粝而枯槁。尤其是嗓音,每天出工收工,母亲都要用尖利沙哑的嗓子仰天高喊,长年累月,犹如凄厉的高音喇叭。纳闷,那时母亲还有一个铃铛和哨子,但她却偏偏要高声呼喊:“劳——动——走——唻!”“劳——动——走——唻!”母亲高声呼喊着,一遍又一遍,声音传得很远很远,盖过了野草地、梭梭林、芦苇荡和大片大片的醉马芨芨滩,以至于我的同学刘双全在许多年之后,还记得我母亲呼喊的腔调,他模仿着,惟妙惟肖,形神酷似,铭心刻骨。
母亲的辛劳最终换来了尊敬和权威,也换来了黄灿灿的麦子,颗粒饱满的玉米,还有豆角、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以及萝卜、土豆、大白菜和莲花白,每每在泛着白碱的打麦场分菜时,家属院的所有大妈阿姨和孩子们都出动了,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欢声笑语,喧嚣,尖叫,奔跑,流窜,如过年一般热闹。微风飘来,麦香菜香四溢,沙土原野荒草气味弥散,温馨,迷醉,缱绻,沁人肺腑。
母亲就是那年入的党。表格上填写有母亲入党时间:1967年1月。于是,当年的镜像缓缓显影出来。母亲不识字,没上过学,是个文盲。我清楚记得,母亲是请灵芝阿姨帮她写的入党申请书。黑魆魆的冬夜,异常寒冷,漫天飞雪中,灵芝阿姨来到我家,她脸型稍宽,肤色润白。灵芝阿姨的小棉衣是一朵一朵的粉色小花,我从未见过那么漂亮的小棉衣。母亲与灵芝阿姨趴在桌子边上谈了好久,熄灯号已经吹过,发电机不再嚎叫,房间一片漆黑。母亲点亮煤油灯。那是一盏我家用过许多年的煤油灯。玻璃灯罩被擦得锃亮,灯捻子被拧得最大。我在被窝里,好奇地偷窥。母亲与灵芝阿姨的一举一动,被灯光映射在粗糙的灰墙上,黑影巨大。母亲说一句,灵芝阿姨写一句。她们嘴里咿咿呀呀不停地发出“奋斗”“理想”“到底”“共产主义”的誓言,还一遍又一遍小声重复。煤油灯的光晕散射在她们脸上,柔和,昏黄,静谧。母亲洋溢在无限的憧憬之中,目光深邃又洁净。少年的我仿佛从那个瞬间起,知道了母亲的追求,知道了母亲的执拗,也知道了母亲的高远与波光潋滟。没有功利,没有蝇营狗苟,没有鸡零狗碎,只有超拔,只有澄明,只有内心深处洋溢的暖意和若隐若现香风熏暖的气息。那是一个年轻母亲的追求和嬗变,一个随军家属的提升和觉醒,一个朴素妇女的夙愿和终极目标。我听着,隐隐约约分辨着,虽然懵懵懂懂,但心尖温暖浑身燥热。母亲说的是真心话,朴实的话,暖心的话,绝非大话、套话和虚伪的胡言乱语。母亲激情四溅,宛如进入了新境界。那一夜,母亲和灵芝阿姨写得很晚很晚。我终于支撑不住,迷迷糊糊睡着了。
那几年,父亲去天山北坡一个叫精河的农牧业县“三支两军”,父亲的真实身份是精河县革委会主任。父亲在那里忙忙碌碌,整整三年未回家。母亲就带着我、大弟、小弟兄弟三个,吃喝拉撒睡,锅碗瓢勺,砍柴,挑水,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一把抓。同时,母亲又是领头羊,带领一大群家属大妈、阿姨们,开荒种地,砍伐红柳、梭梭,铲割大片的芨芨草、骆驼刺、苦豆子以及碱蓬草、灌木亚菊,她们像英勇的战士一般,吃苦耐劳,忠贞不渝,汗洒疆场。我以为,她们就是我身边的王杰、刘英俊、雷锋、向秀丽、欧阳海以及门合,她们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母亲当然是最高大的那一位,她无畏无惧,无所不能,浑身上下都闪烁着穿透四野的朗灿之光,箭射着叱咤风云的磅礴之气。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低能智商。
五
回河北了。一切跌入冰谷。最早父亲母亲没有住房,就租住在一个孤寡农民的破烂小院里。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阴暗,逼仄,杂草丛生,还有一股酸腐的霉味。父亲、母亲与小弟拥挤在一张加了块木板的床上,如三只搁浅的困兽,开始了另一场拉锯战式的艰难战役。记得我结婚带妻子第一次探亲,一进那个小院,蒙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心底透凉透凉。那小院四周的土墙破烂不堪,一口旧缸装着半缸浑浊的饮用水,墙角有一低矮的茅草屋,臭气熏天,那是厕所,里面挖有一个坑,支着两块几近腐朽的木板……我妻子始终没敢下蹲一次,她宁肯走很远的路去找其实也并不干净的公厕。虽然她从小也是上旱厕出身,可她无法忍受这污浊与奇臭。
我愤愤不平,脸气得涨红,面部表情扭曲而怪异。我狼嚎一般说,怎么能这样?怎么会是这样的下场?一个为祖国解放、保卫边疆出生入死又驻守边关几十年的老军人,一个随丈夫在荒野戈壁辛苦劳作几十年的随军家属,并且还把两个儿子留在了新疆,不算劳苦功高,也该有应有的照顾和尊重吧,怎么转业回家乡了居然连像样的住房都没有解決!——我愤怒,我膨胀,我要上告!我要上访!这难道是一个曾经的解放军团长的待遇吗?!但,我的歇斯底里让父亲母亲诚惶诚恐,都赶紧制止我。父亲内疚又慌乱地说:只是暂时的暂时的,说了,说了,要给分房子,正在规划设计,正在选地方设法解决哩。母亲也捂着我的嘴说,不说,不说,家里的老乡都是这样过的,人家祖祖辈辈都一样,人家能过,咱也能过。
我压住气听从了父母,只好作罢。我只是短暂结婚探亲,我还要回新疆,我必须听从父母,不能把事情闹大,不能再给他们添乱。
是的,母亲没有了单位,母亲回河北后的工作始终在希望与失望中踯躅徘徊,没着没落。母亲也如一只无头苍蝇四处碰壁。母亲只好把党组织关系暂落在父亲单位了。母亲说,我是一个党员,不能脱离组织。从那时起,母亲就开始主动往父亲所在单位交党费,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冬去春来,一交就是几十年。母亲深知组织的重要,也深深眷恋着组织,仰望着组织。但是,母亲却没有找到工作。也就是说,母亲其实是一个没有工资收入的人,但母亲却一直在默默地交着党费。
母亲的工作是长久聚集在父亲心头的阴霾。父亲无能为力。父亲转业回河北没两年就退居二线了,几年后彻底离休。我以为,父亲或许是不适应,或许是不熟悉地方工作。他可能天生就是一个军人,就适合戎马生涯,就适合舞枪弄炮,就适合在荒野边关驻守。父亲身材魁梧,健壮,善于打仗,不怕牺牲,具有军人的崇高品质。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参加了解放军。他说,那时部队的番号叫西北野战军新编第四旅,俗称新四旅,后来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部队一直从华北向西挺进,一路打仗,一路拼杀,太行山、秦岭、崆峒山、祁连山、火焰山、西天山、婆罗克努山,他的战友越打越少,他却奇迹般越打越勇,火线入党,火线提干,最后跟随彭德怀司令员王震司令员在罗元发军长的带领下,长途奔波到祖国最西边的伊犁惠远。从此留守边关,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剿匪平叛、带兵训练、修挖工事、开荒种地、“支左”“爱民”,父亲成长为一位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团长。我始终认为父亲骨子里就是扛枪打仗带兵的军人,只具备军人相貌,军人潜质,军人风骨。他的思维、认知、技能全部来自部队,来自军营,他也许真的不适应地方工作,应付不了地方那些复杂的机制、结构,那些抓心挠人的官场和人事关系,那些千奇百怪的社会毒瘤。父亲皱着眉头吐着烟雾说: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也许这种不适应让父亲惊惧,惶惑,不知所措,也让他懵懵懂懂,晕头转向。父亲苦恼着,眉宇凝成了道道绳索,两眼变得一抹黑。
找来找去,上上下下都是疙瘩,都是荆棘,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接收母亲。学历和年龄的门槛高不可攀,规定和条款的制约铁板一块,它们如一堵高墙,最终将母亲挡在了墙外。母亲是文盲啊,抗日战争时期出身的农村女孩怎么可能上学读书啊?!其实,那年回河北老家时母亲也才只有四十五六岁,想想,多么年轻啊。母亲虽然口持乡音,但家乡却无法接纳,无人问津。人事主管部门官员态度生硬且冰冷地说:年龄太大了、太大了,不好安排,要等机会!
什么是机会?父亲母亲不懂。
母亲的工作问题,停泊了,搁浅了,终止了。
我抽出父亲的《部队干部转业申请表》,盯着表内母亲一栏看了许久。我发现,有一行话是专门询问填表者的:是否随同调动及对工作的安排。父亲规规矩矩在这一栏下帮母亲填写道:随同调动,安排适当工作。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它其实也是母亲的最真实的想法和夙愿。但是,没有人在意,没有人关注,也没有人发恻隐之心。想法只是想法,夙愿只是夙愿,只是一厢情愿,永远没法得到另一方的认可和关怀,也就永久没法实现。——就像天空一角绚丽彩虹,永远悬挂在深邃阔大的天空,赤橙黄绿青蓝紫,却无法接近,无法触摸,无法企及。丽日朗耀,云蒸霞蔚,清旷悠远,惠风和畅。这些明丽与美好都与母亲无缘。母亲伤心地哭了,一次又一次,喑泣着说:可不,我不能吃闲饭啊!
母亲就一直在吃闲饭。一晃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又过去了,她始终未能找到工作。母亲一脸严肃,再也没有了悲伤和愤懑。
我知道,母亲的痛在心灵深处。
六
许多年之后,我忽然发现一个现象,机关干部兴起到新疆挂职的热潮。一个科级干部,到新疆后,必定要高配副县(处)级或县级,一两年锻炼、锤炼、磨炼之后,必定要回到内地,回内地后必定要重用和提拔。原因就是,他们去过边远艰苦地区了,他们去过洪荒恐怖的新疆流汗了、吃苦了、镀金了。而回望我们的父辈,他(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中最具活力的二三四十年奉献捐助给了新疆大地,奉献给了西部荒野、沙漠戈壁以及保卫建设边疆的事业,两鬓斑白时,又转业转回内地,不是降职使用就是找不到合适工作,何苦啊!——淡淡的忧伤和隐痛长时间袭扰纠缠着我的心,撕扯着我的五脏六腑。那画面仿佛就是风霜雪雨袭击后消损的干枝枯叶,干瘪,萧索,漫漶,满目疮痍。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父亲母亲勤勤恳恳惯了,任劳任怨惯了,他们小心翼翼,他们隐忍宽厚,他们心地善良,他们永远不愿意给别人制造麻烦,甘愿自我蹂躏。或许他们只需要一点点认可,只需要一点点公正和温暖。
眼里含著泪水,内心流着血。我的汩汩作响的血脉,一半来自华北平原,另一半来自新疆荒野。我的父亲母亲回到了华北平原,我和我大弟留在了新疆。新疆其实就是我的第一故乡。我在新疆出生,长大,学习,生活,工作,并且娶妻生子,我还将继续留在新疆直至化为灰烬。我忽然卑微地悟出一个观点,我的父母其实真不该再回去,不该再返回他们依旧眷恋的故土。那些故土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摆设和象征。当然,他们也真的无法决定他们自己命运。或许,他们不那么认为,他们内心深处依旧感念着生养过他们的华北平原和滹沱河水。虽然那个平原早已不再是从前的平原,大地之上时时笼罩着溷浊的雾霾,曾经清澈的滹沱河水早已干涸。但他们乡愁不灭,乡愁清冽,乡愁简净。乡愁就是掺杂了多彩绚烂的华丽向往,就是掺杂了个人少许私情的终极幻觉。
母亲居然想通了,神态又恢复了从前的欢悦。母亲后来对父亲说,算啦,算啦,找来找去太费时,太费事,太伤脑筋,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母亲于是给自己想出一个无法自给自足的工作——卖冰棍。母亲从此就背着我和大弟偷偷卖了许多年冰棍。小弟与她同回的河北,小弟目睹了母亲的所作所为,曾经为此大吵大闹过,说是都没脸见人,没脸见同学同事和老家的亲戚了。但母亲很固执,如一头倔牛。开始,我对此事毫不知情。一年回家探亲,看望父母,在汽车站刚下长途客车,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晃动着,纷乱中觉得面熟,像母亲,犹豫不敢确认,因为那黑瘦的老太太背着一个白色木箱在中巴车上叫卖……定睛细看,正是母亲。——我与母亲撞了个正着。我眨巴着双眼,头一阵嗡嗡嘤嘤,眸子不再转动,怔住了。
傻眼,崩溃,战栗,坍塌……不敢相信。我的头鸣叫着,身体晃晃悠悠,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也感到无地自容。
向母亲发火了,用最污浊的语言,最丑陋的表情。我尖利刺耳又喋喋不休地啸叫呐喊,如一只凶狠的恶狼。
母亲一遍一遍自我检讨,始终赔不是,歉疚地说:我应该告诉你们的,都是我的错。母亲无奈地强颜苦笑,眼泪却汪汪的:这是你妈妈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不能没事干啊!母亲的强颜苦笑,其实是内心在哭,在抽泣。我看到的是肃杀、寥落、渺小。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母亲突然变得又瘦又小,身躯羸弱,骨架枯干,原本就不丰腴的脸庞更是皱纹密布,爬满了沧桑和疲惫。我再也不敢直视她,满眼阴翳。仰天长啸,我是一只凄凄戚戚的小老鼠!
母亲向我表示,以后再也不干了。
母亲表现出了无限的殷勤,甚至有些奴卑。她迈着勤快的双腿,买肉,买鸡,买兔子,几乎把我小时候爱吃的饭菜统统做了个遍,花样繁杂,味道鲜美。我恍惚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少年时的新疆。仔细想想,当年哪里吃过这么多好吃的,总是苞谷面窝窝头、发糕、搅团以及钢丝面,偶尔有一点肉,也被母亲做成炒熟的哨子,放在一个小盆里,慢慢吃。那时,没有冰箱,肉没法保鲜,炒熟的哨子是最好的存储方法。家家户户都那样。看着母亲在厨房游动,我吃着喷香的饭食,满嘴流油,不住打嗝,就再也不忍发火了,也不再恶犬般横眉指责和训斥。
闭嘴了,沉默了。母亲不易,母亲艰难啊!
但结果是,我前脚离开河北老家回新疆,母亲后脚就又背起她的小木箱出门了,风雨无阻,谁也拦不住。朦朦胧胧中,我看见母亲瘦骨嶙峋,躬着腰,驼着背,挎着木箱,去很远处批发一些冰棍、雪糕,然后,沿街、沿中巴车站拥挤的人群叫卖:“冰——糕!”“冰——糕!”声音沙哑、凄凉……我心痛无比。
七
《干部家属随军审批报告表》虽然是父亲的主表,但实际上是母亲的随军申请表,时间是1957年6月,填写有主管部门的签字:同意随军。落款处有父亲上上一级党组织的印章。我推算,那个时间就是母亲一路坎坷奔波到新疆的最初时间,也是她看到黑不溜秋的父亲后,大哭一场,又不得不点头下嫁的时间。而父亲的《部队干部转业申请表》时间是1982年,附属在父亲简历栏下的母亲在这张表中的唯一要求是:请组织安排一个工作。
父亲档案袋里母亲所涉及的三张履历表,就像一条正弦曲线,画出了母亲几乎一生的行为轨迹。这条曲线细若游丝又沉重如铅,积淀了时间,砥砺了生命,点划了人生冷暖。我终于隐隐约约觉得,母亲从风姿绰约,飒爽英姿,到风烛残年,垂暮老妪,犹如在喧哗之后、繁缛之余逆光中闪烁的一缕清逸,一抹曼美,一隅绮丽,一泓隽永。
继续在父亲的档案袋里搜寻,企图找到母亲更多的蛛丝马迹,但我很徒劳。琢磨了好一会儿,我忽然又觉得母亲已经八十四岁了,已经走到人生暮年,她其实有没有档案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母亲是一个普通人,遇到了普通人的遭遇,又过往了一个极不普通的人生履历。她的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档案,它淡定地匍匐在那里,煌煌荧荧,白光闪闪,容颜浴净,意旨微茫。
八
从档案馆出来,大院里一树一树桃花杏花怒放着,花团锦簇,香气袭人,微风拂过,摇曳生姿,一派和润绮丽的景色。母亲又拽着我往回返,说是去父亲的生前单位一趟,我纳闷说:有什么事吗?母亲说,大事哩!走吧,咱去交党费,我每次去,门卫都要审问老半天,如审问从前的美苏特务和地富反坏右一样,要身份证、要户口本、要单位人出来认领,还要填写表格,我人老眼花,又不识字,现在写个名字手抖得厉害,字也歪歪扭扭,门卫还斜眼看我,像轰鸡狗一样轰我走……再就是,你爸爸单位的老人都退休了,年轻人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你爸是谁,好麻烦的,正好,你在,给他们解释起来方便。
盯着母亲,我静默了好一会儿,感觉精瘦羸弱的母亲似乎又恢复了先前的丰腴和干练,又恢复了当年在荒野戈壁烧荒、担粪、浇水、呼喊的样子,爽利,执拗,风风火火,酣畅淋漓。眼圈模糊了,不再多问,也无法多问。我与母亲一起向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威严大门走去。
责任编辑 王 童
(本文选自:北京文学 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