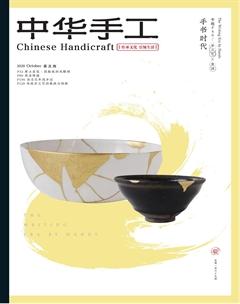故纸堆里的修书人
刘海军



一般说来,虽然宋代古籍更久远,但宋代古籍比明清古籍保存得更好,因为宋代多用皮纸,拉力强,耐折磨;明清多用竹纸,质地较脆,易坏;而民国时期的书则脆薄,保存同样不易。
一群“半路出家”的修书人
“什么味道?真好闻!”刚出电梯,一股淡淡的中药味扑鼻而来。
“是芸香草,我们早已闻不出这种味道了。”“80后”修书人崔月婷虽然健谈,但此刻一脸淡定,与想象中古板的修书匠不太一样。“芸香草可以防虫,如果在馆里闻到谁身上有这种味道,那一定是我们特藏文献中心(包含传习所)的。”
在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地铁环线终点站重庆图书馆出口,一眼就能瞥见被玻璃幕墙包裹的重庆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重庆传习所就设在5楼。
目前传习所有8位修复师,4位“80后”,其他都是“60后”或“70后”。虽然年纪最大的快到了退休年龄,但他们多是半路出家,仅有1988年出生的徐言勃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纸质类文物修复专业,也是所里年龄最小的。
走进修复室操作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各种古籍、纸张、修复工具以及一些现代仪器,填满了整个房间的墙上、桌上、搁架上或角落里。一眼望去,最显眼的要数一张超大的红色大漆装裱台。几位修复师完全被书页包围,各自安静地坐在修复桌前,听到有人来,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继续干着手上的活儿:溜口、包角、找平等,很安静,很忙碌,也很有节奏。
被崔月婷带着在工作室转了一圈,准备拿起相机做一下记录,她有些“慌了”:“你不会发出去吧,要是被赵老师看见,肯定会批评我们,太乱了!”她口中的“赵老师”可是大有来头:本名赵嘉福,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古籍修复师,至今已经在古籍修复行当里浸淫了整整60年。2010年,重庆古籍修复传习所(当时称作“古籍修复中心”)从上海邀请赵嘉福前来担任导师,赵老欣然应允,这一教就是10年。“赵老师真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不仅技术绝、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毫无保留地教。”崔月婷的言语中透露着她对赵老由衷的敬重。“我们也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以前师傅是怕徒弟学会,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则反过来,就怕学生学不会。”对此,赵嘉福也谈过自己的看法:“我受过传统的教育,我的付出是应该的,为什么?我要有一颗报恩的心,我手上的技术都是老一辈工匠传给我的,他们又得到了什么?他们也毫无保留,我们也是赶上了改革开放才有了今天,我回报社会是应该的。”正是怀着这种传承使命之心,如今77岁高龄的赵老,身经两次手术,仍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重庆古籍传习所、辽宁图书馆等地传道授业。
“2007年,国家成立了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也是从这时才在全国全面铺陈开来。重庆因为陪都那段特殊的历史,藏有不少珍贵的古籍——据说藏量达到53万册,因此一直备受重视,保存得也较好,所以古籍修复也算全国进行得较早、较好的。”谈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崔月婷掩饰不住内心作为重庆修书人的骄傲。
“按行规,修书一般3年出师,我马上就到3年,但我感觉离出师还早着呢!”其实崔月婷自2007年开始就已经接触到这门技艺,只不过作为一名真正的修复师是在2017年。她揶揄自己道:“刚开始以为自己是块璞玉,结果发现也是块石头。”她转身一指:“喏,我们许彤老师都干了10多年了,还在学呢!”“60后”的许彤是重庆第一批半路出家学习古籍修复的人,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刚开始实施,全国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招生,许彤就主动报名申请,争取到重庆唯一一个名额,就此与古籍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她仍担任着赵嘉福老师的助理。
“我们一天经常要洗8次手,摸一次书就得洗一次,皮都磨薄了。”对于修书人而言这压根不算什么,更令人担忧的是粉尘、霉菌等容易引发鼻炎、咽炎等职业病。最近传习所赶着修复一批线装书和民国文献,即便呛得咳嗽不止,还得硬撑着。
“给我们年轻人‘祸祸的古籍都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看起来有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虽然这是一句夸张的玩笑话,但一个“祸”字能看出崔月婷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对修书这门老行当发自内心的敬重。
认真对待每部古书的“老汪头”
一本古书的修复,不仅需要修书人具备高超的修复技术,还要集古籍版本知识、古籍保护知识、文史知识、艺术审美等于一身。“在别人看来,把纸粘补上去就成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为了让笔者有更直观的认识,崔月婷特意演示了“补窟窿”环节,“这里面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干补、湿补、托补、衬纸等,而配什么纸、力度多大则需要更多经验了。像这种虫蛀的情況算比较轻微的损伤,只需稍作修补就好了。修旧如旧嘛!”
“修书一般分准备、修整、复原3个阶段,20多道工序,一招一式极为考究,起手落笔皆有道理。”崔月婷讲了不少修复的要点。这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汪学军所言类似:“古籍修复最基本的步骤大概有24步,但多则可达40多步,根据书籍损害程度不一而论。”40多道工序中主要包含配纸、染色、制浆糊、溜口、补破、折页、裁齐、打磨、打书眼、订线等。
裁齐也称裁边,是“大刀汪”最得意的一门手上功夫。汪学军是“大刀汪”第三代传人,汪家三代人手上都有着一身令人叫绝的裁边手艺。一把超过3.5kg的纯铁大刀,拿起刀,一刀下去,干净利落,而且是几本一起切,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因为活儿干得漂亮,大家都到汪家去裁书。于是江湖上渐渐有了“大刀汪”这么个名号。
“裁边的时候要注意手的力度,用力太大会破坏书页,用力太小又容易裁得不齐,还要注意用刀的角度,刀口要稍稍往外偏一点,然后直切下去,裁出的书才会齐整。”提起裁边手艺,汪学军的言语中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种自信。尽管现在“大刀汪”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对于一些珍贵的古籍,汪学军还是坚持手工裁切。“机械化裁刀不能切古书,因为古书的纸张已经焦脆了,纸张可能会被机器砸裂,毕竟机械化裁刀的冲击力度是无法跟手刀的触感、柔韧度比较的。”
据汪学军讲,古籍修复用得最多的有镶、溜、补、托、衬5种技法。其中“镶”在一段时间颇受修书人欢迎。“提到修补装帧哪能越过它呢?镶是一种装帧方法,又叫惜古衬或穿袍装。”镶指金镶玉,这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因为经历岁月洗礼的书页泛黄,而在新镶的白纸衬托下,黄白相间,如金似玉,因而得此雅称。金镶玉的前半段跟其他技法一样——制定修书计划、制浆糊、溜口、去水印、下捻、裁边等,然后拆除纸捻,开始制作金镶玉——选纸、裁纸、打眼、折边、折页、锤平、包角、打眼、订线、裁粘书签、制作书套等。“要特别注意一个地方,包角用的浆糊一般比较稠,如果在潮湿多雨的南方,由于包的角不透风,容易生虫或逗老鼠咬。这是包角的一大缺陷。”
“做金镶玉一定要溜口。”溜口的作用是为了加固书口,便于进行金镶玉装订,如果不溜口,书口就容易开裂。“有些人,甚至一些书里介绍,把修补裂开书口的步骤叫做溜口,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溜口,溜口,就是滑溜的意思。先把该补的都补了,溜口的时候动作就麻利,抹浆糊的速度和动作也就很快了,就像滑冰一样顺溜,这才叫溜口嘛!”
因为金镶玉能做到修旧如新,所以曾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那时候人们的审美都是以新为准,觉得新的体面好看,为了迎合这种审美,大家也就喜欢什么都用新的。但后来随着人们审美和对古籍价值认识的提高,才将“修旧如旧”作为修复古籍的基本原则。就因为这,汪学军还曾跟朋友闹掰过。有一次朋友拿来一套清代五色套印古籍,破损得不是很厉害,只要稍作修补即可,可朋友一定要求做成金镶玉。“我觉得这套书做金镶玉不太合适,本来书的尺寸就比较大,每页再要衬上一张纸,周边再多出一些空白,就把书变得又大又厚,也许看起来够气派,但对于古籍本身的保存来说未必是好事。可不能让这套书毁在我的手上!”
但这并不表示汪学军不认可“金镶玉”,相反,他对金镶玉有独特的认识:“古籍修复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伪。虽然很多人会提到修旧如旧,但在我看来,修旧如新和修旧如旧是辩证统一的,要从古籍的状态出发,加上修书人的认知进行修复,而非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古籍修复的意义是保护,所以保护才是真,要更加完好的保护。如何才能做到完好保护呢?例如“金镶玉”可以把书页都完好地保护起来,不仅能显示旧,也能显示新;而按照修旧如旧的做法,修一回‘蹭一回,越打磨越少,到最后可能东西都‘整没了。所以,修书要根据破损情况,从实际出发,从出发点看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古籍修复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之上进行,究竟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这是两条路子,而非修旧如旧就把古籍修复的未来发展之路给封死了。”
修复少数民族古籍的“面糊匠”
古籍修复作为书画装裱的一个分支,在很多方面都跟书画装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派别划分上二者就大体一致,分为沪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等,但传承到现在,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而现在更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南派和北派”。其实在技法上,南北两派并没明显差异,而造成这种分化主要是因为南北气候差异大,从而对古籍造成不同损伤:例如北方干燥,书页会霜化;而南方雨水较多、气候湿润,纸质易酸化、生蛀虫、受潮生霉等。现在,尤其是国家提倡古籍修复以来,南北两方的传承人、导师与学生互通往来、相互融合,更是模糊了两派的分界线,将南北的较量转变为跟时间的赛跑。
虽然鼎盛时期我国曾出现过多个派别,但他们主要修复的都是汉文古籍,却不见提及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令人遗憾的是,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这让文字记录本就不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受到很大挑战。直到2017年,杨利群首次修复完成“纳格洞拉洞藏经”藏文古籍,才让这一局面有所改观。
2010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古籍考察组从一名采药人口中打听到,香格里拉县一处隐蔽的洞穴内藏有一些藏文经书,经抢救发掘出藏文经书12种、2 009叶,包含了《丹珠尔》大藏经、民间僧人法事记录等,可为深入研究云南藏文化奠定基础。后来这批古籍以发掘地命名为“纳格洞拉洞藏经”。“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类似藏文古籍修复的先例,都认为‘条件不成熟,应该再缓缓。但这批经书的情况非常糟糕,急需抢救性修复。”杨利群现在回忆起第一眼看到这批经书的场景,仍感到十分痛惜。他主动请缨,以“按照原貌、不做装帧、整旧如旧,最小干预,修复材料可去除、过程可逆”原则进行尝试性修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让这批藏文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而杨利群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对傣文、彝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进行探索,成为国内少有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师。最近,他又开始研究贝叶经的修复,并且已经初步完成了贝叶的染色和修复,只等整理好材料就可以开始尝试性修复了。
“我十二三岁时就在家里从装裱字画开始学起,长大后顺利进入云南省图书馆当了一名‘面糊匠。”在圈子里,古籍修復师还有一个俗称——面糊匠,因修书时常常需要用浆糊将破损的地方修补、粘贴起来,而且为了追求效果,修书人大多都是自己亲自调制浆糊,一方面避免在市场上买到伪劣产品,另一方面自己调制的浆糊使用起来心中有数,因为不同的纸张、环节使用的浆糊浓稠度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打浆糊是一个修书人的基本功。”类似的话,汪学军也说过:“单就打浆糊,这里边学问大着呢!这个不是说打成稀浆糊就成了。那时候,老师傅走过我跟前只是说‘再兑点水,人家为什么让我再兑水?这就得靠自己琢磨,你得自己看看是怎么回事,这糨子是用来粘纸的,稀了该怎么办?粘不住又该怎么办?怎样才合适?这些都得靠自己弄清楚。如果浆糊调制得不好,以后会对纸张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里边儿就需要心里时刻装着‘讲究,而不是‘将就。”
“藏文跟汉文古籍修复最大的不同在于纸张和装订方式。”一提起古籍修复,杨利群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藏文古籍采用梵夹装,而修复用的是狼毒草纸浆修复,东巴经则是荛树皮,傣文、彝文也是用的各地特色的构皮纸……”配纸是杨利群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少数民族古籍修复难度最大的当属藏文古籍,传统用于抄写经文的藏纸多加入天然植物原料,韧性强、防虫蛀,可这一传统造纸技艺如今几乎是找不到了。”后来杨利群终于在安徽找到了颜色接近的构皮纸作为基本用纸,再将狼毒草根部捣碎,取其汁液加入补书所用的纸浆中,终于将这种合适的配纸研制出来。
而修补纳格洞拉洞藏经时,杨利群还独创了人工纸浆补法——将混合纸浆均匀地浇在纸张的缺损处,不断用镊子调整纸浆的厚度、平整度,再经按压、晾晒完成。后来,杨利群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12期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上担任了11个班的授课导师。
“科技可以用,但要慎用”
杨利群刚开始并未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职业,也未刻意去学,古籍修复顺其自然地就传到了他的手上,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操持了这门传统技艺。“应该是受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吧,从小就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敬业专注的工匠精神。”杨利群出自古籍修复世家,父亲曾是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鉴定修复专家,母亲退休前一直从事古籍修复。正是这种家族传承,让杨利群从小对古籍修复耳濡目染,心底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修书情结,所以一干就是近50年。
近50年来,杨利群看到旧人离去新人来,看到古籍修复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也看到一些传统修复方式被高科技取代,例如老化机看纸张的变化、显微镜分析纸张结构、白度仪测定纸张白色程度等。通过高科技仪器,确实比人工要来得更准、更便捷,如纸张脱酸机可以为纸张脱酸,以便更好地保护古籍,纸浆补书机能协助人工又快又好地修复古籍。
“不过不管科技如何先进,手工修复的许多细节仍是无法取代的。”在杨利群看来,有当代科技辅助可以让修复变得更简单容易,但有些需要坚持传统的地方还得坚持,比如藏文古籍的纸浆制作,就需要经过传统手艺水煮和敲打出来的纸浆才能用,这是现代搅拌机无法做到的。
对此,汪学军也谈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们汪家的大刀也改成现在灵活自如的小刀了,能用得着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也是好事,以前磨刀、裁边都是体力活,还伤腰,是真的很累啊!”看着搁在展示架上的大刀,汪学军有时候也会感慨一下。“比如喷水壶就比以前的好用,传统的喷水壶都是靠嘴吹的,有根长长的吸管,一吹,把水壶里的水吹成雾状,噗噗噗,一会儿就把人给吹晕啦!那一页一页吹过去,嘴巴麻了,把人的脑袋都给吹大了。现在手轻轻按压幾下,就会喷出均匀的小水珠,省心省力还高效。”
“科技当然可以用,但还得慎用科技。”汪学军说了句跟杨利群类似的话。他讲了一次亲身经历:有一次,一个推销员拿着使用传统方式制造的太史纸(又称粉连纸、连史纸)给他看,结果压根儿不是,他们是把黄色的竹纸加工染白了,就成了他们所谓的“太史连纸”了。“所以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能太依靠科技,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古籍修复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专业,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行会、保护神的行业,只有自己挺直腰杆子保佑自己。”汪学军接着又感慨道:“不过现在好了,国家和各地文化部门重视,不仅职业教育开设了专业,连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都开设了这个专业。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何愁古籍保护不好,何愁文化不兴呢!”
古籍修复技艺
古籍修复技艺又称古籍装订修补技术,在我国拥有上千年的传承史,是一门在书画装裱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技艺。它可以让破损的古籍化腐朽为神奇,是保护古籍完整流传至关重要的一环,因此,这项技艺也被誉为古旧图书的“续命汤”。2008年,这项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掌握这门传统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仅有中国书店肄雅堂的汪学军和国家图书馆的杜伟生两位,但近些年在各级部门努力下,传承保护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