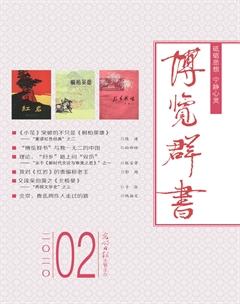巴金、钱锺书、李广田与“中年写作”
吕彦霖
“中年写作”一词最早见于诗人萧开愚1989年发表在《大河》上的一篇名为《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的短文中:
诗人应当摆脱孩子气的青春抒情,让诗歌写作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在正常的文学传统中,这应当是一个文学常识,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
有研究者从萧开愚的题目中的三个关键性词语——“抑制”“减速”“开阔”,解释他的这番言说背后的理念:“‘减速意味着从‘快向‘慢过渡。不仅仅是一种节奏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心态的变化。”“‘抑制意味着放弃此前过激情感或过激思想,将分寸感带进诗歌”。“‘开阔则既指视野,也是指胸襟与美学的区域。”由此可见,萧开愚所说的“中年写作”并不是具象化的对“中年”这个年龄阶段的指认,而是指一种有别于“青春激情”的创作状态。
另有研究者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将这种“演变”放置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将“中年写作”与阿多诺、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加以融汇,结合20世纪文学发展的现实,创造出一个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晚郁时期”,并将其美学特征归纳如下:
1、“晚郁时期”是回到本土的写作。
2、“晚郁时期”的写作是一种更加沉静的写作,看不到激烈的形式变革,但却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内化经验。
3、“晚郁时期”也有如赛义德所说的“晚期写作”,有一种自由放纵的态度。不再寻求规范,其创作有一种自由的秉性、任性的特征。
4、“晚郁时期”有深刻内敛的主体态度,对人生与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超出了既往的思想,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交的哲思。
5、“晚郁时期”真正有汉语言的炉火纯青。
本文中的“中年写作”视域可以视为“中年写作”与“晚郁时期”美学特征的综合。笔者认为,《寒夜》《引力》与《围城》三部小说分别从不同的向度展现出“中年写作”的特征,预示着作者成熟创作心态的形成。
谈到创作状态的转变和“中年写作”特征的显现,巴金当属于三位作家中最明显的一个。巴金的前期作品具有相当明显的“青春书写”倾向,他喜欢以鲜明炽热的笔调,讲述具有英雄气质的理想人物是如何投入激烈的社会斗争之中的故事。同时,他的创作往往为情绪所驱动,对人物和事件有严格的分类,赋予他们泾渭分明的性格。因此,他早期的作品虽然能够引起轰动,却难以带给人长久的回味,有论者批评他“一直将文学当作发泄愁苦,宣扬理念的工具,缺乏创作的虔诚,锤炼的耐心”。
然而自1942年的《还魂草》开始,巴金展现出一种新的写作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在《寒夜》中达到成熟。作家似乎放弃了原有的激情书写与主观判断,代之以一种理性内敛的冷静态度;不再执着于书写反映大时代的英雄事迹,转而将目光投注于普通小人物之上;文本的内在秩序也由简单直白变为复杂缠绕,同时展示出一种“大巧不工”的艺术风格。“史诗式”的书写习惯,也转变为“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的关切。显然,这种写作姿态包含了对“整体”的消解和“当下”的注视,“沉静的写作姿态”和“深刻内敛的主体态度”。放下了对“功利性”偏执的作家,开始使用自己擅长的方式,重铸自己的艺术个性与美学风格。
值得注意的还有《寒夜》对曾树生和“家”的评价。在作品中,曾树生感到生活的无望和青春的消耗,她希望离开家庭寻找自我的价值,但是她如果此时离开也意味着抛下重病的丈夫和上学的儿子,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自私行为。作者写出了她的心灵搏斗,当她下定决心“救出自己”的时候,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她看到自己手中的书——曹禺的《原野》。作者用这样的一个“互文”暗示了她的选择——和花金子选择仇虎一样,她最终也抛弃了家庭,独自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作者对她的评价也和曹禺对花金子的评价一样,并未完全以道德化的眼光进行批判。在面对读者对书中人物的质询时,巴金更是直接阐明了人物塑造期间所持有的开放性态度:
也有读者来信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再看对“家”的评价,对“家庭”的批判始于五四时期,“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开端, 对‘家的批判和否定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巴金的早期作品中,尤其是“激流三部曲”中家庭更是以“黑暗的象征物,专制的具体化”的形态出现。而在1942年以后的创作中,巴金对家庭的批判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写到家庭的温暖和它在动荡时代对个体的保护。他对人物和家庭评价的转变,不仅来源于“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同样也与他社会身份的转变和抗战的特殊情境密切相关。正如论者所指出的:
1944年,巴金结了婚,那年他40岁。从后来小说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渐从抽象浪漫课题,转到具体的婚姻问题上去,这归功于成家对于他人生观的改变。
由“离家”到“掌家”,身份的转换带来了更多的“理解之同情”。抗战的流亡经历和苦难体验也使得知识分子希望“寻找软弱、孤独的个体赖以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样的“时代情境”使得他们重新审视“家庭”的价值与意义。

再看钱锺书,笔者以为钱锺书的《围城》之“中年写作”特征主要表现为:“深刻内敛的主体态度,对人生与世界有深刻的认识”和“真正有汉语言的炉火纯青”。《围城》中,作者以普通人物方鸿渐的所思所为为切口,上升到对人类所面临的普遍性存在困境的体认,如此集中地展现对个体存在思索的长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属首次。这种对存在的深入思索,无疑与作者困守“孤岛”时期的私人体验密切相关。同时钱锺书以惊人的才华和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识,在《围城》中充分显示了调和了中国传统的古雅文字与西方影响的“现代”语言之后,文本可能抵达的高度,这种来源于“综合”的“炉火纯青”是过度欧化的“五四”语言与古奥的古典文言所难以企及的。在对《围城》的阅读中,我们除了能看到作者一贯的机智与犀利,还能感受到一种在其旧作中不易察觉的“哀矜”。作者以往对人物的讽刺和揭露,往往拨开其“文明”的面具,写出其背后的“丑态”,从而带给人以“笑声”。但在《围城》中,作者虽然嘲笑了方鸿渐的懦弱与荒唐,却对他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面对生活的种种“力不从心”感到同情。这种创作情绪的“复杂化”,这种背后有“泪水”的“笑声”,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感”,也可视为作者成熟的标志。
最后这种“中年写作”的特征在李广田的《引力》里主要体现为:对“限量的事物和时间”的关注与“不再寻求规范,自由放纵的创作态度”。“限量的事物和时间”强调写作中个人经验和情感的灌注,而“不再寻求规范,自由放纵的创作态度”则强调一种遵循个性,挑战规范的创作手法。李广田的《引力》是作者的一剂用来自我抚慰的“精神良药”,创作小说时,他的妻女仍滞留沦陷区,流亡路途之险恶,机关空气之压抑,使得他急切寻找新的精神慰藉。远方的妻女自然成为最重要的寄情对象。因此他将她们写入作品,甚至在相当数量的故事情节中照搬妻子的来信,也就不难理解了。也正因为这是一部“留给自己的作品”,因此小说不重情节,而是对情绪与心理的变化情有独钟。《引力》虽然算是长篇小说,但实际上如同一段段散文的“拼接”,作者在叙述中尽力调动各种文体服务于情感的表达,模糊了本来的体裁界限。有论者就指出:“李广田只是依自己的材料和感兴信笔写下去,不大顾及小说的章法。”这种渗入大量个人化因素的自由化表达,赋予了《引力》一种真实与诗意相互交融的品质,自由的表述又修正了“过分人为的艺术结构”,艺术地表现出最高的真实,这与“汉园”时期的“京派”趣味有很大的不同。另外,這种反映个人经验的自由表达也与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知识分子渐趋生成的“岗位”意识有关,在“岗位”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启蒙责任相对减少,文学更多地成为他们个人的“志业”,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个人化色彩。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成熟的创作状态当然也与逐渐打破“中西、古今、新旧之争的困局”,呈现出“文化综合”趋势,逐渐趋于理性和包容的时代文化语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