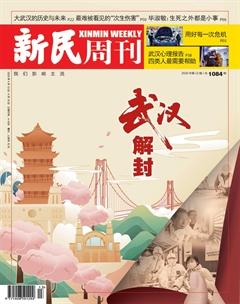城与事
分餐制
陆小鹿(上海,白领)

近来,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数据。
出乎意料,印度的情况竟比想象中要好,不知何故。喝了恒河水,百毒不侵?当然,这是调侃了。
有人嘲笑,印度人现在吃饭还在用手抓,那是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抓饭团去蘸调料。不过,印度人不会直接用手去桌上抓取食物,而是用勺子从桌上取好食物,放在自己盘子里,再用手抓着吃。
我非专家,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分餐制的确比合食制更为卫生。最起码,它减少了人与人通过唾沫传染的机会。
之前去餐馆里聚餐,比较讲究的餐馆,会每桌配备一至两双公筷。再讲究一点,会每个食客各配备两双筷子,一双用来夹菜,一双用来吃饭。
但部分小馆子,尤其是面馆之类的快餐店,就很不讲究,通常是将一把筷子一齐插在筷筒里,也不知有没有做过消毒处理。
我有一阵患了洁癖,午餐去写字楼附近的餐馆,总是自带餐具,一双筷子,一把勺子。吃饭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但有时又觉得与身边人显得格格不入,别人都很自如地拿起店家提供的筷子,仿佛就我一个人懂卫生似的。后来,从众心理让我放弃了自带餐具。
但在家里,我还是可以定规矩。我家是合食制,不过,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筷子和勺子,我们从来不会混用餐具。喝汤时,用汤勺盛到自己的小碗里,不会大家都拿筷子像吃火锅那般在汤里洗筷子。
此次疫病来袭,使得用餐习惯又被摆到桌面上来讨论。无论如何,我想,餐馆不论大小,今后都应做好餐具消毒工作,若是团体聚餐,请给每人配备两双筷子。在家里,我们也可以学印度人实行分餐制,每人一只大盘子,把各自想吃的菜夹到自己盘子里,做到一起用餐但分食进餐。好习惯,有利于身心健康。
唱响《欢乐颂》
尹画(上海,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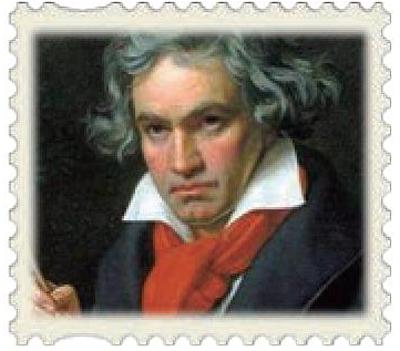
刷新聞,看到“小提琴女神”安妮-索菲·穆特确诊了新冠肺炎。很吃惊,也很难过。
犹记四年前,穆特来华演出,我买了高价票去看。那时,她多精神啊!穿着一袭鹅黄色的抹胸鱼尾裙,像美人鱼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去年年末,穆特又来到中国,在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带来四场贝多芬作品音乐会。当时,北京电视台对她做了专访。在视频里,穆特特别提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一章《欢乐颂》。她说贝多芬就是用《欢乐颂》向全人类发出一个信息:大家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在一起,这不单能让生活更美好,或许,也是人类能够存续的唯一道路。
得知穆特确诊了新冠肺炎后,我又单曲循环了数遍《欢乐颂》。熟悉的旋律在耳畔铿锵回旋,充满力量感。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穆特早日康复。
今年恰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原本,各地安排了很多纪念活动,但受疫情影响,演出不得不按下暂停键。不过,演出暂停,音乐却没有停止。3月20日,荷兰鹿特丹爱乐乐团上线了一则视频。18位居家隔离的乐手拿起乐器,以卧室为背景,分别录制了各自声部的演奏视频,最终剪辑成贝多芬《欢乐颂》的片段。恢弘磅礴的气势,在视频最后30秒达到高潮,听得我浑身振奋,言语无法表达心情。
这场战役,已跨越国界,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唯有团结起来,一起努力,才能迎来胜利。
贝多芬的《欢乐颂》,实际上是为席勒同名诗歌谱的曲。诗言:“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在你光辉照耀下面/四海之内皆成兄弟……”自我记事以来,从未遭遇这样严重的疫情。而最近看到中国派出医疗专家组支援意大利、塞尔维亚、英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动。患难之中见深情。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非常时期,音乐也可以是战斗武器。在这个特殊的“贝多芬年”,希望一首《欢乐颂》,能让全世界人民更加紧密团结,望全球疫情早日得到控制。
孔兄买单记
安谅

“咦,孔兄人呢?”众人寻思着。明人猜想:“应该是买单去了,哎,这孔兄!”
孔兄与他们有20多年的交情了。大家坐在一块,总要聊到最初认识时的一件往事。那年镇江的舅妈寿辰,高速刚通不久,有驾证的明人借了一辆小车,自己驱车过去。车上坐着妻儿,儿子才一岁多。耿平正好有假期,得知明人的计划,也乐意相陪。他又叫上了孔兄,另开了一辆小车,在前头飞驶。
明人不常开车,车开得挺慢。耿平他们就在路旁弯道上,等了他一阵。孔兄说,还是我来开吧,你歇一会儿。明人同意,于是,孔兄稳稳地驾着车,踩实了油门。车行了十多分钟,突然异样地抖动起来。“车轮胎坏了!”孔兄让系好安全带,随后聚精会神、缓缓降速,最后安全停在路边。下了车一看,前右胎瘪瘪的。孔兄抹了一把汗:“好险!”耿平说,幸好是孔兄接过了方向盘,如果是生手明人开的话,一见轮胎爆了,多半就踩刹车了,那就糟了,车子倾覆都有可能。
这事令明人对孔兄有了好感。孔兄的名字叫孔繁茂,听着很熟悉、亲切。国字脸,剃了个光头,黑瞳闪亮,唇边带着一缕戏谑,高大的身材,有种英锐之气。听说他在做生意,具体明人也没有打听。而和孔兄再相逢,是因为有一次身为大学教授的耿平,说要请几位在官场的老同学聚聚,且再三说明,不为受托办事。饭局末尾,明人发现,孔兄悄悄先出去了一会,不用说,是把买单任务扛走了。
后来,耿平聚聊,总是把孔兄叫上。次数多了,明人不禁想,难道是在为孔兄设局?否则孔兄何必一次次买单呢。现在已清楚了,孔兄做工程材料买卖,据说生意尚可。可耿平没提过,孔兄与明人熟稔了,也没有过任何暗示。倒是另一位老同学过意不去,给孔兄推荐了一个项目。耿平马上说,不妨让另一位亟需项目的朋友做,孔兄也就当场让了。
好几年前,明人到北京出差,一位朋友推荐他去一个有点名气的“流水宴”看看。在某小区的高层内,一位脸上写满沧桑的六旬男子,这家的主人,热情地迎接了他们。长条桌旁,坐了好多互不相识的客人,主人以微笑和酒菜相待。上的菜并非山珍海味,都是主人的湖北家乡土特产,用小盘子盛着,明人频频举箸,回味无穷。回味更加深刻的,则是这个流水宴客来客往,主人以交友为乐,似乎毫无企图。后来听说,主人还是大有收获的,座中高朋不少,做了一些生意。
这孔兄不会是流水宴主人的再版吧。
这回,孔兄果然又是去买单了。他返还落座后,明人悄声说,你老这样,我们过意不去。我们没法为你做生意助一臂之力,要严格遵守制度规章的。孔兄忙回:“明兄千万别这么想,我绝不麻烦你们什么的,友情比生意重要,也长久。何况,你们都是有才学的,和你们在一起,我可以学习不少东西呢。”这一说,明人对他更刮目相看了。“孔兄孔兄,绝非你想象的孔方兄。人家有底气!”耿平在一旁高声说道。
明人把目光转向孔兄,孔兄的双眸依然晶亮,和脑袋上的光亮,相映成趣。明人想,上海滩上,孔兄是可以深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