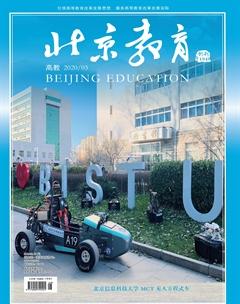“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与大学三种“智慧型”人才的培养
杨杏芳 赵显通
摘 要: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实现从培养“知识人”向培养“智慧人”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一个真正有战略眼光、有格局的大课题。如何面对并解决好这个大课题,需要高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体现为立足于“新大成智慧学”的哲学基础,开出“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以此作为大学教育新的指导思想;而在“实践创新”方面,则体现为以“约翰·怀特方案”“怀特海方案”和“钱学森方案”为模本,参考近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教育经历和发展轨迹,探讨如何培养这三种类型的“智慧人”,使得高等教育从当下的“机械论的、静力学的与还原论的”狭隘的“小教育”中跳出来,走向未来真正的“辩证论的、动力学的与系统论的”拥有无限创造力的“大教育”!
关键词:动力学的大教育;知识人;智慧人
从“约翰·怀特命题”出发引发的对大学教育的思考—大学教育是围绕“知识人”的培养为中心而高效运转的巨型机器
1.“约翰·怀特命题”及其相关观念
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教育哲学大家约翰·怀特教授又推出了一部新的力作,可以看作是他的名著《再论教育目的》一书的姊妹篇,[1]翻译为《学校教育幸福论》(Exploring Well-being in Schools)。[2]在这本书中,怀特教授重点探讨了“Well-being”(译作“良好生存”或“幸福”)这个人类最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念,进而反思了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
他对学校教育想表达的一个最深重的忧虑是,“正如事情所显现的那样,学校教育把获得考试的成功作为中心任务,……竞争每年都在加剧,标杆也在逐级提升,……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从局部看,围绕著考试的指挥棒打转的学校教育的确能将各个方面的工作凝结起来高效运转,但若从整体来看则缺乏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制度下,学校教育被严重扭曲,完全迷失了自我,不知道自身究竟为何而存在。”[3]
笔者把这段话称之为“约翰·怀特命题”,这个命题是他对中小学教育总体情况所作的批判性概括,但他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定下分析大学教育问题的基调。
2.大学教育是围绕着“知识人”的养成实现高效运转的巨型机器
从“约翰·怀特命题”出发引发我们反思大学教育是围绕着什么中心来运转的。一言以蔽之,大学教育是围绕着“知识人”的养成实现高效运转的巨型机器。
第一,大学专业教育的目标定位助长模式化倾向。大学在于培养掌握各学科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的“学霸型”人才,学分、考试、文凭和成绩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知名学者张楚廷教授曾强烈批判质疑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化”的提法和做法。那我们要追问,究竟是什么提供给大学的人才可以“模式化”培养的土壤?是大学教育对“知识”的追求与重视。
第二,大学通识教育的作用与功能被异化。从本意看,大学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启迪智慧,具有人文、历史以及哲学的格局与眼光,帮助学生学会去做一种“智慧人”,懂得在面对多元的世界与复杂的事物相互冲突时如何做出最为恰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但是现在的大学通识教育却异化为“知识和学分”,也不能对学生自身的生存选择与走出迷茫起到任何作用。爱因斯坦说过,“大学教育如果只重视掌握知识、学好专业,那学生毕业离开大学时,他只像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有智慧的人”。[4]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现今大学教育实践整个遵循的都是培养“知识人”的逻辑,它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众多热点问题,如大学生的厌学问题、就业难问题、创业教育问题等产生的总根源、总症结。
3.实现从培养“知识人”向培养“智慧人”的根本性转变是中国大学教育深具战略眼光的大课题
鲁洁教授(2004年)在《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一文中批判了“知识人”的教育目标对人的幸福生活的践踏,“为了知识,人们忘却了自己,忘却了生活,甚至牺牲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知识得到之时,也就是人自身、人的生活被异化之时,这是教育的悲哀!”[5]
著名过程哲学家怀特海(2002年)认为应以培养比“知识人”更高级的“智慧人”为目标。他指出,“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传授各种科目。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6]
面对“知识人”的教育目标定位的重大缺陷,国内很多学者都呼吁,必须要进行教育理念的革新以塑造“智慧人”,[7]认为“转识成智”是当代教育的一种价值走向。[8]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实现从培养“知识人”向培养“智慧人”的根本性转变,是一个真正有格局的大课题。
理论创新—“新大成智慧学”的哲学基础与“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
如果我们聚焦在如下三个最为关键性的哲学维度或分析框架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当代大学教育那些热点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三个最为关键性的哲学维度:一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突出的是 “反映论”或“符合论”的关系,还是真正的“功能论”的、“实践性”的与“对象化”的关系?二是采取的是 “实体性”抑或“过程论”的致思方式?三是体现的是“还原论”的抑或彰显“复杂性”科学范式,如系统论的有机联系与互助协同及整体涌现?
不难发现,当今大学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都重视的是上述三个哲学维度的前半段,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活动亟须进行高度的理论创新,必须重视这三个哲学维度的后半段,据此重建新的哲学基础和开出新的大学教育理论,唯此方能走出高等教育研究事实上的“哲学贫困”的局面,尤其是历史理性和科学理性的“哲学贫困”。
1.“新大成智慧学”的哲学基础
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方面,一定要有“把高等教育作为最先进的哲学的实验室”的理论自觉。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钱学森的系统科学哲学这三大哲学思想来源,在综合集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大成智慧学”这个全新的范畴和思想。概而言之,“新大成智慧学”有如下核心观念:
第一,哲学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变—从“实体性思维”到“辩证的过程思维”;从“静态的形态学描述”到“动态的发生学分析”;从“还原论”到强调“整体涌现性”的系统论。[9]
第二,本体论的维新—“可能的事件世界”作为人的哲学真正的起点。马克思“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把“可能世界作为人的哲学的真正的起点”,[10]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将“人的可能世界”进一步明确为“事件的创造性进展”。[11]
第三,认识论的革命—从认识世界的“反映论”到改造世界的“功能论”。科学理性主要由形式逻辑主导,追求的“反映论”和“认识世界”的哲学旨趣;历史理性由辩证逻辑指导,追求“功能论”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旨趣。[12]
第四,“浪漫主义的文化理性”逻辑实现对“机械的科学理性”的扬弃与超越。“文化理性”与“历史理性”是同义语,而“历史理性”又是价值与事实、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人的可能世界”是彰显人的自由本体存在的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13]
总之,“新大成智慧学”就是将“可能的事件世界及其创造性的进展”作为人的哲学真正的起点,而扩张“可能的事件世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钱学森的横断综析的“大成智慧工程”以达到最大化与最优化的功效,实现系统功能的“整体涌现性”和“整体协同”与综合创新。[14]
2.立足于“新大成智慧学”的哲学基础,开出“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
秉持马克思主义的“重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原则”、怀特海的“重有机过程的辩证原则”以及钱学森的“重整体涌现性的系统原则”这三大原则,来开出“动力学的大教育”的如下五条纲领:
第一,“動力学的大教育”的第一问—人的发展的“动力源”来自历史理性所谓的“文化进化”的张力结构及其矛盾运动。在人的发展最为关键的“动力源”问题上,或者说在“人的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上,历史理性的哲学观认为,“文化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后者是千万年漫长的时间积累,同时也是盲目的、受环境的制约性更大;前者体现出的不仅仅受环境制约的一面,更体现出对环境的强力改造的自由与解放的一面。
马克思认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进化机制”。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有两重内涵:一方面,在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上,“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带来比单纯的“认识世界”更强大的发展动能;另一方面,认为改造世界的活动涉及到“两重对象化”,既包括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对象化,又包含对个体的主观世界的对象化。在这两种对象化的活动与过程中所必然面对的诸如“外在的与内在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现实的与理想的”等的张力结构及其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的发展及其自由与解放的动力之源。[15]
第二,“动力学的大教育”的核心问题—不断提升现实的个体的“自觉与自主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化程度”。“历史理性”的牛鼻子或说其核心问题是“对象化”问题,“对象化”的前提条件是现实的个体有较强的“自觉的与自主的自我意识”。张楚廷教授(2006年)提出的“教育的五大公理系统”,其中第三条“反身性公理”就说得很透彻。[16]对象性与自我意识,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解读为建立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关系”,使得外界的“物理世界”变成与我自己“切己相关”的“工具性的世界”。[17]“历史理性”所谓的“对象化”又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问题,“对象化”的程度越高,人的发展的动力越大,人也发展得越好。
第三,“动力学的大教育”是“自因自主的”“唯发展论的”“唯成长论的”。历史理性认为人类生存与发展遵循的是一种“文化进化方式”;体现“自为的自由律”与“非决定论”。[18]因此,在教育的起源与发展观上必须主张“人的发展自因说”,反对人的发展的“外力决定论”和人才培养“模式论”。
如同张楚廷教授(2006年)所言,“教育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发展自己;教育本质上是要让人成为他自己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教育就是要让人的内在精神力量变得更加强大”。[19]而过程教育哲学家怀特海指出,“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具有最大的教育价值”。[20]这也是“动力学的大教育”的灵魂所在。不同于“静力学的教育学”强调“外力决定论”“唯学科知识论”“唯考试论”的倾向,“动力学的大教育”的纲领是“自因自主的”“唯发展论的”“唯成长论的”。
第四,在“有意义的活动”与“事件的创造”过程中不断获得人的发展的新动能。马克思的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追求“功能论”以及“对象化”的改造世界的哲学旨趣,[21]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在活动过程中进行“事件的创造”,[22]在学校教育上反对一味的“学科知识逻辑”,而是更强调“知识的运用”与“生活的经验”逻辑。这些都表明:实践活动过程的重要性,只有在“有意义的活动”与“事件的创造”过程中才能不断获得人的发展的新动能。因此,不断扩充和增加人的发展的新动能,是教育成功的关键!
第五,“动力学的大教育”要突破教育活动的“时空的有限性”,激活和动员系统的全要素进行分工合作与互助协同,以实现系统多方力量的“综合集成”与“最大化的整体涌现”。钱学森(1990年)的“大成智慧学”的系统科学哲学思想认为,系统学的基本原理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要以“恢复事物间的普遍的必然联系”、追求“系统的相互协同与整体涌现”为己任。这就要求,“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强调事物间的有机联系,突破时空的有限性,追求系统内各个局部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协同与整体涌现性”,[23]可以构成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最大“动力源”。
倘若遵循基于钱学森的“系统论”及怀特海的“有机体活动过程论”而提出的这条“动力学的原理”,就必然会使得学校教育走向并成其为一种“大教育”。
以约翰·怀特的“有意义的生活”为例:它是一个肇始于家庭、接力于学校、确证于社会的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过程”且不可能一蹴而就,仅从这一点来看,就能反映出来“有意义的生活”它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大教育”的概念。
综上所述,从原理上说,将局部放在整体中,作为整体中的局部加以考虑,并能与整体中的其他局部互助协同,则必能成就其大。真正的“动力学的教育学”其精髓必然体现为一种“大教育”,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最后谈谈“动力学的大教育”的总体特征及其与“静力学的教育学”的区别:以往的中国高等教育学,无论是观点、范畴还是学科体系,都显露出机械的、外因的、工具的、僵化的、割裂的等特征。譬如:“静力学的教育学” 的“唯学科论、唯分数论、唯考试论”的倾向,必然使它体现为一种“小教育”的格局。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以“新大成智慧学”为哲学基础的“动力学的教育学”, 具有实践的、自因的、自主的、过程的、辩证的、系统综合与开放的等全新特质。它尤为强调事物间的有机联系与整体涌现性,因而也就拥有了无限的创造能力,它彰显的是自由的与创造的生命,并构成了对作为“知识之学”的“静力学的教育学”的一种彻底否定与颠覆!
实践创新 —“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与三种“智慧人”的培养
1.“约翰·怀特方案”—大学教育要使得学生成为一种能够去过“有意义的生活”的人
在约翰·怀特的《学校教育幸福论》中,他不仅抛出了“约翰·怀特命题”,而且也提供了一套他的解决方案,认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要引导学生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能够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某种有价值的活动之中并取得成功,惟其如此才是“良好的存在”(Well-being)或“幸福”的人生该有的状态。相应地,学校教育必须要作出巨大的转变以适应这个新的教育目标的要求。[24]
2.“怀特海方案”—大学教育要培养能运用知识来创造美好生活的“创客”
第一,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大学精神“纽曼路线”与“怀特海路线”的对比。“纽曼路线”的大学精神:坐而论道,重视自由知识、自由学术与自由教育,认為掌握原理性的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以培养绅士为目标;“怀特海路线”的大学精神:在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上,信奉“起而行、行胜于言”,认为仅仅只掌握了原理性的知识,教育过程并未到此结束,而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把知识加以利用,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来塑造美好的生活—“教育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地利用知识的艺术”。[25]
上述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大学精神,体现两种不同的科技传统—“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也体现两种不同的哲学智慧—“反映论”和“功能论与实践论”的哲学旨趣。
第二,“怀特海方案”—如何培养能利用知识创造美好生活的“创客”。怀特海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具有高度自我发展能力、善于综合运用知识进行“事件的创造”的“智慧人”。他认为,文化的精髓是“创造新的知识事件的活动”而不是“碎片化的信息知识”;知识的价值在于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运用,通过利用知识创造事件来极大地开阔自我发展之路。[26]因此,教育目的不是为了求得实在的知识,而是为了利用知识塑造未来的生活。“当我们不再成为知识的奴隶,而学会了积极地、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时候,我们才最终拥有了智慧。智慧高于知识,因为它可以让人获得最本质的自由”。[27]
在怀特海那里,思想与行动结合的“经验逻辑”重于单纯的学科自身的“知识逻辑”,他说“大学的目标是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成人的力量”“教育是教人们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不能让知识僵化,而要让它生动活泼起来—这是所有教育的核心问题”。[28]
3.“钱学森方案”—基于钱学森的系统科学哲学,培养新型的“大成智慧型”人才
第一,钱学森关于“大成智慧学”的教育理想。他的“大成智慧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要求谙熟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现阶段与全过程、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把“还原论”与“整体论”、“性智”与“量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等有机结合起来,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人机结合并以人为主的方式,迅速有效地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古今中外有关经验、信息、知识、智慧之大成,总体设计,群策群力,从而使我们突破障碍,不囿于部门学科的局限,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获得高于任何一门学科的见解,在整体优势与综合创新的基础上,科学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实现前人“集大成而得智慧”的理想。[29]
第二,“大成智慧型”人才的概貌。从人类历史上看,一直都不乏“大成智慧型”人才。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达·芬奇等人也是集大成者;而在中国,如古代的老子等人都是大成智慧集于一身而作出伟大创新的杰出人才,当代的钱学森本人也是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全才。
钱学森要求“大成智慧型”人才应该具有大智、大德的思维结构和内涵,具有全脑型智慧,德艺双修,做到知识与信息层、情感与动力层、智慧与方法层的综合集成。这样的“大成智慧型”人才具体说:“熟悉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30]
这种“大成智慧型”人才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又不仅仅是某个行业的专家,是全与专辩证统一的人才,其擅长从整体和全局上研究和解决复杂性问题是其优势所在。他与常规人才之间也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辩证关系,也是全面发展的一代帅才、将才。钱学森先生认为这种新的“大成智慧型”人才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堪比高等教育人才史上的“文艺复兴”。[31]
经典案例研究—近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教育经历与发展轨迹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1.近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教育经历与发展轨迹
一是学生时代的梁思成如何选定他的“有意义的生活”?16岁~17岁时的中学生梁思成多才多艺,会画画、会弹琴,甚至会开小汽车,但对未来人生目标并无定论。他最终选择“建筑师”作为一生的志业,除了梁思成自身多才多艺的素养之外,还受到来自这么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恋人林徽因的提议。她在英国生活的经历以及她对西方古典建筑之美的切身感受,对年轻的梁思成的影响至关重要。其次,是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时学习建筑学和美学,受到美国大学的科学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最后,是来自博古通今的父亲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曾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寄过一本古籍书—宋代的《营造法式》,对于青年梁思成来说,它像一本很难懂的天书,但是一旦读懂了这本天书,就找到了打开中国古建筑奥秘的钥匙。青年梁思成接受古今中外的多方影响,终于选定他的“有意义生活”的故事,就是一种“动力学的大教育”的最好解读和直观体现。二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开启了梁思成的“创客”生涯。体现的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观—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进而“创造事件”。三是“太太客厅”的男主人与一个真正的“大成智慧者”。梁思成是一个将历史、哲学、艺术、文学与诗歌、建筑与科学等熔于一炉的集大成者。
2.梁思成的教育经历和发展轨迹给大学教育带来的当代启示
第一,培养“知识人”必须向培养“智慧人”的转向。仅以第一种“智慧人”的转向为例来说明。例如:怀特教授所言,教育目标问题上,有两个逻辑:一个是学科、知识、考试逻辑;另一个是“领导学生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逻辑”。前者被人们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定势,而不追问学了这许多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怀特教授认为,这是教育领域最大的迷思,它导致了学生太多的不幸与灾难。与之相反,怀特教授认为学校教育是引导学生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逻辑,在教育目标遵从的逻辑方面,如果说“学科知识的逻辑”仅仅只是少部分人的“动力源”—适用于或者禀赋对路,或者机缘特殊的这部分人;那么“有意义的生活”的逻辑更能构成所有人的成长与发展的真正“动力源”。
第二,上述三种“智慧人”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且对象化程度越来越高。三种“智慧人”的层层递进关系:三种“智慧人”的培养方案之间有一种共同精神气质,但也有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反映的是 “动力学的大教育”的核心问题—“历史理性”所谓的“对象化”问题以及“对象化的程度”问题。换言之,在培养“智慧人”方面,“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所做的那些原理性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怀特的“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自主的个体”要在大千世界中寻找并选定符合自己期待的某种有价值的活动,它也涉及到美学和价值论问题,明确“有意义的生活”只是历史理性所谓的“对象化”的初步,其“对象化”程度也是最低的;怀特海的“创客”比约翰·怀特所提倡的“有意义生活”的对象化程度更高;[32]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型”人才的对象化程度则是最高的。[33]
“约翰·怀特命题”让我们反思,中国高等教育到底是围绕什么运转的?一言以蔽之,是围绕“知识人”的培养而运转的巨型机器,我们必须要实现从培养“知识人”向培养“智慧人”的转向。而立足于“动力学的大教育”纲领,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培养三种“智慧型”人才,以充分彰显人的自由与创造的生命,并开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全新气象,使得高等教育从当下的“机械论的、静力学的与还原论的”“小教育”中跳出來,走向未来真正的“辩证论的、动力学的与系统论的”拥有无限创造力的“大教育”!
参考文献:
[1]约翰·怀特.再论教育目的 [M]. 李永宏,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
[2][3] WHITE J.Exploring Well-Being in Schools: A Guide to Making Children's Lives more Fulfilling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011:1,23.
[4][7]邓钢,陈放,王谦.教育理念的革新—塑造“智慧人”[J].教育发展研究,2006(17):63-67.
[5]鲁洁.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育信条:塑造知识人[J].教育研究,2004(6):5.
[6][20][25][26][27][28]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 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12,45,48,52,66,137.
[8]靖国平.“转识成智”:当代教育的一种价值走向[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3):11-16,72.
[9][14][23]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3,6,10.
[10][12][15][18][21]何萍. 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63,365,526,527,533.
[11][22]A.N.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卷一)[M].周邦宪,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9,13.
[13]鲁洁. 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J].教育研究,1998(9):13-18.
[16][19]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5,37.
[17]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59.
[24][32]约翰·怀特著.教育与“有意义的生活”[J].杨杏芳,赵显通,译.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1):1.
[29][31]钱学森.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5,7.
[30][33]钱学敏.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7,30.
(作者单位:杨杏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赵显通,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