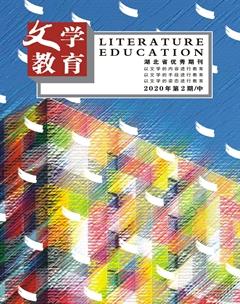制度化译者的爱国伦理探究
高洋
内容摘要:制度化译者具有“被赞助人”、“公务员”、“社会人”三重身份,这三重身份要求制度化译者必须遵守爱国伦理,做出爱国行动。这种爱国伦理适用于国家翻译实践环境下,是政治要求和个人伦理诉求的统一。
关键词:制度化译者 爱国伦理
1.引言
如今,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与全球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国家翻译实践也在不断增长,对“制度化译者”的研究便显得更加迫切。但纵观中西方翻译伦理研究,给予译者爱国伦理这一话题的关注尚且不足。诺德的“忠诚”概念,切斯特曼的“服务伦理”模式似乎与之相似,但终究是西方学者立足于西方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归纳而得出的理论。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属于输出型翻译,夹带政治目的,具有一定特殊性,而且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下的“制度化译者”与西方国家的自由译者或职业译者又大不相同。因此“制度化译者”的爱国伦理与“忠诚”、“服务理论”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本文摸索性探究国家翻译实践中“制度化译者”的爱国伦理,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2.制度化译者的爱国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是人的众多诉求之一,是人社会性的体现。当人按照某种行为规范行事而获得外界认可时,人的伦理诉求便得到实现,其社会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李颖,2018)将伦理诉求运用到国家翻译实践活动中,可以观察到不同翻译主体(赞助人,翻译机构、译者、译审等)的伦理诉求。伦理诉求以价值取向为基础,国家翻译实践的伦理诉求反映的是制度化译者对翻译实践价值的追求,制度化译者的伦理诉求则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遵循某种伦理关系规范,进行具有产生价值功能的翻译选择。制度化译者是国家翻译实践活动中的翻译主体之一,具有多重身份,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守的伦理关系规范也定然不止一种,所追求的翻译选择也必定具有不同价值。因此,对制度化译者爱国伦理诉求的探讨,便不得不剖析制度化译者的多重身份。
制度化译者具有“被赞助人”的身份。国家翻译实践由主权国家自主发起,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目的性和自利性,要求参与各方具有爱国的价值追求。制度化译者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主体之一,在接受国家赞助的同时,也受到政治约束,在这些制约下,制度化译者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国家的关系,遵守“被赞助人”与“赞助人”的伦理规范关系规范,考虑国家利益,满足国家要求,实现国家目的,本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做出每一个有利于国家的翻译选择。
制度化译者具有公务员身份。这一身份会淡化其译者身份,而国家翻译实践的性质在此时也更倾向于是一项国家任务,制度化译者则变成了国家任务的执行者。在执行這项任务时,制度化译者的一切行为选择都会受到政治意识的影响和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的制约,而其中一条便是“维护政府形象和权威,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格、人格尊严”。制度化译者为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的要求,选择放弃选材,决定翻译策略,裁定翻译选择,参与译后编辑、译本署名等原本属于译者的权利,甚至对某些原文的理解,都无权阐释,还需向上级领导请示。既定的制度化翻译流程也呈现出政治特征,译者、译审、最终裁定人之间也存在着行政级别上的差异。制度化译者所有的译者行为都与政治行为高度重合,变成极具政治意识的选择。在行政体系中,制度化译者将公务员身份视作主要身份,并以此身份为准绳开展相关翻译工作。
制度化译者具有社会人的身份。社会人最基本的一层解释便是中国社会的一名成员。在中国社会,自古便有“忠君爱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如今爱国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中国社会对公民的期待和规范,又是一种政治原则,表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要求。而生活居住在中国的公民,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沉浸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并接受着中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爱国是制度化译者作为社会人必然的伦理诉求。历史上,翻译一直与中国社会的兴衰息息相关。佛经翻译维护社会秩序,科技翻译提升科学文明,五四期间的翻译开启民智,五四后期的翻译奠基改革。在社会大背景下,翻译本身的价值十分明显,而译者通过翻译报国、强国所产生的价值也同样不可忽略。与普通译者相比,制度化译者虽然受到诸多制约,但译者身份使之仍然在语言性层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面对当今时代西方对中国的歪曲理解和文化压制,制度化译者会不自觉产生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感和通过翻译报国、强国和兴国的责任感,其社会人的身份也会驱使制度化译者在翻译工作中呈现出“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汪宝荣,2018)。
3.制度化译者的爱国伦理行为
制度化译者供职国家机构,接受国家赞助,服务国家目的,是国家向外传达声音的话筒,虽然其译者行为受到诸多制约,但这并不表明制度化译者就是单纯的“翻译机器”,其“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性选择仍依赖译者(任东升,朱虹宇,2019)。只不过,此时译者的语言性行为选择是在爱国伦理诉求驱动下,以表达中国立场、说明国家政策、展现社会风貌,弘扬中国文化、实现国家目的等为主要考量的爱国伦理行为,其所译文本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甚至浓重政治气息”(同上)的特点。
3.1美化国家形象
由于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不同,西方对中国的政治路线、中国执政党、中国领导人都有一定的曲解,而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长期受到西方霸权主义和西方话语体系的压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他塑”国家形象的被动状态,这往往会导致国家形象的失真,使中国失去有利的国际环境。面对这一窘境,中国主动出击,通过国家翻译项目积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声音。作为“被赞助人”的制度化译者,自然应遵守“赞助人”与“被赞助人”的伦理规范,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纠正错误的西方认识,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
制度化译者沙博理编译的《中国古代刑法及案例故事》一书中,收纳了许多古代断案故事,有官员受贿错判案,也有个人专权独断等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为了避免该书的西方读者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迁移到现代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误解、歪曲,沙博理在后序中提供了基于中国价值观的解释:“他虽然是老百姓渴望的清官。但他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崇拜权威和男权占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的另一种体现”(Shapiro,1990,272页)。除此之外,还说明“近些年,现代中国已经开始努力清除封建思想在司法系统和整个社会中的残余”(同上)。
在建国十七年期间的国家翻译实践中,有许多革命题材的作品,其中不乏反动派血腥暴力的情景描述和浪漫的情爱故事。“但过度的血腥场面及情爱描写会缩小小说的读者群、有损革命人物的高大形象,违背国家翻译机构组织译者翻译革命历史小说的初衷,译文需要对其删减或者雅化,使其更适合对外传播”(任东升,连玉乐:2019)。这种“萃译”方法虽然没有说明具体发生在翻译前、中、后哪个阶段,但其理念仍然是制度化译者在爱国伦理诉求驱动下可以做出的语言性翻译选择。
《习近平治国理政》(两卷)的翻译也体现了这一点。制度化译者将其中一个标题——《“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翻译为“Man of the People:profile of Xi Jinpi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这种译法高度灵活,且符合目的语规范,但这一翻译行为背后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有助于彰显习近平的平易近人、亲民的形象”(陈双双,2019)。《习近平治国理政》(两卷)的翻译使用了“异化、显化、简化、信息重组等翻译策略”(赵祥云,2017),这也是制度化翻译的一种新趋势,制度化译者的爱国伦理诉求也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3.2突出文化因素
韦努蒂(2008)曾指出“归化”、“异化”是一种伦理态度或伦理效果。这种伦理态度或伦理效果体现在制度化译者身上便是爱国主义行为。因为国家翻译实践的选材大多极具中国特色,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中国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想要在翻译中保留本国特色,建构国际化与体系,让国外读者知晓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便不得采取以英语为共核,以中国特色为依托的翻译手段,强调原文本中所包含的中国特色文化。而具有爱国主义伦理诉求的制度化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承载文化责任,持有文化立场,进行文化比较、履行文化使命,并会采取直译为主,兼带意译的翻译手段,以求最大程度地做到文化翻譯保真,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下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这种做法既是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着重宣传中国成就,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也是满足译者自身的文化荣耀姿态,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文化输出层面,自觉承担传播中国文化的重担。
4.结论
制度化译者爱国伦理存在于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语境之下,产生于国家政治要求与译者自身价值诉求的有机统一,作用于带有功利性目的的外向输出型文本。这一爱国伦理是国家翻译实践的核心伦理,是实现翻译目的的重要保障,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助力,也是制度化译者实现自身价值诉求的重要途径。制度化译者爱国伦理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也属于适合中国自己的译学话语,其研究对当今中国致力于走向世界舞台的国家战略和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构都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双双.翻译副文本对原作者的形象塑造——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洪捷.五十年心血译中国——翻译大家沙博理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4):62-64.
3.任东升,连玉乐.《红岩》、《苦菜花》萃译比较研究[J].外语与翻译,2019.
4.任东升.“萃译”之辩[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