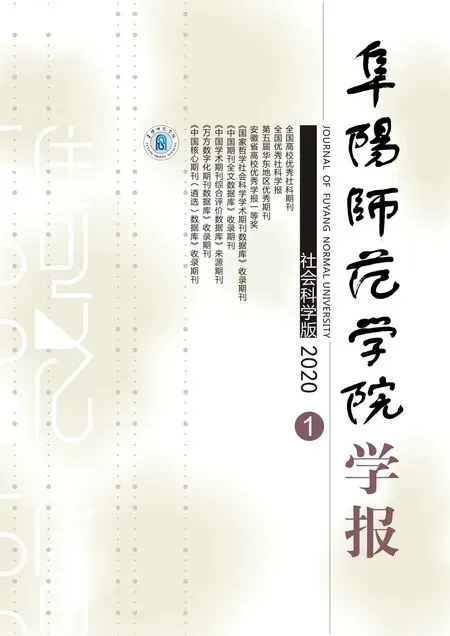孔老相会时间再考察
衣抚生
孔老相会时间再考察
衣抚生
(河北经贸大学 发票博物馆,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孔子和老子相会,可以考察清楚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孔子17岁时,第二次是孔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去周向老子问礼,大致是在孔子43岁到50岁时。《庄子》中的记载难以全信,只能当成孔老相会确实发生的旁证。
孔老相会;老子;孔子
孔老相会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儒、道两家的创始人切磋问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孔老相会的时间,学界有过很多讨论,早期的讨论以阎若璩、梁玉绳、钱穆、罗根泽等学者为代表,往往倾向于将孔老相会定为一时一地。后来的研究以陈鼓应、孙以楷等先生为代表,将孔老相会的时间定为多时多地,从而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然而陈、孙等先生过于相信《庄子》,没有注意到《庄子》一书寓言十之八九,而且往往借老子打压孔子,从而打压整个儒家,因而会对事实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歪曲,不可尽信。我们对《庄子》的利用一定要很慎重。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孔老相会定为至少两次。
一、第一次孔老相会
根据古籍记载,孔老相会发生过多次。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孔子17岁时(公元前535年,鲁昭公七年)。东汉学者边韶《老子铭》说:“孔子以周灵王廿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1]北魏学者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皇甫谧《高士传》也说:“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2](1)郦道元明确说明,这段文字引自皇甫谧《高士传》。但是今本《高士传》内没有相关记载,可能是《高士传》在流传的过程中,内容有较多散逸。参见皇甫谧:《高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近代著名学者高亨先生也持类似观点[3](2)高先生的观点和《水经注》有一个细微的区别:《水经注》认为孔子去周学礼,而高亨先生认为是老聃避难,到了鲁国,孔子在鲁国跟随老聃学礼。。据高亨先生研究,当时,老子因事前往鲁国,孔子早在15岁时就“志于学”,听说老子的到来,非常高兴,前去跟随老子学习。由于孔子此时太小,跟老子学习的主要是婚丧嫁娶方面各种具体的礼节,我们可以确定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是《礼记·曾子问》中的3条记载: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
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
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我们认为,孔子17岁见老子的记载是可靠的。理由是:
第一,据阎若璩考证,当年恰有日食:“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昭(公)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4]这就证明了《礼记·曾子问》记载的准确性。
第二,通过分析这三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孔子思想尚不成熟,对三年之丧这种重要问题都还没搞明白,这显然是孔子早年的事情。
第三,孔子以晚辈的身份助葬,也显然是早年的事情。我们可以在《论语·子罕篇》找到旁证:“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上有公卿父兄,勤勉助丧,当是早年之事。
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将《礼记·曾子问》中的4条记载全部归为孔子17岁时发生的事情[5]。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当。这4条记载都是事后追述,而且是孔子晚年的事后追述,怎么可能一定都发生于一时呢?我们通过细致辨析后,发现有一条不应定为孔子17岁时: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祫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
《论语·八佾篇》说:“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入太庙问礼之事,有可能发生在孔子人生中的很多时刻,不一定是在17岁时。而且17岁正是孔子“吾少也贱”(《论语·子罕篇》)的时候,是否有资格入太庙、了解太庙、能想到这么细节的问题呢?我们认为,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要慎重处理。
《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也有一则老子给孔子讲礼的记载,与这3条类似,很可能是孔子跟从老子参加丧礼时学到的:
子夏问于孔子曰:“客至无所舍,而夫子曰:‘生于我乎馆。’客死无所殡矣,夫子曰:‘于我乎殡。’敢问礼与?仁者之心与?”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馆人,使若有之,恶有有之而不得殡乎?’夫仁者,制礼者也。故礼者,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异,不丰不杀,称其义以为之宜。故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论语·乡党篇》记载:“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子夏问的问题与此有关,可能是孔子受教于老子以后形成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出,孔子17岁的时候,问的还是非常具体的礼,而没有涉及到礼的本质。
二、第二次孔老相会
《史记》记载孔子还曾和南宫敬叔一起去拜访老子。这是第二次孔老相会。
发生的时间,根据清儒阎若璩研究,有两种说法:“《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是为昭公之二十四年。”阎若璩认为,应该以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为是,原因是《礼记·曾子问》记载,孔老相会期间发生过日食,而昭公二十四年恰恰有日食:“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如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公)二十年,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4]
阎若璩给出的这两个时间都有问题,是在误读《史记》原文基础上得出的错误结论。前辈学者对此多有辩正。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有刍见,故不厌其烦,进行详细解说。我们先将阎氏得出结论的《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相关材料罗列如下: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僖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僖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孔子年三十五……
这一段材料是判断孔子和南宫敬叔适周日期的关键。如果此处记载无误,那么孔子和南宫敬叔适周日期是在“孔子年十七”时,而非鲁昭公二十年。钱穆先生说:“《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二十年也。”[6]亦可通。阎氏对《史记》有误读。而且,《史记索隐》早就指出这段记载存在错误:孔子17岁时,孟僖子只是“病不能相礼”,而非“病且死”[7]。而且,孟懿子、南宫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昭公二十年时,南宫敬叔仅为10岁,既未能朝见国君,也无法和孔子适周问礼,甚至还未拜孔子为师。因此,鲁昭公二十年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准确的。
阎氏又据《史记索隐》,认为鲁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去世,南宫敬叔师从孔子,两人适周问礼。这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史记索隐》并未说孔子在鲁昭公二十四年适周,相关记载为:“昭公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这一记载指鲁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命其子南宫敬叔师从孔子,并非指南宫敬叔此年和孔子适周。阎氏明显误读《史记索隐》。毛奇龄在《经问》中已经指出阎氏的两次误读《史记》[8]。其次,南宫敬叔师从孔子之后,跟随孔子适周,并不一定是在师从孔子的当年。因此,我们无法将其确切定位到鲁昭公二十四年。
既然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的说法不准确,那么应该如何确定其年份?我们认为,毛奇龄的说法较为可取:“孔子适周问礼老子,见《(孔子)家语》《史记》《礼记》诸书,本是实事。然但有其事已耳,不必问其年也。”因为我们“实不知在何年”[8]。我们能确定的,只是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后。既然如此,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庄子》说的51岁?清人梁玉绳就持这一观点:“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9]由于《庄子》中并未明言孔子与南宫敬叔问礼,材料不足,而且《庄子·天运》明确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既然是“南之沛”,明显不是适周,因此也不会是孔子五十一岁时。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甚至认为此事是伪造的,理由是:“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6]
我们认为,钱穆先生的分析有其合理之处,但值得商榷。孔子适周学礼于老子,当是事实,见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品,不容否定。但是,至少在司马迁的时代,人们就已经搞不清楚此事到底发生在哪一年,所以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安排此事就颇为为难,导致放错了位置。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把适周之事放到孔子17岁时呢?真的是因为司马迁把“病不能相礼”误读成“病且死”了吗?我们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病不能相礼”和“病且死”之间差别较大,难以取信。更有可能的是孔子17岁时确实见过老子,后来也确实和南宫敬叔一起去向老子问礼,司马迁把两件事弄混了,才都混到孔子17岁时。这种混乱也证明了孔子17岁时发生过孔老相会。
我们虽然无法确定这次会见的时间,但是却可以缩小范围。詹剑峰先生曾经对此有过很细致的考察:
据史实推断,孔子适周当在三十一岁以前。因为鲁昭公二十二年(孔子三十二岁),周室已发生内乱,打了五年之久,孔子当然不能于周家两派贵族武装斗争之时去观光问礼。而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也发生内乱,昭公出奔,国内无君,孔子因乱适齐,流亡在外也有几年,自无“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之事。而鲁昭公二十六年,周室王子朝已“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也因之免官归居于陈,孔老自无在周相见之理。根据此等实事,我们假设孔子三十岁左右,鲁国有一位南宫先生向鲁君请求同孔子一起到周去观光,鲁君给了他们以物质上的帮助。在周访问的时候,顺便见了老聃。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10]
詹先生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鲁昭公二十五年到三十二年,昭公外奔,鲁国无君,南宫敬叔自然不可能见到鲁君。鲁昭公二十二年爆发的周王室内乱,也会导致适周的困难。该年,老天子周景王去世,他的两个儿子——新天子周悼王(又称为王猛)和其弟王子朝——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激烈的战争。通过分析《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室之乱,我们可以发现:在长达五年的王子朝之乱中,王城(或曰成周,今洛阳)及其周边地区是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被反复围困和争夺。孔子曾经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篇》)。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确实不适合去王城学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昭公二十三年六月,王子朝进入王城,并占据了三年之久,一直到鲁昭公二十六年十月(《左传》认为是十一月),周敬王才在晋国的帮助下,重新夺回王城。孔子或许不会在叛乱者王子朝占据王城的时候,去周学礼。
然而,我们不赞同詹先生将孔老相会时间向前推的做法。我们注意到,孔子当时尚无法面见鲁国国君,需要南宫敬叔在中间传达,而且鲁君对孔子及其家世并不了解,需要南宫敬叔进行大篇幅详细介绍。这说明:
第一,当时的鲁国国君对孔子和孔子的家世尚不是很了解,而鲁昭公对此非常熟悉。孔子20岁时,尚默默无闻,却受到鲁昭公的关注,并在儿子孔鲤出生后,得到鲁昭公的赏赐。这说明,当时的鲁国国君必定不是鲁昭公,而只能是鲁昭公的继任者鲁定公。因此,这次孔老相会发生在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之后。
第二,南宫敬叔已经成年,并且从政,因而能对国君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宫敬叔生于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假设他实行冠礼并且任职朝廷是在20岁之后,那么这次相见最早不会早于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
第三,当时的孔子尚未出仕,所以才需要别人中间转达。孔子出仕是在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担任中都宰,此后朝见国君就不需要南宫敬叔在中间转达,而且会被鲁君熟知,不需要介绍其家世。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次孔老相会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509年至502年之间,此时孔子43-50岁。
通过这次相见,孔子对老子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对老子也更加崇敬。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曾对子贡喜欢议论别人的做法进行过批评(3)《论语·宪问篇》:“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反对欲望过多(4)《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和有骄气(5)《论语·泰伯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自认为能较好地侍奉长辈和上级(6)《论语·子罕篇》:“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些都和老子对孔子的劝诫是一致的,很可能是孔子对自身经验和老子劝诫的总结。可以说,老子给了孔子非常及时有效的劝导。
三、《庄子》中记载的孔老相会
《庄子》中多次记载孔老相会。陈鼓应、孙以楷等先生都对这些记载深信不疑,并据此来研究孔老相会、老子思想的转变。其实,前辈学者早就指出,《庄子》一书寓言十之八九,不能全信,陈、孙等先生未免走向极端了。下面,我们结合《庄子》中的记载,进行分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庄子·天运篇》)
这是《庄子》中唯一有确切时间记载的孔老相会。这段记载中的老子形象与《道德经》一致,反映了老子的思想从《礼记·曾子问》时的知礼、守礼转向自然无为的过程。这是其合理性,但是,问题也不少:
第一,孔子51岁时正担任中都宰,事业处于上升期,而且公务繁忙,既不会认为自己没有得道,也不可能抛下公务,跑到国外见老子:“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亦无暇适周矣。”[6]
第二,孔子曾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过总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篇》)。三十而立,立于礼也;四十而不惑,“知者不惑”(《论语·子罕篇》),智也。孔子30岁就在礼乐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坚持终生;40岁就形成了自己的主见,不会再迷惑。那么,孔子到了51岁时,听到别人非议仁义礼乐的言论,又怎么会特别信服呢?如果孔子特别信服,为何始终没有改正呢?这种矛盾是《庄子》的记载不能全信的明证。
既然孔子51岁时见老子不可全信,那么《庄子》为什么要这样写?答案很可能是:孔子“五十而知天命”,50岁左右而达到了知天人之际的很高境界,《庄子》想强调孔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道家给的,是学道的结果。既然儒家的最高境界来自道家,而且孔子的这种境界没有传下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篇》),那就不必学儒家,直接学道家就好了。也就是说,《庄子》通过这一记载达到了压制儒家、鼓吹道家的重要目的。
我们再举《孔子家语·观周》和《庄子·天运》的相似记载,来说明《庄子》的可靠性问题: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庄子·天运》)
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知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孔子家语·观周》)
《庄子》和《孔子家语》都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孔子到处游说诸侯,效果很不好,又找不到原因,就向老子请教。儒家、道家著作都有记载,可见此事应为事实,或是当时流传较广的说法。然而,两书所记载的老子的话,却差别很大。《庄子》中的老子,强调的是自然无为,反对儒家的仁义学说,对孔子和儒家进行根本上的否定。《孔子家语》中的老子,强调的是游说的技术细节,展现的是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并没有对孔子和儒家进行根本上的否定。我们认为,《孔子家语》的记载较为平实,也较为符合孔子和老聃当时的特点,因而是比较准确的。《庄子》的记载较为玄虚,明显具有道家打压儒家的意气之争,很可能对事实有所引申和调整。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庄子》中的孔老相会故事,可能不完全是虚构的,而是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进行了再创作。只是这种再创作,往往会将故事主旨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引用时一定要非常谨慎,需求旁证,而不能直接当作事实。这就是我们不赞同陈鼓应、孙以楷等先生考证结果的地方。
结语
通过分析前辈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孔老相会发生过多次,早期的学者们却误认为只有一次,想把所有的记载都统一到同一次相见之中,于是无论怎么安排都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后来的学者们不管《庄子》记载的诸多问题,完全相信《庄子》的记载,从而走向偏差。
总之,我们认为,孔老相会发生过多次。第一次是孔子17岁时,第二次是孔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去周向老子问礼,时间大致是在孔子43岁到50岁。《庄子》中的记载难以全信,只能当成孔老相会确实发生的旁证。
[1]洪适.隶释·卷三·老子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6-37.
[2]郦道元.水经注校证·卷一七“渭水”条[M].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 412.
[3]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79(1): 35-39.
[4]阎若璩.四书释地续[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5]陈鼓应,白奚.孔老相会及其历史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22-26.
[6]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10.
[7]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08.

[9]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五·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16.
[10]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0-21.
Analysis of the Meeting Time of Confucius and Lao Tse
YI Fu-sheng
(Museum of Invoice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Hebei)
It can be clearly confirmed that Confucius had met Lao Tse twice. The first meeting was in 535 B.C. when Confucius was 17 years old. The second meeting was between 512 B.C. and 502 B.C. when Confucius was between 43 and 50 years old. The records incannot be all true and can only be used a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Confucius-Lao Tse meeting; Confucius; Lao Tse
2019-05-11
衣抚生(1982- ),男,山东烟台人,历史学博士,河北经贸大学发票博物馆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
K22
A
1004-4310(2020)01-0013-06
10.14096/j.cnki.cn34-1044/c.20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