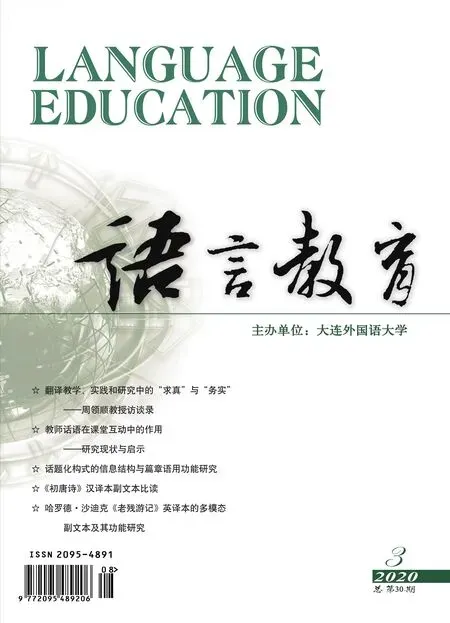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
——《最漫长的旅行》之解读
胡振明 徐婵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在英国著名现代作家E·M·福斯特所写的小说中,《最漫长的旅行》(The Longest Journey)一书总能激起评论家们的兴趣,同时这部小说又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福斯特本人这样说过:“这是我最钟爱的作品……因为与其他作品相比较,我在这部作品中更为接近心中所想,或者说更为接近心灵与思想的交接点,创作冲动闪烁其间”。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么个尴尬事实,这部小说是“我的五部小说中最不受欢迎的”(Forster,1984:166)。
文学评论家们承认福斯特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投入了比其他作品更多的激情,“他是在心里写作,把心中全部激情、魔力与情感付诸于纸端”(Furbank,1977:148)。但他们对《最漫长的旅行》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莱昂内尔·特里林盛赞这部小说是福斯特作品中“最出色、最具有戏剧性、最有激情的一部”(Trilling,1982: 56),而卡瓦列罗则指出“这部小说的成功总是令人质疑”(Cavaliero,1979: 74)。无论我们怎样去评价福斯特这部心血之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漫长的旅行》显然是福斯特作品中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Rose,1971: 51)。福斯特写这部小说时,正值他迈出象牙塔,踏入社会之际。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虚伪对这位接受了人文教育的年轻小说家的人生观与个人情感产生了极大影响。毫无疑问,当时的他“处于几近相同的状态……即自己大学生活中与世隔绝的世界与普通的现实生存需要彼此妥协的状态”(Crews,1962: 50)。通过小说主人公里基(Rickie)的故事,福斯特把不同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自己的困惑以及被遗弃感付诸于笔端。如此一来,这部小说成为一个难得的,能让读者、评论家了解福斯特创作理念、生活态度的文本,“《最漫长的旅行》对理解福斯特的思想及其作为小说家的抱负具有独特的重要性”(Martin,1976: 47)。
一
《最漫长的旅行》甫一发表,在1907年5月18日的《雅典娜神庙》(Athenaeum)杂志上就刊出了这么一篇未署名的书评:“《最漫长的旅行》可以被描述为对一位热切的理想主义者展开的细致研究。主人公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情境的变化被迫陆续放弃自己绝大多数的理想,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目睹了理想的逐步消解以及部分重建”(Gardner,1973:86)。这篇书评不仅勾勒出小说的轮廓,而且为后来的评论奠定了基调。“理想”与“消解”成为这些评论的关键词,评论家们也相信存在着某种对立,文本分析应该由此入手。罗斯·麦考利看到,“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看法,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热切对立,真相与谬误,存在与虚无造就了福斯特的作品(无论其是怎样的文类)整体结构的统一性”(Macaulay,1938: 10)。
尽管对福斯特作品分析所展开的二元对立观点具体表述各有不同,然而,它们大致可以被概括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评论家们极力找到一个诠释里基一生悲剧的令人信服的说法,即他的理想与现实相违背,因此遭致自己不可避免的失败。对他们来说,现实是一把标尺,不仅测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且还起到规范性的作用。因此,“里基所犯的极大错误就在于未能让自己适应现实,不客气地说,是他还没有成熟”(Gransden,1962:51)。在这些评论家们看来,里基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导了自己的判断与观察,并且把外部世界扭曲以此适应自己心中的那个美好范式。无情事实带来的极大冲击力不仅让他的理想幻灭,而且还导致他的终极悲剧,死亡,他身上那迂腐的墨守成规以及耽于幻想的性情成为失败的脚注。
不难看出,评论家们似乎将“现实”视为人人接受、遵行的唯一标准,即个人主观意识的对立面。“现实”被用来检验主观意识准确与否。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本身并不是白纸上的一个墨点,而是一个有着多维度、多面的事实存在。如果某个事实从不同角度来审视,我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还会彼此对立。因此,理解与自己所选择的观察视角密切相联系。在众多的观察视角中选择其一,并以这个自认为最佳的视角进行观察以期获得准确的认识,这本身就意味着此举受本人的主观意识主导。对现实的观察并不如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与主观意识绝然对立,而是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我们以小说中斯蒂芬(Stephen)被发现是里基的同母异父兄弟为例。里基非常惊恐地知道自己与粗俗的斯蒂芬有血缘关系后,他决定面对事实。而在妻子阿格尼丝(Agnes)看来,与斯蒂芬沾亲只会带来羞辱,因此极力阻止丈夫向斯蒂芬告诉实情。一直把斯蒂芬抚养带大的菲林夫人(Mrs.Failing)长期保守这个秘密,只是在里基言语冒犯她之后,出于报复目的而告诉实情。我们看到对于斯蒂芬与里基是兄弟这个事实,上述三人出于不同的动机而随后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说明同一个事实具有不同的意义层面,从而导致不同的后果。每个人所理解的意义层面就是他所认为的现实与事实。对现实的观察因个人的视角而不同,也就是说,每个人眼中的现实并不是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表象。
尽管我们试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现实,但总是无可避免地受制于自己的局限性。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事物,我们总是根据自己以前的理解进行解释,并且无法超越现有的知识范围。同时,在特定时间以及特定情境下,我们只能选择一个视角来理解现实。这个选择意味着将其他视角以及其他阐释现实的可能选择都排除在外。不难看出,对现实的理解,对真相的寻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性,只是个视角问题。评论家们所看重的“现实”主题事实上就是置身于某个房间时周遭的若干面墙。这部小说“质疑了现实的性质,以及个人观点的相对性……‘真实’成为一个非常令人怀疑的字眼出现在福斯特笔下英国中产阶级人物的话语中”(Forster,1984: 7)。
我们看到,解读《最漫长的旅行》这部小说不应该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角度而展开,而是从分析受各种主观意识主导,并对现实有不同看法的理解入手,在呈现小说里面“现实”不同层面的过程中探讨产生不同观点的内在动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小说的关键所在。为此,应该把小说中对“现实”主题所有不同层面的理解置于一个共同的场域中,这个提供充分展示它们彼此之间互动关系空间的场域可以被称为“权力场”。
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尼采这样写道:“每一个本能就是某种对权力的欲望;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的视角,并会将之强加于所有其他本能之上以作标准规范”(Nietzsche,1967: 13)。权力是一种主导或影响他人行为或事物进程的能力,根据尼采的观点,每个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体都在强迫他人接受由自己的视角而制定的标准,这无疑就是一个谋求权力的过程。米歇尔·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种人类关系就是权力关系”(Foucault,1980: 168)。应该指出的是,福柯此处所指的权力超越了我们传统认识,是“被分散的、不确定的、异形的、无主体的并有复制性的,这构成了个人的存在与身份”(Best &Kellner,1991: 48)。因此,权力不再局限于社会关系层面,而是构成个人认知与存在的一部分。同时,福柯把权力界定为“一种多样的、流动的,并具有深远意义的强力关系场域,此间从未有过完全稳定的统治效果”(Foucault,1980: 102)。在后现代语境中,权力的实质并不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力量,并不如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命令与主宰他人,而是由所有组成者构成的流动的互动关系,因此社会也就可以被视为一个由具有主体欲望的个人所组成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每个欲望都有自己的拓展空间,具有获得主导、命令他者的能力,因此流动性成为权力场最显著的特点。在这个个体权力彼此争斗的动态场域中,主导权力的地位也势必是暂时的与相对的。
我们可以把《最漫长的旅行》这部小说视为一个虚拟的权力场。根据小说人物对现实的不同看法,他们的主体欲望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可称为知识分子的欲望,以里基与安塞尔(Ansell)为代表。他们期望在现实的复杂表象之中把握本质,寻求真理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他们还力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现实,尊重真理。然而,因为知识权力的介入,他们寻求真理的努力成为权力拓展过程,对现实的理解偏离了自己的初衷。阿格尼丝与菲林夫人属于第二类欲望,生性虚伪、冷酷,眼中的现实就是以达到个人私欲为旨归,并在每一个层面都与知识分子的欲望构成对立。而斯蒂芬则是第三类的真挚性情之人。尽管想真实地生活,但他尊重现实的客观独立性,并没有试图加以改变。本质上来说,小说人物中凡此种种对现实的理解构成了权力场中的个体权力,相互纷争以求获得主导地位。它们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聚焦在里基,小说主人公身上,并被表现为“不同人物与力量为控制里基而展开的争斗”(Colmer,1975: 71)。
二
《最漫长的旅行》以“当奶牛们被某人看到时才存在,还是它们自己就存在?”(Forster,1984:3)这个关于“客体存在”的哲学问题为开始。里基并没有参加被简化为“奶牛在这儿吗?”的哲学讨论,只是静静坐在一边的旁观者。对于天生跛脚的他来说,他对残酷命运的悲戚超越了他对形而上问题追问的兴趣。这位残疾,但心地善良的男孩自小就饱受家庭中无爱的冷遇。他的父亲是一位道德败坏、身体残疾的恶人,因为他的虚伪、自私与残忍,里基的母亲最终选择离家出走。在里基父亲看来,儿子只是一个徒增笑柄的可怜虫;而善良的母亲则害怕亲近自己的孩子会让她与别人相好的事情为人所知。因此,这个可怜的孩子从小是在极度孤独中长大,幻想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童年的不幸生活必然给里基的心灵带来创伤,让他痛恨自己的残疾,渴望完美,同时又让他极度渴望爱。他知道父母之间并不存在爱情,也品尝到不幸福的婚姻所带来的苦涩,所以他珍惜真正的爱情。然而,他并不知道何为真爱,这就为他后来所犯下的将外露的激情视为真爱的错误埋下伏笔,而这一切认识都是“以他自己的直觉为基准的”(Stone,1966: 190)。
可怜的里基在家得不到温暖,在学校里又遭到杰拉德(Gerald)等人的戏弄,一切的悲惨直到他步入剑桥大学后扭转。这所欢迎一切真理寻求者的大学展开双臂拥抱了里基。“剑桥大学……代表了质疑、开放以及寻求真理之热切的态度”(Crews,1962: 50)。在这里,里基极为厌恶的虚伪、虚假被关在门外。里基获得自尊的同时还与同学们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正是在剑桥大学求学生涯中,在这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里基重新得到了自信。
尽管里基力图像剑桥的同学们那样掌握现实的真实意义,但他缺乏清醒的观察,深邃的洞见以及不偏不倚的思考。准确了解客体就应该观察它的真实状态,而不是用自己的视角与理解来决定客体存在的方式。这就是“奶牛在这儿吗?”哲学问题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他看到阿格尼丝与杰拉德激情地拥吻在一起时,原本面无表情的她“瞬间闪耀出如星辰般的神秘之美”(Forster,1984:39)。他一度同情阿格尼丝,因为她即将面临不幸的婚姻,但此刻的她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那位从小就欺负他的粗鲁、野蛮、冷酷的杰拉德也因为这激情一吻而在里基眼中成为一尊端坐在永恒宝座上的神佛。可见,里基渴慕的爱情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但显然此时的里基“将性欲解读成超凡的爱情”(Stone,1966: 200)。更糟的是,他还对此痴迷不已。他的想象以及内心的渴望使判读产生误差,不仅被表象所迷惑,而且还认定这是现实的真实意义。而对于斯蒂芬,里基只是看到他身上粗俗的一面,无视他的真诚。里基用知识分子举止文雅的标准来评判斯蒂芬,在偏见的左右下,他把斯蒂芬的坦率视为粗俗,不顾及后者蔑视陋习,充满爱心的事实。甚至当里基得知斯蒂芬奋不顾身救孩子时,他“宁愿去想到他的粗俗,他那粗野的忘恩负义以及毫无敬重上帝的心”(Forster,1984: 135)。斯蒂芬身上所具有的“原始人般的真实性”(Brander,1968: 110)是匿于粗俗的举止之下,并不容易被人识别。里基对阿格尼丝与斯蒂芬的判断都有偏误,要么用主观想象,要么用偏见给现实中的人们赋予了不准确的认知。
里基的剑桥同学兼好友安塞尔曾经这样劝过里基,“世界物象可能有两种:第一是诸如奶牛那样的真实存在的物象;第二是某种病态想象的主观产物,我们赋予了它真实的表象,结果遭致我们的毁灭”(Forster,1984: 18)。对于这位“客观追求真理”(Beer,1962: 77)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与虚假恰如他笔下所画的圆圈,里面套着正方形,正方形里再套圆圈,如此下去。真实、真理、真相就是画正中那个无法画出的点。安塞尔看出阿格尼丝是一位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想法的女人,她并不爱里基,只是出于用别人替代自己两年前去世的未婚夫杰拉德的目的而选择了里基。安塞尔预感到这场婚姻会带来最可怕的灾难。同时,安塞尔对斯蒂芬抱有好感,认为他是自己所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完全不被那些表象所误导。小说中的安塞尔与里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在认知外部世界的方面成为鲜明的对立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塞尔是宗教里的先知……摆脱了精神层面的束缚”(Crews,1962: 56)。
阿格尼丝与菲林夫人则是现实生活中虚伪的化身。阿格尼丝有强烈的控制欲,婚后的她一再践踏里基的生活原则,不断用虚假来折磨这位善良、社会经验不足的知识分子。她成功掩饰了自己真实的自私意图,使里基愈发沉溺于那些虚假的表象之中,最终,她使里基相信并接受了她的虚伪世界。她极力阻止里基与斯蒂芬相认,这让里基于心不安,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位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思想上迂腐,主观上邪恶,手段上虚假,只是想着操纵他人以满足自私所需。菲林夫人是里基的唯一近亲,里基所珍视的真理与善良在她眼里简直一文不值,只会用讥讽来发泄自己对健康美好事物的嫉恨,以及逃避现实。她“热衷误导他人,最终真假是非观点被遮蔽,误导了自己”(Forster,1984:267)。这位只想在伤害他人中找到自信,在虚假中找到寄托的菲林夫人出于报复之心而告诉里基,斯蒂芬是他的同母异父兄弟,借以嘲笑她害怕面对的真实世界。
小说中的斯蒂芬则是“诗歌与叛逆之子”(Forster,1984: 234)。虽然是在菲林夫人家长大,但没有被后者的虚伪、冷酷和愤世嫉俗毒害。当他被挪揄回答自己未能救出来的孩子灵魂会怎样时,他大声说道:“需要一座桥,而不是所有这些空谈”。在他看来,连接起每个人的心灵之桥是拯救灵魂的途径。当他得知临近学校的一位小学生遭到欺负时,他随时前去帮助这位如当年里基那样的受害者,而不是像一些伪君子那样给可怜的小学生写封无动于衷的信,说什么“精神的成长出于患难”。他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宁愿自己去死也不从自己不爱的人那里接受任何钱物。不难看出,斯蒂芬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美玉,“是自然‘事实’的‘真实’之美的化身”(May,1997: 36)。他与安塞尔都是有志于真实而真挚地寻求真理的人,只不过前者出于质朴本性,后者出于智识。福斯特本人对斯蒂芬偏爱有加,认为他“引领了我们人类的未来”(Forster,1984: 278)。
三
当里基指责安塞尔对阿格尼丝无礼时,安塞尔回答道,“我当然是位有礼貌的人,甚至对那些未被救赎的人也是如此(‘未被救赎’是他们当时用来指那些自己不喜欢或了解不多之人时的用语。)”(Forster,1984: 17)。那么,谁来救赎呢?谁将被救赎呢?救赎的动机是什么?随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勾勒出小说中不同主体欲望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同的现实理解指导下,权力场中的每个欲望都在救赎他者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番努力的实质就是使自己的欲望视角成为指导标准。对里基来说,他想把自己的妻子与同母异父兄弟从虚假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并接受他对现实的理解。而阿格尼丝,她极力让里基适应现实社会,如她所愿,这就是她理解的对里基的救赎。斯蒂芬则要用自己的真诚来救赎里基那颗在索斯顿学校虚假世界里日渐麻木的灵魂。
如前所述,里基仅仅因为看到杰拉德与阿格尼丝的激情之吻就将爱情具化于他们两人身上,出于肉欲之欢而在一起的两个冷酷而虚伪之人瞬间在里基眼里成为了天神般的人物。杰拉德猝死之后,里基在前去安慰阿格尼丝的同时一厢情愿地让她永远记住曾经拥有过的伟大爱情,而且还非常可笑地将捍卫这份未曾有过的爱情视为自己的人生意义。他不敢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对阿格尼丝的爱慕,甚至与她结婚后还要提醒妻子“杰拉德曾经给予过你的远远超过我能给你的”(Forster,1984: 72)。在他看来,如果阿格尼丝忘却这份情感等于是背叛,所以永远将之铭记就是让阿格尼丝永远保持真实的自我。可见,里基的最大错误就是“将别人理想化,并赋予他们原本就没有的感情与价值观”(Finkelstein,1975: 48)。阿格尼丝并没有如此高尚,她出于现实的需要而选择和里基在一起,并且决意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当里基为未来职业选择感到困惑时,阿格尼丝为了迎合他而称赞他写的故事很好,而内心却毫不喜欢。里基的作家之路走不通时,阿格尼丝劝他前往索斯顿学校任教。在这所腐败庸俗的学校里,里基日益感到压抑与苦闷,原本雄心勃勃拯救他人的里基现在成了令人摆布的可怜虫,“她撒谎,并教他撒谎;她使他远离那些适合自己的书籍,远离朋友与兄弟,简言之,她极力操纵他”(Forster,1984: 249)。
阿格尼丝并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她要么被别人征服,要么征服别人,她的征服夹杂着某种残忍”(Trilling,1982: 66)。有强烈控制欲的她一步步带着里基踏入她的虚伪世界,并成功地让他“发现自己既不能在自己并不适合的工作中,也不能在不再尊重自己的妻子身上找到亮光,而且他也不再爱她”(Forster,1984: 177)。同时,她极力阻止里基与斯蒂芬相认,甚至想用金钱来收买斯蒂芬。她所做的无非出于自私的动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歪曲事实,欺骗他人。里基这位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中节节败退,并且最终认识到:“我们的灾难要归结于我的性格,而不是婚姻”。他意识到自己还是走上了曾经极力避免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种种欺骗与虚伪让他喘不过气来,所能做的就是远离这一切。当他放弃了对阿格尼丝的救赎后,“世界又再次真实了”(Forster,1984:266)。
里基得知自己与直率到近似粗鲁的斯蒂芬有血缘关系后惊恐地晕倒。斯蒂芬的出现似乎重新揭开里基不幸过去的一幕幕。然而,尽管现实残酷到令里基心寒,他仍然认为无论怎样,自己必须面对并接受这个事实。在他看来,掩饰真相,逃避事实违背了自己在剑桥所遵循的、令他重新获得自信的求真原则,撒谎无异为精神的堕落。然而优柔寡断的他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背叛了自己的原则,屈从于阿格尼丝的操纵。里基始终对此有内疚感。当得知斯蒂芬可能被送往国外时,他为自己兄弟的困境而自责。事业不顺,爱情不再,内心痛苦的里基终于下定决心与阿格尼丝决裂,选择与自己的弟弟一起生活时,他的出发点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拯救,即让斯蒂芬戒酒并与过去的生活割裂,从此过上体面的生活。他曾经用爱情来试图拯救阿格尼丝,这一次是用自己对母亲的爱来拯救斯蒂芬。在他看来,“斯蒂芬已经变形,已经神圣地成为母亲慈爱的肉体化身”(Colmer,1975: 77)。他的这番拯救改造一如上次那样毫不奏效。当斯蒂芬指出里基的问题所在时,里基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把这个兄弟视为过去的符号,并试图给这个符号赋予自己所想要的意义。等到他自认为已经让斯蒂芬戒酒,自己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时,斯蒂芬的故态复萌给他以致命的打击:“第二次破产了……再一次假装人们是真实的”(Forster,1984: 270)。绝望之际,他将醉酒的斯蒂芬从迎面而来的火车那里救了出来,自己却重伤,结束了失败的一生。
阿格尼丝用虚伪来消解里基的所谓拯救行动,而且还借机操纵后者。而斯蒂芬则尽全力让里基明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当斯蒂芬得知早在两年前里基就已经知道他们有血缘关系时非常震惊。他宁愿要粗俗的真挚,而不要虚伪的文雅。他这样批评里基,“你最大程度地伤害了我心中的某件事,我一度认为它并不存在”(Forster,1984: 245)。当他看到里基日渐堕落而痛苦不堪时,他真挚地邀请里基与自己一道开始新的生活,离开那些让自己成为野兽的虚情假意之人,忘掉已经毫无意义的过去。在这份真挚的感召下,里基下定决心翻开生活的新一页。在新生活中,里基在斯蒂芬身上找到母亲那种善良越多,他就越发地将斯蒂芬视为新的理想范式。斯蒂芬察觉到了这一点,看到里基又在犯同样的错误:“一个人所有的思想不能归属于任何他人……你不能占有他人”(Forster,1984: 261)。裹上一层想象面纱的事实并不等同于理想的现实。可惜的是里基离开人世时才明白这一点。但里基的死也的确改变了斯蒂芬。多年后,当斯蒂芬与自己可爱的女儿嬉戏时不禁想到:“他还活着并且创造出生命……他的精神在痛苦与孤寂中消逝,但不知道所遗赠下来的拯救。‘他会注意到他给我的东西吗?’”(Forster,1984: 278)。里基生前未能完成的救赎却在死后得到实现,这一次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救赎。
在《最漫长的旅行》小说中的权力场中,每一个主体欲望都参与了权力关系的互动,其目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他者遵从的标准。作为知识分子的里基发现自己追求真理,了解真相,谋求拯救的努力结果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而不是如其所愿。这令他困惑不已,而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窘境。在福柯看来,权力无所不在,而且“真理”与权力密切相联。真理源自权力关系,而且在此间滋养。因此,“有必要想到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不应该用‘科学’‘意识’这类的术语来解读,而是用‘真理’‘权力’来思考”(Foucault,1995: 76)。因此,知识分子们执迷于真理,对他们来说,真理不仅是现实的正确表象,而且还有校正谬误的力量。他们也的确试图用超脱外在干预的真理客观性来评判一切,然而他们没看到权力场中的真理并不如他们所想,真理本身也经历了某种变化。真理“不再是绝对的……静止的,一旦明示就万事大吉,而是相对的、遗传的、演变的”(Stone,1966: 48)。而且,真理不可避免地在权力场的互动中谋求主导他者的力量。
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寻求真理之路也就是寻求权力之路。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想借助真理来颠覆或者重建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场。事实上,真理只是一股将知识分子们的愿望吸入权力场的向心力,而不是将他们的目标超越于此的离心力。出发的起点最终成为失败的终点,这难免让他们困惑不已。小说中的里基所寻求的真理其实是自己理想的想象阐述,在寻求的过程中他不自觉地视其为某种救赎,而本质上又是寻求权力之路。他将社会与现实理想化,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来改造爱情、兄弟之情以及自己的事业,期待这一切如自己所愿那样“真实”,但他的失败也就在自己迈出的第一步,做出的第一次尝试中埋下了种子。里基的悲剧也正是福斯特本人处于理想与现实张力之间种种困惑和窘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