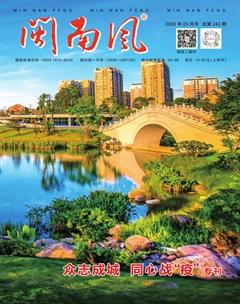我的念想
杨西北
我居住的地方属老商业区,道路四通八达。因为新冠病毒的防控需要,已传出小区要封行,限制居民的外出和访者的进入。心想,要如何封路呢,大小的路口有七八个。没想到,有天下午看到最近的路口开始打框架,一夜之间,所有的路口都封死了,封墙上还有“不准破坏,上有探头”的标语。仅留下数百米远的一处大路口,有一个可关的活动门,有人员守着,任何人进入都得测体温。居民们开始领取通行证,每家每天只能允许一人外出买菜等生活必需品。大家似乎很快就适应了,说到底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毕竟是罕见的一次,还是令我感到某种拘谨、紧张和些许不安,疫情肯定是严重的。虽然老老实实呆在家中就是不添乱,就是贡献,甚至与爱国聯系在一起。我还是安静不下来。
好几个夜晚,我出门上街,就是在街上走走。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因为整个社区都没有疫情感染者和疑似病者,所以没有太多的恐惧。才八九点钟,原先非常热闹的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车迹罕至,安静得很。空气格外新鲜。我将口罩捋到下巴,独自享受这个世界的静谧。这样的安静当然是反常的,任怎样的闲庭信步,心里也是安静不下来。倒腾着的东西太多,一波一波。
地方上已经派出几批医疗队驰援被封城了的武汉。那是一处没有硝烟的战场,战场是会牺牲人的,已经有白衣战士倒下来了。这些年轻的医务人员心里是明白的,他们仍然听从召唤,义无反顾地出发了。我在微信上看了他们出发的照片,我看得很详细,就是想记住他们。地方媒体上对他们在方舱医院电话采访所透露的片断信息,牵动着许多人,让人感受到艰难,也感受到希望。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人性的礼赞。
有一位目睹家乡汶川在地震时和地震后的状况,下决心从医的护士,也加入到援助武汉队伍中,她说,当年全国那么多人帮助我们,这次我当然要站出来。我想到十多年前汶川大地震数日后,我到那里采访,认识的一个很幸运从瞬间垮塌下来的教学楼逃生出来的女生。面对几十条天天在一起的性命顷刻消失,她几近崩溃。但她终于走了出来。已为人师的这个女生现在喜欢收养流浪猫,似乎周围还有一圈人。前几天我在她的微信中看到她如此疼爱地为膝下的猫们起名字,受到触动。这是从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在旷寂无人的街道行走,脑子特别活跃。我想,如果我是医生,会去武汉吗?当年传播抗震救灾的事,有艰难有危险,做了,直接救人的事,还有犹豫吗?
大学的同学,有不少是湖北的,有多人后来就留在武汉谋生。我们的同学群中,疫情爆发以来,所有的微信几乎都与武汉有关。有喜欢唱歌的同学录了歌发出,表达感情和声援。幸运的是,这几个在武汉的同学因为居住地都封得早,平安无事。他们老老实实宅在家中,却也忙得很,忙着了解已进入战时状态的疫情防控,忙着同外界交流情况。如今媒介空前发达,信息满天飞扬,遇到真假难辨时,他们就成了最理想的咨询对象。他们毕竟就在最前方,最了解情况。对于远在福建一隅的社区,每日还可以外出一次,他们是非常羡慕的。我综合他们发出的种种文字和视频,我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武汉必胜!大学的同学们数年前已商定,两年聚会一次。我们毕业后首次聚会就是在武汉,我们展开横幅在黄鹤楼前的留影情景历历在目。于是,我们开始在圈中讨论今年聚会的时间和地点。
就着街灯微黄温暖的夜色,我带着微笑走回通往社区的门。已临近规定的关门时间。年轻的门卫上前来,举起测温仪就要朝脑门一“枪”,我说,测手腕吧。测温仪移下来,开了一“枪”。我问,多少度?回应,34。我说,这么低啊。回答,都快半夜了,凉啦。小伙子又问,有通行证吗?有。手神气地一挥,去吧。
我回到了家,中止了多情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