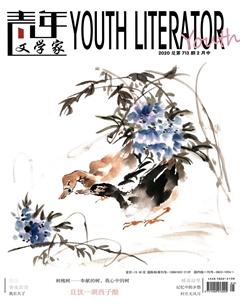由盂蘭盆節發微
马翔宇
摘 要:盂蘭盆節即中元節,來源於佛教觀念。傳入中國後,此概念之宗教意義與文學意義皆有嬗變。本文意在考察盂蘭盆節的文獻出處、由經文散發出的孝親觀念以及該觀念的本土化。
關鍵詞:盂蘭盆節;《佛說盂蘭盆所說經》;孝親觀念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5--02
一、盂蘭盆節的來歷
七月十五是中國民間流行的鬼節之一。它可被稱作中元節,亦可被稱為盂蘭盆節。“盂蘭盆”,是梵語“ullambana”的音譯,即“救倒懸。”盂蘭盆節是佛教徒依據《佛說盂蘭盆經》中內容設立的追思、超度祖先的節日。《佛說盂蘭盆經》最早於西晉傳入中國,由月氏三藏竺法護譯。而盂蘭盆齋當始於梁武帝時。《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載“(大同)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這當為最早關於盂蘭盆會的記載,但民間節日風俗何時真正興起,或晚於大同四年(538年))除施齋外,民間還有誦經、放燈、放焰口等多樣的宗教活動。
而這樣的內容毫無疑問也是屬於宗教文學研究範疇的。所谓“宗教文学”,就是“两栖于宗教与文学的作品群”,蕴含了以上段落所述的宗教与文学间模糊却又密切的关系。宗教和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两者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开始研究宗教时,下意识地会从自己熟知的或信仰的宗教中取出一些概念,引为对应的特征。我们在对宗教起源进行思考时,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宗教为何存在”。有一种答案应该是——宗教满足了人类不断创造更有利于表达自我的艺术形式的需求。宗教刺激了文学。佛教专注的问题一开始并不具备哲学倾向*(箭喻经),它把视野投放在关于存在的实际问题上——如何减少身心的苦?如何增长身心的平和?佛教所关心的问题、佛陀所经历的实修、佛教教义所提倡的体验,促使了佛教文学现实本质和普世价值的产生。这在小乘经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文学同时又影响着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为了传播教义和渲染情绪,佛陀说法时就采用了相当丰富的文学手段,比如譬喻和夸饰。这些口头文学中的方法,连同后出文本中包含的叙事手法、时空观念、复杂结构、玄想性格等,形成了丰厚的佛教文学传统。除此外,佛教中的觀念仍然會影響中國古典文學內涵的發展。例如本文關注的孝親觀念。孝親觀念古來有之,在佛教傳入後,形式和內容都為之新振。本文意從印度佛G12教觀念出發,考求中國傳統孝親觀念的轉變。
二、由《佛說盂蘭盆經》簡述佛教的孝親觀念
我認為,佛教中孝的觀念是以緣起為基礎的。《雜阿含經》十二卷有云:“此有即彼有,此起故彼起”,二十一卷有云:“若有此則有彼,若無此則無彼,若生此則生彼,若滅此則滅彼。”[1]這樣看,早期佛教經典就已經認識到了事物間不斷變化的聯繫是世界生成的原因,也是關於本質的基本理論。佛教中父母與兒女之間的聯繫,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經存在,在孩子出生後具體展現(即可識的色與想),從子女供養親長後開始轉向,在子女為父母完成贖罪和超度後結束這次輪迴、開啟下次輪迴。這種聯繫是沒有主體的、無常的、自發的。如果非要有一個主體,也只能是法——它主宰了佛教的孝親關係。
竺法護譯本的《佛說盂蘭盆經》短短793字,簡要地講述了大目犍連救母一事,並無太多細節。但我認為它蘊含了中國佛教孝親觀念的精華。無論是在它之後相繼譯出的真經,還是本土創作且流傳甚廣的偉經,它們所說的孝都沒有真正超出《佛說盂蘭盆經》中孝親觀念的範疇。
“大目乾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經文開頭就給出了對“為何要報恩父母”、“如何報恩父母”這兩個核心問題的解答。在因果相連之中,父母的“乳哺”之恩乃是一個因,當引起子女回報這一果。《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敦煌本中有類似的說法:“母子之情天生(性)也,乳哺之恩是自然。”“人間哺乳恩最深”。而在中國本土創作的佛教偉經中,關於“恩”這個因的描述很多,幾乎都涉及生理。《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中講到:“第一怀胎守护恩;第二,临产受苦恩;第三,生子忘忧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回干就湿恩;第六,哺乳养育恩;第七,洗濯不净恩;第八,远行忆念恩;第九,深加体恤恩;第十,究竟怜悯恩。”十恩之中,有七恩都與生理相關。對於懷胎、孕育、臨產、養育等詳細的描述,將孝親關係中的“因”赤裸裸地展現在信徒面前。在《佛說血盆經》中寫道:“不關丈夫之事。只是女人產下血露,汙觸地神。若穢汙衣裳,將去溪河洗濯。流水汙漫,誤諸善男女,取水煎茶供奉諸聖,致令不淨。”更將母親生子流的血視為不淨,視為生產之原罪。雖然這兩部都是偉經,但它們在中國相當流行,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國佛教孝親觀念的真實面貌——它將印度佛教的原始教義誇張化、文學化了,但內核無異。
前文提到過,我認為生養、孝親關係的根源是緣起。它在本質上與陌生眾生之間的關係沒什麼不同,不過是因果而已。佛教不僅不避諱或粉飾父母和子女間的生理關係,甚至還大膽地描繪這種關係。佛教將恩情的重點放在生理上,更容易令文化素質較差的普通信眾理解“因”,從而堅信自身應當回報父母。這與儒孝有相當大的不同。《孝經·開宗明義》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複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其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常用來比喻父母之恩,然而從原文來看,它更多地在講孝的方式,即:不損傷“身體髮膚”是孝的開始。而“為什麼孝”,應當關注“夫孝,德之本也。”這一句話;結合《孝經·三才》所說“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可以看出儒家把孝看作本(仁義之本與道德之本)。它是天經地義、無法解除的東西。孝之緣由,不是父母恩情,亦不是父母子女之間的社會契約關係,而是內在的、無法抑制的盡孝衝動。對比佛孝與儒孝,它們在對“為何孝”這個問題的回答上有巨大的差異。後面還會提到兩者在“如何孝”上的差異。
接下來《佛說盂蘭盆經》中講到:“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神、地神、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在此經中,只說到乾連之母罪業深重,生餓鬼道中,但並未提及具體原因。而在《大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中有言:“生存在日,不修善業,廣造諸罪,命終之後,便入地獄。”亦有其母自白:“阿嬢生時不修福,十惡之愆皆具足。當時不用我兒言,受此阿鼻大地獄。”關於如何行孝有言:“汝向家中懃祭祀,只得鄉閭孝順名。縱向墳中澆瀝酒,不如抄寫一行經。”將經文與變文結合來看,孝親觀念在盂蘭盆信仰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結構。由主體看,它由三部分組成——父母、子女、佛;由本質看,它也由三部分組成——罪、贖、佛。佛在這兩個並行的排列組合中,都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在盂蘭盆故事中,母親因生前不修善信佛、“欺誑凡聖”,積累深厚罪業,死後墮入地獄;兒子投佛出家,證得阿羅漢果位,以對佛至誠、對母至孝之心,得方便來贖母之罪;佛法在最高處主宰因果,運行不紊。本土原生的鬼節一般通過建立人間與冥間的關係,來獲得兩端重新交流的機會。盂蘭盆節則是改變原生聯繫,將二元結構轉化為三元結構,核心由父母和子女這樣“無我”、“無常”的兩端變為了佛法這個相對“有”的實在。這就是佛教基本義理在孝親觀念中的體現。
而盂蘭盆經所蘊含的三元結構,也大量存在於流行中國的漢譯佛經之中。《佛說孝子經》中,佛問諸沙門:“親之生子,懷之十月,身為重病。臨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難言。既生之後推燥臥濕,精誠之至血化為乳,摩拭澡浴,衣食教詔,禮賂師友,奉貢君長;子顏和悅親亦欣豫,子設慘慼親心焦枯,出門愛念入則存之,心懷惕惕懼其不善。親恩若此,何以報之?”而佛的回答是:“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為孝養猶為不孝。”此經和《盂蘭盆經》的邏輯結構一樣,開頭先仔細描繪了父母之恩情,給予子女報恩奉孝充足的理由。其回答“雖為孝養猶為不孝”則是徹底地、清楚地解釋了佛教孝親的三元結構。父母生前不依佛法而不勸,乃是不孝;父母死後不以佛法超度其靈魂,乃是不孝;父母生前死後自身不篤佛法,乃是不孝。為孝之法緊緊地包圍著佛這個核心,無他耳。《佛說父母恩難報經》曰:“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隱處;無戒,與戒教授,獲安隱處;不聞,使聞教授,獲安隱處;慳貪,教令好施,勸樂教授,獲安隱處;無智慧,教令黠慧,勸樂教授,獲安隱處。”其理同上,只是將勸父母信佛揚善的方式更加具體化了。《地藏菩薩本願經·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中,悅帝利罪女邪見,譏毀三寶,死後墮入地獄;因其婆羅門女(後為地藏菩薩摩訶薩)宿福深厚,篤信佛法,鬼王無毒令其母生仞利天,得小解脫。婆羅門女倒是因此再度立弘誓願,但終其經不見悅帝利罪女悔過。我對此深有疑惑。依照佛法之精嚴,此罪女應當是真心發願悔過的,否則不可能僅憑其女之功德而出地獄、入仞利天。經中對罪女的自我反省隻字不提,過於強調依佛法盡孝;而本文中所引他經,也對悔過之事一筆帶過,不加詳述。三元結構中子女是相對主動的,而有罪之父母是絕對被動的——理論上應當平衡和動態的孝親關係,在佛經中其實是殘疾的。父母在負擔起生養角色時,他們就已經背上了“原罪”;父母受苦受難時別無他法,只能等待所謂“孝子”的出現。因此我認為,無論是佛教的孝親觀念還是傳統儒家的孝道,都不能說是完美的——前者依佛而立,卻不能在孝親關係中達到佛法所宣揚的平等和動態;後者依心而立,卻缺乏必要的盡孝方法論的指導。“愚孝”就是一種偏離原始孝義的盡孝方式。
注釋:
[1]《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一冊,562頁,經號26.
參考文獻:
[1]買小英:《論敦煌佛教家庭倫理中的行孝方式》,《敦煌研究》2015年第3期.
[2]劉昱均:《儒、佛孝親觀理論依據之比較》,《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15年9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