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存真、严谨、至诚的老一辈教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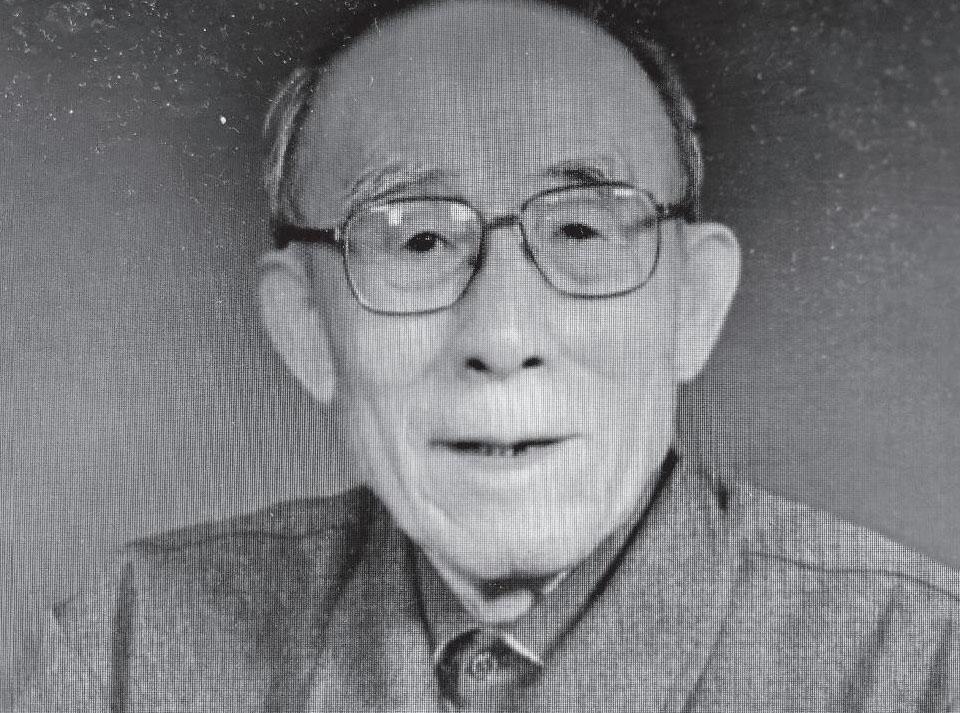
黄济先生是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2006年,“西部阳光行动”农村教育支教项目请先生担任专家顾问,我因参与了此项目,有机会与先生相识。此后,无论在生活、学业,还是在精神上,先生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鼓励和教诲。纯真的家国情怀、严谨的治学精神、教书育人的师者风范,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写下此文,以表追忆,以为纪念。
一、至纯至真的爱国情怀
先生爱国,爱得朴素执着。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又伴随新中国一路成长的人,先生的爱国情怀渗透在血液之中,体现在生活之中。
有一次我去先生家,谈话中他突然问我:“晓燕,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拿出手机快速翻看日历—3月18日,我便调动所有的脑细胞进行搜索,仍是一筹莫展。他看着我的表情,大概知道我很为难,便说:“今天是刘和珍君牺牲的日子。”随即讲了北京师范大学爱国进步学生被害的往事。又讲到了1946年自己随华北大学二部迁往铁狮子坟(北京师范大学校址)的第一天,时任副校长范文澜的演讲,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模仿范校长的口吻,颇有激情地讲道:“同学们,听听这头铁狮子说些什么?段祺瑞曾在这里(铁狮子坟)设府,日本司令部曾在这里扎营,刘和珍烈士的血也曾流在这里。今天,我们迁校至此,就让这头铁狮子告诉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谁从这里倒下去,谁又从这里站起来?”他动情地演讲着,像一个战士在诉说革命的故事,那激情澎湃的样子,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感动不已。还有一次,他讲到蒙养教材时,从书架上拿出《百家姓》和《千字文》,书有些陈旧,我刚翻开第一页就看见他标注的文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精神万古流芳。”在这两行字下面,特意用小号字体写着:“今天是刘和珍君牺牲的日子。”最下面的落款是:“1997年3月18日,购于北师大书店。”那小小的一串泛黄的字迹,将3月18日这个日子鲜明地衬托出来。
先生关心时政,坚持每天阅读报纸,观看《新闻联播》,虽离休在家,但对国家的大事小情仍极为关心。2014年3月28日,我去他家里讨论《美和美育》一文的写作。在谈到美具有情感性特征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沉默片刻后对我讲:“不管什么时候,人都是最有情感的动物。我今天看到一则报道,就特别地动感情,也特别伤感。”说完,他走进书房,拿出当日的《北京晚报》,指着一则头版图片新闻对我讲,“这是今天报道的韩国政府归还我国437具抗美援朝的烈士遗骸的新闻。看到这篇报道我很难过,437人,为什么只有15位家属去领取遗骸?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主要的一点是,这些烈士牺牲于60年前,当时,他们很多人还尚未成家,没有后代,就这样无名无姓地战死在了异国他乡。这是让人想到最难受的。”接着,先生又讲起了自己青少年时期上流亡学校时,校长张敏之及2,000余名学生在流亡途中,惨遭国民党杀害。他沉痛地讲道:“我们的学生爱戴校长,为保护校长,许多的学生也被杀害。其中就有100多名女学生,站出来为校长喊冤,无辜地死在了国民党的枪下。想起这些人,我就觉得感伤。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无名英雄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一定要珍惜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生命,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
2008年汶川地震,他时刻守候在电视机边,关注灾区的情况,并奋笔写下《为汶川大地震而写》:
地会震裂,但天不会塌方;人被震死伤亡,但壮志不会挫伤。人在自然灾害面前,似乎不堪一击;但人在抵抗自然灾难时,又是无比刚强。中国曾经历过无数灾难,但最终还是屹立东方。我们为死者哀悼,为生者祝愿,重建家园。今天灾区是一片瓦砾,明日将是新的铁壁铜墙。永远压不倒的人民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人民团结、众志成城,国旗高扬!
先生爱国,爱得深沉。正如他在其《口述史》中所讲的:“个人生活、民族存亡,都摆在我的面前,逼迫着我去思考和选择,去寻找一条‘别样的路来。就我个人来说,是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跋涉出来,走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来,获得了新生。我所走过的求索之路,实属不易,但我终于走出来了,找到了共产党,走向光明大道,我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
我最佩服先生的超凡记忆力。许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相识或有过一面之交的人,甚至某个曾经看到过的东西,只要你提供相关信息,他都能清楚地说出来。偶尔记不起来,他就会使劲儿地皱眉头想,直到从脑海里把它找出来。这让人不得不惊叹:他的大脑一定是张蜘蛛网,能粘住所有知识的小昆虫。但交往多一点后会发现,其实他也不是过目不忘的神人,只是事事比别人更用心罢了。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提到。他与同学们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时讲道:“我个人并无什么大的才能,一辈子就是喜欢思考点问题,因为我相信勤能补拙,遇到疑难,总要锲而不舍地寻个究竟,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与先生交往中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指导我撰写《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兼评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一文(以下简称《历史经验》)。在探讨系统知识的地位与学生的主体性学习的内容时,他反复强调人的内动力和自求力在学习知识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系统知识的学习需要教师的指导,但更要依靠学生自己付出劳动和努力。在教育改革中,要引导学生在刻苦学习中,由“知学”到“好学”,再到“乐学”,鼓励学生养成自求自得与独立思考的习惯。”撰稿期间,为了让我更好地理解这部分内容的核心要旨,他讲了自己少年时求学的一段经历。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日数学老师给他们出了一道计算题,题目如下:
有卵一篮,朝食全篮之半及半卵,午食朝余之半及半卵,晚食午余之半及半卵,而卵适尽,求篮中盛卵几何?
先生边讲述往事,边在一张纸上将这道题在一张草纸上写出来。我听得目瞪口呆,究竟是什么神力,竟能让一位90岁高龄的人将近80年前的一道题目记得如此真切?写完题目后,他又用现代白话给我重新解释一遍,说当年自己由私塾转入洋学堂,对数学几乎是一无所知。为了这样一道计算题,他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晚间睡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整夜都不能入睡,各种推算在脑海里反复出现,辗转反侧直到第二天凌晨,他突然豁然开朗,用逆推法获得了解题的思路,并且成功算出了答案。先生边说着又把当年的解题思路对我重讲一遍,随着他的讲解与语调,透过时光的河流,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旧时少年,在苦学中获得知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快乐情境。
《历史经验》一文见刊后,先生又指导我构思《美和美育》一文,有一次,我们在谈到1958年中国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问题时,他忽然想起了当时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除了朱光潜还有另外一位学者,但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先生皱着眉使劲儿想,用手拍着脑门,还是想不起来。本来我想回家后在网上搜一搜,然后尽快打电话告诉他,可竟因杂事忘记了。又隔几日,我去他家。他一见面就高兴地说:“晓燕,那位学者的名字后来我找到了,叫‘宗白华。你那天走后我一直想,记起来有‘白华两个字,可是姓记不清了,脑子里一直响着好像叫‘朱白华,觉得不对,但好像很接近了,又继续想,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查出来是‘宗白华。”我怔怔地听着,看着他那可爱又几近较真儿的模样,顿时自责起来,先生不会使用网络检索,不知百度,更无朋友圈,只能凭手头仅有的一些书籍和脑海里的记忆,一步步思索,一条条查找,才得以找到。先生的这份认真和“较真儿”让我汗颜。
先生强调治学要有所“止”,这是他反复强调的观点。有一次,他讲《中庸》,突然停下来,说“止”就是目标,也就是说治学要有目标,更要有向着目标的积累、忍耐与等待。先生私下经常感慨,自己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都“被运动”了,直到60岁,才开始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到了90岁,又一个30年过去了,他还是在乐此不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研究。他对年轻的博士生们说:“我是有目标的,我认定的东西,一般不会动摇,因为我相信自己设定的目标。”讲这些话的时候是2011年冬天,90岁高龄的先生坐在英东楼的一间教室里,与我们娓娓道来,他说:“假如老天还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还要按照我设定的目标走下去,我是有目标的。”当时,他也正在为《国学十讲》系列书稿的撰写每日伏案疾书,对选读的每部经典都进行重新注释、翻译和点评,目的就是立足现实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这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要“发掘和整理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学有所止”。
先生治学严谨,甚至表现在对每一个字的态度里。先生一生钟爱《红楼梦》,同情曹雪芹及他笔下的贾宝玉。2014年是曹公逝世250周年,他专门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红楼梦>随笔—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请我帮他在电脑上输入后打印出来。文章写得很长,加之引用有原著中許多不常用的字,尽管我录入得很细心,自己也校对了一遍,但他还是逐字逐句地看,将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之处打电话告知我。我修改完打印出来交给他,他又仔细审阅,看出疏漏处后再电话告知我。我再次修改完交给他,心想这次肯定是没问题了,谁知电话铃又响了……后来一次到他家,谈话间他对我说自己平时也总是混淆许多字,写错字别字,闹出很多笑话,说着他进屋抱出《辞海》《辞源》,和一本小小的几乎要被翻烂的《新华字典》,告诉我自己平时如何查字典,教我如何辨认一些常见的混淆字。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我的粗心马虎,只是在翻阅这些工具书的同时,耐心地为我讲解中国字的部首、结构以及某些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让我认识到写对字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少出错。
先生在谈治学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别人常常是自以为是,我则常以自以为非自勉。”在指导我撰写《历史经验》一文时,论及杜威学说及国外其他一些重要观点时,他感慨自己做研究、写文章一直以来有两点遗憾和不足:一是外文不好,不能熟读外文教育原著,进行深刻的比较研究;二是实践不够,参与教育教学实践机会太少,对很多问题认识把握不清。因此,在讨论写作时,他总会谦虚地说:“晓燕,你出过国,懂外文,这部分的内容你多做些思考和研究。”《历史经验》一文历时多半年终于完稿,投给《教育研究》后,我打电话告诉先生,他说:“试试吧,文章不一定会刊发,但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文章刊发后,拿到样刊的他认真阅读并进行勘误,还多次提醒我,关于文章的观点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有争鸣是好事。
三、至平至淡的人师风范
先生身上永远带着一种风范,润物无声,为人师表。生活中的他更是温软真诚,让人如沐春风。先生对待家里的保姆像是对待自己的家人,他要求保姆与他同坐一桌吃饭,而且碗筷一定要坚持自己洗刷,决不要保姆代劳。我曾问过先生为什么这样,他说这是家里的习惯和传统,周老师(先生的爱人)持家的时候,他们和孩子们都是碗筷各有所属,各自饭后负责洗刷自己的碗筷并归位。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先生把尊重他人和生活自理等习惯“一以贯之”的表现。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自己的衣物,从来不让保姆洗,自己的被子也从来不要保姆整理,有时候买菜、买米、买烤饼等事情也亲力亲为。而且,他总是想办法鼓励保姆要继续学习,并为她们的学习提供一切便利。大张是我们从甘肃老家介绍到先生家里帮忙的,在得知大张出门在外时常挂念老父亲后,先生曾托我们寒假回老家时送给老人家一件棉衣,据说这件衣服是别人送给他的,可是他自己舍不得穿,宁愿送与更需要的人。而他自己,一件灰白色的外套,衣领和口袋处竟都留有自己用针线缝补的痕迹。小吴是另一位曾在先生家做过保姆的四川小姑娘,在先生的鼓励和辅导下,自学成才,通过了成人考试的全部科目,已在北京成家立业,过着幸福的生活。
先生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负责的态度,无关事情的大小,凡是他经手的事情,必是一丝不苟。2007年我因申请博士生联合培养计划项目,冒昧启齿请求先生为我写一封专家推荐信,他答应后便详细向我询问拟申请的国外的学校、导师及专业情况,然后又详细地记下我的个人信息。一封推荐信,几易其稿。最后交给我的定稿,专门用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信纸,写得工工整整,读来就知道费了一番心思,如篇中就使用“尊敬的××阁下”,措辞考究又可爱。先生写一个字就要写得工工整整,甚至用绳子捆一包书也要捆得整整齐齐。有一次,他要整理家里积存的杂志,并说要分好了类送给我,作为学习的文献和资料。他先把散落各处的杂志按名称分类,又将分好类的杂志按年份分摞,之后又将分摞的杂志依照出刊日期排列顺序,方才用细绳捆上,那杂志被捆绑得方方正正,就连细绳的绕法和线头系法都整齐化一,足见先生做每一件事情的用心。
先生极为真诚,浓缩在他待人接物的举手投足之间。每次去拜访先生,在楼下按了门铃,还未上到二楼就已听见他站在门口等候的声音了,让人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每次交谈完要走的时候,先生必要亲自送至门口,好像还有许多未讲完的话,让人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谈天中,先生偶尔也会讲笑话。有一次,讲到孔子的教育思想时,他问道:“孔子的弟子们都最爱吃什么?你知道吗?”见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便说:“最爱吃盐,七十二咸(贤)人嘛!”说完自己便笑起来了。接着又问:“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多少人已婚,多少人未婚,你知道吗?”我又答不上来,他便说:“已婚的30人,未婚的42人。”我說:“这也有人研究啊?”他说:“这个不用研究,是孔子自己说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不就是七十二贤人嘛。”说完自己又笑起来。
先生是个重情重义又生性浪漫的人,这是从他对待周老师的神情中感受到的。周老师因身体原因,长年卧病在床,听不见,说不出,也动不了,唯有右手可以做几个简单动作,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先生每次走到她的床边,必要用超大的音量与她对话,他们深情对望又无言的眼神,让我极为感动,世间最美好的爱情誓言也抵不过他们之间这份相濡以沫的守候与守护。2014年是周老师90岁寿辰,先生为实现她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替她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几经辗转,周老师入党的愿望终得以实现,先生还撰写《周密小传》一书,作为送给周老师90岁的生日礼物,并自费印刷装订成册,赠与友人学生作为纪念。先生送我这本书的时候,正逢我和爱人一同去他家里看望他,他递给我们书时笑称:“希望我们的爱情能给你们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先生经常告诫我,做人要和风细雨,哪怕发生再大的事情,特别是给别人提意见,也要充满温情。他也经常说,人要坚强,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泄气,甚至干出蠢事。先生常以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告诫我们,人只要有正气,有骨气,最终是会得到自己应有的结果的。先生还多次说:“人,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有点才华的年轻人,一定要防止骄傲。人,不应该有太多‘为天下先的傲气,但要有‘为人先的志向。”
2014年12月3日,先生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我去医院看望他,当时的他意识已经不再清晰,模糊中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口中却依然不断地喃喃自语着关于国学书稿的写作问题。看着先生躺在病床上被疼痛折磨着,我泪如雨下,但也深刻感受到,先生的生命始终与学术同在、与教育同在。在生命的尽头,他仍把学术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以上是我对先生的追忆。
【王晓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