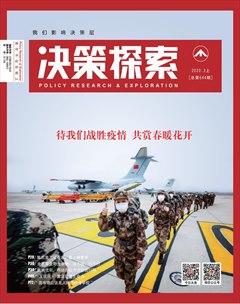砖雕门楼里的家风故事
陆士虎


清晨,旭日再一次镀亮江南古镇南浔。
頔塘(古运河)水宛如一道柔软的绿绸环抱着古镇,江南名园小莲庄荷花迎着朝霞绽放,嘉业堂藏书楼里的古籍默默不语。霞光中,轻纱般的雾帐,给南浔抹上了一片水晶晶的秋色。
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浔古老的石板路上,串街走巷,寻根溯源,仿佛回到那发黄的方志所记载的峥嵘岁月。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聪慧的南浔人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滩,与洋人做生意,涌现了一批巨富大贾,俗称“四象八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名门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当我跨入一座座名门宅第,抬头凝视着一座座砖雕门楼,仿佛与那些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先贤会晤,聆听他们叙说百年沧桑的家风故事。
建筑雕刻可分为木雕、砖雕、石雕等,木头与石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两种材料,人们对它有一种亲切感;陶砖虽是人造物,但它是水、土和火的结晶,是人类最早的发明之一。用这些材料进行雕刻,其本身就是通过艺术注入生命,带着人的情感。江南建筑如此,南浔也不例外。
南浔的宅第大多是多进式建筑,每一进都由砖墙隔离,每道砖墙都有墙门。墙门主要以砖、木、石为材料,平常人家一般采用木头作门框,大户人家则用石头作门框,故称为石库墙门。石库墙门内外一般都有砖雕装饰,也有的只在门内或门外一面,俗称砖雕门楼。
这些砖雕门楼上都刻有寓意深远、造型生动、工艺精湛的图案,且有醒目题词。这些题词,往往寄托了主人的思想理念、人生追求、治家宗旨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主人的家训或家风。如民国元老张静江故居的“世守西铭”“有容乃大”,近代儒商名士张石铭旧居的“世德作求”“蓝田毓秀”,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莱臣的“世泽遗安”“厚德载福”,民国北派画坛领军人物金家的“永建乃家”“心地芝兰”,上海新世界主人邱家的“唯适之安”等,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主人对家庭和后代的企盼、祝愿及训导、警示。
这些门楼上的题词,有的来源于古代典故,有的是名人格言警句,有的是主人治家报国的座右铭,言简意深,内涵丰厚。
经历上百年的风雨,南浔不少门楼已经破损,甚至消失(有的门楼正在修复),仅仅是铭刻在历史记忆中了。所幸这些人家的家训家规家风还在,他们的后代子孙传承和弘扬好家风的精神还在。
刘家孙子满月不摆酒
刘镛白手起家,凭着勤劳和智慧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富。按一般人的想象,这日子不知道该如何穿金戴银、花天酒地了。恰恰相反,刘镛对世道、对自己始终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刘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积德而来的,自己没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时生活很节俭,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吃饭时要吃完碗里最后一粒米的习惯。如果碗外粘了一粒米,一定要用手拈来放进嘴里,并且要求家人也这么做。他虽然很节俭,但却花费巨资为祖宗建家庙、为家族办义庄、为子孙办私塾,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豪宅。
刘镛有着强烈的“惜福”“辟邪”观念,时时以当年的艰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训自励,不愿过多地享受,而宁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赈灾,多次获得朝廷及地方的嘉奖。
他曾对儿子说:“天之予人福泽至不齐也,有以钟爱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谨身节用,则一勺之福亦可以久延;纵欲妄为,虽盈钟之福,一覆而立尽。世之暴殄者多夭,撙节者多寿。以吾所见,历历不爽……岂得谓天道无知乎?吾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区区者不足以倾吾家,诚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纵欲也。吾少也贫,亲历艰难,故事事不敢逾份。汝曹生时境已丰裕,夫岂知祖父艰难积累而始有今日耶?”据《先考通奉府君年谱》记载,他常常告诫儿孙勿忘昔日之艰辛,勿忘祖先的恩德,要小心处世,凡事不可過分。
刘镛的第一个孙子刘承干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长孙视为掌上明珠,准备满月时大大庆祝一番。刘镛却出乎意料地说:“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众人哗然,但又不好直说。
闻此消息,长子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赶来劝说刘镛。
刘镛摇摇头,长叹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上看到财富的诱惑,尝试着去挣一点钱,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为子孙造福,我不愿铺张浪费,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辈们不要太奢华……”
有了孙子刘承干后,刘镛的募捐义举更大方了,捐资赈灾不计其数。但他对自己仍十分节俭,患有胃病,却不诊治,直到晚年时才在家人的劝告下服些补品。
张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浔“四象”之张氏一门,走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一位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市场和书斋,最终成为传统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
张石铭(1871—1928年),名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他和张静江都是张颂贤(字竹斋)的孙子。其父张宝庆(字质甫)是张颂贤的长子,张石铭是张宝庆的独子,故为张颂贤的长子长孙。可惜他父亲体弱多病,“年未三十,因得怔忡之疾,逐到沉绵不能治,卒年四十三”(缪荃孙《张封公家传》)。那时张石铭才16岁,南恒和的大小家事仍由母亲桂太夫人掌握。1903年分家时,32岁的他独自继承了大房的全部遗产,身价上千万,这就使他收藏书画、建造园林大宅和兴办工商实体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张石铭旧居正厅上悬挂着清末状元张謇所书“懿德堂”匾额。“懿德堂”的由来,说的是张石铭对母亲十分孝敬,遵循古训“女子多德曰懿”,故而得名。还有一副抱柱联“罗浮括仓神仙所宅,图书金石作述之林”,是清末宣统皇帝的老师郑孝胥所书,上联是说张氏旧居的建筑很豪华、精致,像神仙住的地方一样;下联赞许张氏的人生爱好,金石、碑刻、藏书无所不能。花厅正上方悬挂着“以适其志”匾额(现为仿制品),为康有为所书,出自张翰(字季鹰,江苏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齐王执政时任大司马)“人生贵得适志”之意。其时皇叔争权,祸难不断,史称“八王之乱”。张翰预见齐王将败,推托思莼羹,鲈鱼烩,即回故土。不久,齐王被杀。
父亲的遗言,从此铭刻在顾乾麟心上,成为他人生的坐标。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断学业,进入顾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为了更好地子承父业,在经营企业方面缺乏经验的他决定从基层做起,从粗活干起,名义上是“见习经理”,实际上只是一名练习生,月薪仅20元。每日过磅棉花、废丝、牛皮和羊皮,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和经理等职。经过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业终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为怡和公司总经理的顾乾麟看到,日军的侵华战争使上海物价飞涨,不少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升学,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厂只想招5名实习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请书。这些求职者,大多数是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其中有许多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想到自己当年有过同样的失学之痛苦,再联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嘱咐,顾乾麟决定遵循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以父亲的名字在上海创立了“叔蘋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贫困学子。
“叔蘋奖学金”除资助贫困学生全部学费和书杂费外,对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还资助膳宿费。此外,得奖学生还可在指定诊所享受免费医疗,在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校外活动中心借阅图书,做物理、化学实验,学习打字、速记、护理、缝纫等技能,以及组织文化娱乐、体育、参观游览活动等,使他们获得了在当时学校教育中得不到的、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中学毕业升入大学、大学毕业出国深造的优秀得奖学生,可繼续获得奖学金和资助。从1939年至1949年十年间,“叔蘋奖学金”共举办二十期,资助贫苦学生达1100多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某些历史原因,奖学金被迫中断。到1986年,顾老先生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在上海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叔蘋奖学金”,继而又将奖学金扩展到北京和南浔等地,形成从中学、师范、大专院校到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奖学金系列化。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着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事业继承人”的遗嘱,指定次子顾家麒(浙江省政协委员、著名外科医生)作为继承人。1995年,顾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币1000万元作为增补奖学基金之用。目前,“叔蘋奖学金”已成为我国私人创办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奖学金。
顾乾麟并不是顶级富豪,在上海他只是略有资产,在香港更只能算小富而已,却倾心尽力践行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捐资助学,令人钦佩敬仰。为此,顾乾麟本人过着简朴的生活,自己和家庭开支甚为节俭。曾在香港为顾乾麟夫妇保健治疗的董元吉(“叔蘋奖学金”第8期得奖同学)回忆过这样的细节:顾乾麟先生平时在家用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极普通的家常菜,两荤两素一汤,到香港后60余年一如既往。1986年,董元吉发现他的一套深绿色西装裤腿前面有个黄豆大的破洞,提醒他不要穿了,顾先生回答说:“我已经70多岁了,还买啥新西装,马马虎虎,省省算了。”
我坐在大桥下的小亭里,小船的橹桨声把我从历史的记忆里拉回。眼前的古镇南浔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让我回到童年,只是常给我讲“四象八牛”传奇故事的老母亲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南浔的老家风依然清晰可见,那些传承和弘扬家训家风的精神仍绵延不绝。今天,我们重拾这份传统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整理家训家规家风的宝贵遗存,充分激发“最美家庭”的乘数效应,无疑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