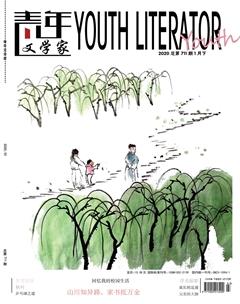迪士尼动画中灰姑娘的“理想自我”
摘 要:《灰姑娘》作为世界童话的代表,和电影有着不解之缘,早在电影诞生后没多久,这个故事就被梅里爱搬上了荧屏,从此对《灰姑娘》的改编就从未中止。特别是迪士尼在1950年推出的《仙履奇缘》成为了影史经典。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对灰姑娘这个形象的构建,特别是通过对其“理想自我”的分析,来达到探究其获得长久生命力内在原因的目的。
关键词:《灰姑娘》;迪士尼动画;《仙履奇缘》;精神分析
作者简介:王晓汗(1994-),男,山东济宁人,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精神分析电影理论。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3--04
1.<仙履奇缘>(1950)的前身
如果说什么类型的童话故事在世界上流传范围最广,那么这个桂冠一定非“灰姑娘型”童话故事莫属。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斯蒂 ·汤普森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写到:“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故事了。”灰姑娘的身影遍布全球,其异文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但是对于这个故事类型究竟有多少异文存在,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这些版本中的灰姑娘的名字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她被人叫做“叶限”,意大利人称呼他为“披着猫皮的辛德瑞拉”,在格林兄弟那里,她被称为“灰姑娘”(Aschen—puttel)。这个类型的故事,生命力至少长达12个世纪,成为了不少人们都耳熟能详的经典。
虽然,灰姑娘在不同的版本中拥有不同的名字。但是此类型的故事包含着共同的叙事元素:女主人公善良而且不幸,她的母亲早已离世,继母和其姐妹对其进行各种刁难,通常都会有神奇的力量对女主人公进行帮助,故事内有一件用于识别女主人公身份的事物(一般是鞋子),此类叙事要素是“灰姑娘型”童话的核心标志。虽然“灰姑娘型”故事在世界各地都广为流传,但是流传范围最为广泛的要数德国格林兄弟版本的《灰姑娘》以及法国佩罗笔下的《灰姑娘》。特别是佩罗版本的《灰姑娘》中出现的仙女,南瓜马车和水晶鞋等象征元素,为后世的影像化改编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灵感。格林兄弟在后面对《灰姑娘》这个故事的继承当中,为了更加贴合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背景,而且也为了对抗法国文化的侵染,并没有把这些元素收录进去。特别是仙女这一富有想象力的角色被换成了树。不过树这一叙事元素,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更加符合对母亲的隐喻,只是缺少了浪漫情怀。
在近百年之后,迪士尼影业将佩罗这篇极具浪漫主义元素的《灰姑娘》搬上了荧幕,从此灰姑娘成为了世界影史里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她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使得人们一直从未间断过对她的改编与创造。而每当人们说起灰姑娘,仙女,马车和水晶鞋就会自动浮现在眼前。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迪士尼对《灰姑娘》这个故事的发扬光大。
2.<仙履奇缘>(1950)的分析方法
电影理论在经典电影理论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成为了现代电影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这并不是一种偶然,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中,导演们已经开始尝试用电影展示人们那难以捉摸的无意识世界。《一条安达鲁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精神分析与电影理论在20世纪之前在各自的领域不断蓬勃发展,最终碰撞出了火花。特别是弗洛伊德学派和拉康学派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无意识理论,梦的解析以及镜像理论等理论观点,成为了分析电影文本的象征关系的重要方法,进而得以找寻人类群体中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拉康的理论研究在不少方面都和电影有着某种同质关系,特别是在对观影机制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拉康的“理想自我”及相关理论的提出,为研究电影文本内部的人物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本文采用拉康对“理想自我”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探讨灰姑娘这一角色获得长久生命力的背后原因。
“理想自我”得以存在的基础是拉康的三界理论。拉康在构建三界理论之前,先对在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容易辨别的三个概念:需要(need) 、要求 (demand) 和欲望 (desire)进行了解释与说明。“需要”是一种可以被满足的生物本能,而“要求”则是用语言表达的需要,哪怕是婴儿也必须通过发出声音来向他者(一般是母亲)表明自己的需要。但是因为他者本身就是存在匮乏的,所以他者的目光不会一直望向怀中的婴儿,因此无法为婴儿提供绝对的,没有确实的爱。拉康说:“欲望既不是对满足的渴望 ,也不是对爱的要求 ,而是来自后者减去前者之后所得的差额,是它们分裂的现象本身。”所以欲望是需要以要求表达时产生的剩余。“在要求与需要撕裂的边缘,欲望就成形了。”需求在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停止对主体的驱动,但是因為欲望永远不可能被满足,而且个体永远在欲望着他者所欲望的,所以欲望的实现不在得到满足的时候,而是在重新产生的时候。因此,欲望的驱动将永远伴随着个体的发展。而需要、要求和欲望分别对应着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即实在界 (the Real)、想象界 (the Imaginary) 和象征界 (the Symbolic)。自我的构建的过程就是在这三界之间,特别是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间不断穿梭的过程。
实在界,相比想象界和象征界来说,对于实在界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实在界也比较难以描述清楚。拉康认为实在界构成欲望的对象,一旦实在界出现破损或者是坍塌,就会影响个体对现实的感知。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存在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语言,然而实在却先于语言,难以琢磨和感知,它像是一个空洞,个体不断尝试着对它进行填补。
想象界,它是一种幻想逻辑,个体在此阶段还处于一种“母我关系”之中,并且通过“镜像阶段”获得对自我的虚假认同,从此走上自我异化之路。主体在此阶段给自己建立了一个虚假的,圆满的,且不具备流动性质的自我形象,而且这种对自我的迷恋不会因为镜像阶段的结束而终止,主体一生都将被这个形象所捕获。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主体的自我构建,就在两界的不断穿梭中得以实现。
象征界,是语言与符号的世界。抽象的父亲角色“以父之名”在这里起着绝对的统治作用,因为“以父之名”是他者中的他者,它不再是弗洛伊德家庭结构中那个真实的父亲的橘色,而是成为了文化,制度,法律等一切秩序的化身。它监视着个体的一举一动,并对个体在想象界中创立起来的完美自我形象提出质疑,要求个体压抑自己的一部分欲望来换取其在象征界的合法注册地位。
而“理想自我”则诞生在想象界中,“镜像阶段”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康这里,一切的起源都来自于“镜像阶段”,“理想自我”同样也是。拉康称:“人的躯体之像是每一种他在对象中感知到的统一性的根源”。镜像是自我的开端,尽管这个自我只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之中。镜像阶段主体对自我镜像的迷恋看似是自恋,但其实这是一种恋他行为。这个诞生于想象像的认同秩序的产物便是理想自我(ideal ego)。它本身是空洞的和不断变化的。这便是拉康对“理想自我”的解释。从镜像阶段开始,人類便会一直努力选找一个理想的形象,并且把这个形象认同为自我,但是这种行为的后果便是无法逃避的幻象和异化。这种认同行为需要一个认同机制,通过认同某个完美的形象而产生自我功能,使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这个形象就是“理想自我”,是主体的“想象的自我”,换句话说,就是“想象的他者”。
人们是如此的喜爱《灰姑娘》这个故事,以至于诞生了一个名为“灰姑娘情结”的专有名词。从叙事层面来讲,这个故事得以成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灰姑娘虽然贫穷,但是却依然嫁给了王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在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得以成功的原因,和灰姑娘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自我”不无关系。下面,本文就以代表性的灰姑娘电影《仙履奇缘》对灰姑娘这个角色的“理想自我”进行分析。
3.对<仙履奇缘>(1950)的分析
影片中灰姑娘与“理想自我”的认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灰姑娘尚且还是婴儿的时候,她往镜子中看时,首先是看到她自己,主体对自我的观看是一种“我看我”的行为,这个动作指向的是主体的理想自我,是一种自恋性认同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镜像阶段”是一种隐喻,并不是单纯的照镜子的行文。身体的破碎也是指个体刚诞生时身体和心理等的混沌状态。主体对镜像的认同实则是对理想自我的认同,是一种与“想象的他者”进行自恋认同的行为。灰姑娘此时虽然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镜中的镜像给了她一种自我完整的错觉,她认出了镜中的那个自己,由此产生了“我”的观念,伴随着自恋的理想自我便产生了。从此,她开启了与镜中自我的想象性的认同行为。
但是这种认同行为远远还没有结束,因为镜像阶段具有层次性,虽然尚在襁褓中的灰姑娘已经通过对镜中完整身体误认产生了自我的概念。但是她还需要一个他者的目光。在之后的阶段,灰姑娘的监护人也出现在了镜中,灰姑娘在镜中通过父母的目光对自己的镜像进行再次的确认,通过父母微笑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话语,比如“看,那个是你”之类的能指语言网络。让灰姑娘对自己的虚假镜像进行彻底的误认,理想自我的幻象与现实身体的差异最终使得主体避免不了异化的悲剧。灰姑娘对“小他者”的误认使得自我认同与自我构建具有欺骗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主体对“理想自我”的自恋情结。
母亲的早早去世,在让灰姑娘可以独享父亲之爱的同时,也势必会带来一些困扰。因为在理想自我建立之前,一个绕不开的阶段便是“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虽然也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并且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拉康并没有弃用这个理论,而是在继承其观点的同时,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拉康依托于符号界与想象界的分离,以“石祖(Phallus)”和“父亲的名义(Nom-du-Père)”两个术语重塑了俄狄浦斯情结。首先对他而言,在情结中主导性差异的并非阴茎,而是“石祖”,即支撑阴茎价值的男性符号化象征,就是说,只有在一个父权社会背景之下,阴茎才可能具有一种想象上的价值优先性。母亲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无论是最初的受孕还是后来离开孩子,这都是她认同石祖所代表的符号秩序的结果。因而,母亲也是一个欲望的主体,只有她放弃自身的全能感并承认自身的缺失,她才有可能因自身对“石祖”的欲望来引导孩子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母亲认同了“父亲的名义”,孩子才认同“父亲的名义”。父亲的功能从一开始就在场,其只是“事后”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来出现。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俄狄浦斯情结结构性地贯穿整个心理发展历程。
灰姑娘因为母亲的去世,这种欲望传递的断层,因而无法正确认识想象中的欲望符号“石祖”,因此她无法确认自己的男人理想以及自己欲望着何人的欲望,“小他者”的过早隐退,加上一父一女的结构模式,使得灰姑娘与实在的父亲的关系容易滑向一个危险的方向。这一点,在很多灰姑娘型的故事中都有提及。甚至其中不乏想要娶自己女儿为妻的父亲形象。也有学者在分析格林童话版本的灰姑娘指出,灰姑娘父亲的缺席,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规避和自己亲生女儿乱伦的欲望,因此才把所有的爱意都给了自己的两个继女。但是在动画版灰姑娘中,灰姑娘的父亲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灰姑娘仍然缺乏一个母亲的爱”,所以给灰姑娘找了一个继母,此举虽然有效地杜绝了危险的父女关系,但是显然让灰姑娘陷入了困境之中。
如果说在父亲没有去世,继母没有到来之前,灰姑娘的实在自我和理想自我已经十分靠近,那么在父亲去世以后,灰姑娘的实在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则出现了裂缝。继母这个角色为什么如此讨厌灰姑娘,在社会学的角度上讲答案是显然易见的,因为血缘和特殊的财产继承制度。但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讲,这个答案又有些复杂。继母对灰姑娘的憎恶首先来自灰姑娘的独一无二性,电影的旁白本身也提到了,灰姑娘的父亲决定再娶一位妻子的理由是他认为灰姑娘在拥有了那么多美好的事物以后仍然需要一个母亲的爱,而不是自己爱上了这位女士,从这一点上,继母被娶进门的理由是灰姑娘。灰姑娘的母亲已然去世,继母的攻击性在通过错位的移情后落在了灰姑娘身上。继母和自己的两个女儿在楼上恶狠狠的望着楼下灰姑娘和父亲一起幸福的玩耍的场景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场景就是继母在望向一个自己的理想镜像,在她的认知中,这个场景是属于她的,因为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而不是灰姑娘。自我是一种对自我的意识,产生于他人的承认。那么对人来说最不能忍受的不是他人对自己的恨,而是他人对自己存在的忽视。继母也需要灰姑娘父亲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同时,灰姑娘父女二人的温馨场面,也成了继母反观自身处境的“镜像”,继母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缺失,也激起了她的仇恨体验。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这时的镜像与主体处在一种否定关系中,这一‘镜像所反映的不是一个完美统一的自我,相反,它映衬出自我的另一方面,即‘缺乏‘不在‘空无的前镜像状态,并激起焦虑与仇恨的负面心理体验。”所以,继母对灰姑娘才愈发憎恨。在灰姑娘的父亲去世后,继母再也无法掩藏自己的攻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