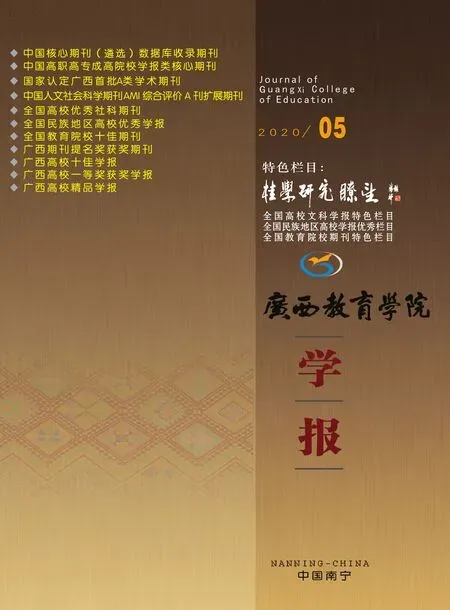自媒体语境下的“锦鲤热”现象研究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刘欣怡,柯高阳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历史上对锦鲤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晋,锦鲤因其 “鲤跃龙门” 的民间传说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吉祥、福气、祥瑞的象征。锦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图腾,更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性力量,其中蕴藏着人们对美好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双重满足的基本期待。考察锦鲤文化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锦鲤一直深受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喜爱,并与中国人所常说的“风水”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锦鲤对于国人一直都是吉祥物一般的存在。然而,在自媒体语境下,人们对锦鲤的日常追捧转换了空间,活动场域逐渐由线下转移到线上,并由于网络社交平台的传播而被赋予了 “转运” 的意味。随着大量 “图片+文字” 形式的符号在网络社交平台内的快速传播,不少商家抓住了商机,开展了许多 “转发锦鲤抽奖” 类的活动,至此,锦鲤的符号意蕴在网络空间内发生了新的异变,这对于个体 “主我” 与 “客我”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融合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锦鲤文化的历史源流考察
远古时期,人类已有了对于 “鱼” 的崇拜,那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图腾崇拜。图腾,即带有某种象征性意义的图案、图像、符号,往往来源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或人们想象出来的非自然的存在。中国的一些民俗研究者认为,“原始人最崇拜的是某种动物、植物或某一自然事物,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最早的祖先和保护者,而自己这个胞族则是从这种‘神物’中孽生出来的。”①徐华龙.中国文学民俗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78在中国中原等地区,常以鱼类或两栖动物作为部落图腾,鱼因多籽而被中国的母系氏族赋予了多子多福之意,那个时期的文物因此多见鱼形图腾,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女性生殖能力、生育能力的敬畏与崇拜。
在《三秦记》 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 “鲤跃龙门” 这一神话传说的记载:“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①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94-95相传,跃过禹门的鲤鱼全都化身成了龙,因而禹门也有了 “龙门” 之称,没有跃过龙门的鲤鱼撞到了周遭的石壁,身上便带有了零星的黑斑,锦鲤的原始性品种周身皆为红色,鲤跃龙门的民间传说着实为锦鲤品种的增加添了几分神话色彩。李白亦曾在其诗作《赠崔侍郎》 中提及了鲤跃龙门的典故:“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诗经》 中的《国风·陈风·衡门》 篇亦写道:“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锦鲤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吉祥、福气的象征,最初只有达官贵人、宫廷贵族才能将其养作池中之物,后来才慢慢走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锦鲤的追捧与喜爱在唐朝达到鼎盛,唐朝诗人如项斯、陈天光、陆龟蒙、黄滔等都曾作诗表达对锦鲤的喜爱之情。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民间习俗、民间信仰赋予了锦鲤多样化的符号意义,鱼同“余”,鲤同 “利”,锦鲤在许多中国人眼中能给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好运与财富,鲤跃龙门则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攀升,人们常通过修建鲤鱼池、在家中摆置鲤鱼样式的挂件等方式以求好运,此为自媒体语境下 “锦鲤热” 现象的历史文化前提。
二、自媒体语境下的“锦鲤”:互动中赋予新的意涵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人们将锦鲤追捧到了一个近乎神圣的高度,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搜索 “锦鲤”,与之相关的关键词多为 “转运”、“水逆退散”、“转发抽奖”、“日常玄学” 等。部分自媒体用户利用人们对锦鲤图腾的追捧与崇拜,通过大量点赞与转发,将锦鲤转运的象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来看,火遍全网的锦鲤实际上也是人与人进行社会互动与交流的一种符号,只不过其发生的场域是在网络虚拟空间内,其表现形式多为图片+文字,并逐步趋向多元化态势发展。“锦鲤” 这一符号的基本含义在自媒体语境下、网络虚拟空间内通过网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正在不断自我更新与变革,在不同情境下也会有不一样的符号意义,正如乔治·赫伯特·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 中所指出的:“当我们运用它来影响其他人,并且通过这种对我们所说的话的理解过程传播关于这种社会情境的信息时,我们也影响了自己。”②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1在自媒体时代,“锦鲤热” 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深层次动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人们在网络空间内的虚拟社交与互动不断赋予 “锦鲤” 符号以新的意涵。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任何一种符号其本身都不具有客观、特定的意义,其意义都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所赋予并不断更新、发展与变化的,当前风靡全网的 “锦鲤” 符号亦是如此。米德指出:“意义——如果说并不总是明确地而是——潜在地存在于它所指涉的社会活动的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中,并且从这种关系之中发展出来。而且它是根据处于人类进化层次上的符号化才开始发展的。”③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2在符号互动论中,符号仅仅是个体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媒介,它可以是文字、语言、图片、声音、表情、手势动作等多种形式,“我们的思维过程总是借助某种符号才发生的……我们的符号都具有普遍性”④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58,其意义是在社会互动过程所形成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若离开了社会互动过程,那么符号本身便不具有特定意义。“锦鲤” 符号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具体到自媒体时代下网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对应许多不同的答案,最为普遍的即为与锦鲤有关的图片与文字,微博搜索锦鲤等关键词,首先出来的即为一个叫 “锦鲤大王” 的账号,该微博账号的每日阅读量保持着一百万以上的稳步增长趋势,并且该账号每天都会定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类似的锦鲤图片,并附上 “本王法力无边,关注并转发者,一周之内或一月之内必有好事发生” 等字样,每条与此类似的微博的转发量都保持在一千万及以上,做出评论与点赞的用户也是人数众多。同时,由于关注人数较多,在 “锦鲤大王” 的微博置顶页面及微信公众号主菜单中还详细介绍了许愿还愿指南,甚至还推出了行善悔过、在线投喂鱼食等新功能。所谓许愿还愿、行善悔过与在线投喂鱼食其实不过是营销者为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谋利披上了一层光鲜的外衣,“锦鲤” 符号对于这类营销号运营者而言只是他们用以敛财的手段和工具,他们了解到人们对于锦鲤的信奉与追捧,了解到 “锦鲤”符号在网络场域内是有市场、有利可图的,网民们的社会心理与 “锦鲤” 符号的历史意蕴给了此类营销号以创造性改变的空间。正是因为关注并参与进虚拟空间中的社会互动人数众多,才赋予了本不具有 “转运” 内涵的图片以神秘的魔力,锦鲤大王一跃成为具有话语权威、有解释权的个体,关注者纷纷效仿转发、点赞、线上充钱等行为。同样在虚拟空间的互动中被赋予 “转运锦鲤” 意涵的还有杨超越,其在一档名为《创造101》的电视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备受争议,从而掀起了不少网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热烈讨论,网民们在交流与互动中认为其有与锦鲤相似的好运体质,才得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随着杨超越祈福图片在网络上的大量流传,“锦鲤” 符号又多了一层象征意味。支付宝 “信小呆” 锦鲤的横空出世,则将 “锦鲤热” 推向了新的高潮。2018 年,支付宝塑造出了网名为 “信小呆” 的锦鲤用户,被丰厚奖金砸中的 “信小呆” 瞬间受到了大家的羡慕与追捧,不少商家瞄准了商机,纷纷效仿,趁势开展起如火如荼的转发抽奖活动以增加曝光度与知名度,中奖者只有几位甚至只有一位,但是转发点赞者数量庞大,商家只需支付较低的成本便换来了低廉甚至免费的宣传。至此,“锦鲤” 这一符号已逐渐脱离其原始图腾崇拜的意味,在 “转运” 意涵的渲染下,在市场经济机制的运作下,在自媒体舆论的烘托下,“锦鲤” 符号逐步变为了一种网络空间内的新型营销手段,其影响力和内涵范围都在不断扩大。
其二,不同的人对于 “锦鲤” 符号有着不同的精神寄托。符号互动论强调符号具有普遍性,是个体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媒介,且只有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才会具有特定的意义,但符号的意蕴不是固定不变的。人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会根据自己对既定符号的理解来选择相应的应对方式,米德提出,“我们必须把心灵看作是在社会过程内部、在社会互动的经验性基质内部不断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有当社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参与这种过程的任何一个既定个体的经验,或者说在这种经验中呈现出来时,心灵才会在这种社会过程中出现。”①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44-145人类因其心灵具有反身性而与低级动物区别开来。当人们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大量转发上述此类 “锦鲤” 符号时,必然会附带自己对该符号的个人理解。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一种宗教信仰给我的印象只是类似于一种关系学说热烈信奉的东西。因此,尽管这是一种信仰,但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评价生活的方式。信仰就是热烈地奉行这种评价。”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M].黄正东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0对“锦鲤” 符号的崇拜已渐渐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将自己较难实现或达成的愿望寄托在一种精神图腾上。自媒体时代人们对锦鲤的疯狂追捧与中国人没有较为统一的信仰有关,中国是非宗教国家,只承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与道教等五种制度化合法宗教,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时刻会面临价值信仰虚无的困境,“锦鲤” 符号的理念转变恰逢其时,迎合了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现实社会生活中无法妥善解决的矛盾与难题有了精神依托。因此,同样的符号,面对主体的不同需求,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含义,同样的锦鲤图片,既可对应求身体健康,也可对应求学业进步、爱情顺利、事业顺利等不同内涵,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主观性与认知性。
其三,网民的跟风刷屏行为正在不断扩大“锦鲤” 符号的传播范围。在 “锦鲤大王” 等微博营销号高转发量的背后是网民们跟风刷屏的行为,同时也体现了自媒体时代人们的盲目从众心理。从行为发生场域来看,人们在网络空间内进行转发 “锦鲤” 符号或者主动发布 “锦鲤” 符号是一种非传统的社会互动过程,在我们的一般性认知里,“群体” 一般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聚集在一起,为了同质化的目的而共同发动某种行动或行为的一群人,而法国心理学家勒庞认为,对于 “群体” 概念的考察与界定应该更注重考察其在意识、心理等主观方面的共同特征,勒庞认为:“即将变成组织化群体中的个体的首要特征,就是个体自觉个性的消失以及思想和情感迈向不同的方向。有了这些特征之后,这些个人即使不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群体’。”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社会心理.[M].张倩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6由此可见,网络空间内此起彼伏地发布与转发与 “锦鲤” 符号相关的内容的网民在社会心理学角度也应被看作是一个 “群体”,只不过其存在场域是在虚拟空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网络社会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社交场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分析“锦鲤” 符号在现代社会网络空间内发生的异变,不仅要考虑其符号的新赋含义,也应注意高频率的转发、点赞现象所折射的深层次原因。勒庞认为,当我们要研究一个群体的行为,就不能只聚焦于单个个体的行为与心理,而更应分析群体的较为明显与普遍的共同特征,“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获得一些虽然短暂、但却十分明确的普适性特征”②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社会心理.[M].张倩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6。而对于群体行为及其心理因素的分析,心理学上早已形成公认的论断:“无意识现象不仅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还存在于智力活动中,而且都起着压倒性的作用。与心理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发挥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③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社会心理.[M].张倩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1在群体性行为中,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实际上更容易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影响与刺激,即其完整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形成,无意识人格怂恿下的群体行为往往欠缺理性思考,米德所说的 “反身性”没能在网络场域的群体性跟风刷屏行为中得到充分实现,米德指出:“除非理性的装备(apparatus) 使自身进入它自己对经验领域的分析,或者说,除非个体使自己进入与——他在任何一种既定的社会情境中的活动都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个体自己进入与——他在任何一种既定的社会情境中的活动都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个体自我的经验领域同样的经验领域,否则,理性的装置就不可能是完善的。”④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49人们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刷屏式转发 “锦鲤”其实也是缺乏理性思考,自我中的无意识因素占上风的表现,以杨超越、“锦鲤大王” 等为内容表征的 “锦鲤” 符号都曾在短时间内登上过网络社交平台的热门搜索榜,这就对网民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告诉他们其他人都在关注此类内容,作为个体自我组成部分的 “客我” 开始发挥作用,此时的 “锦鲤” 符号已经渐渐超出其符号含义的范围,而逐渐具有社会性的特征,“锦鲤” 符号的传播范围便在网民群体的无意识跟风刷屏行为不断扩展着传播的范围。
三、“自我” 发展的实然状况与应然选择
在 “锦鲤热” 现象背后,是 “自我” 发展在信息飞速传播的自媒体时代的彷徨与迷失。在米德的观点中,“自我” 的形成与发展是人作为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根本区别。“自我” 是在人们社会活动、社会交往等社会互动过程所形成的社会经验中产生的,“自我” 更多体现为一个互动与内化的认知性的过程概念,而非实体概念,因此对 “自我” 形成及发展的考察离不开对社会互动过程的充分理解与深入分析。“ 自 我 ” 是 由 “ 主 我 ” 与 “ 客 我 ” 在 互 动 中 共 同构成的,“‘主我’是某种对于处于个体经验内部的社会情境作出反应的东西。它就是个体对其他人——在他针对他们采取某种态度时——对他采取的态度所作出的回答。”①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92而 “客我”即 “社会我”,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受到他人态度影响所采取的相似的某种态度,“自我” 中的 “客我” 包含了社会或他人对 “我”的态度的期待,“自我” 中的 “主我” 不是既定不变的,而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我们往往更能看见“客我” 作用的发挥。
米德指出:“原始的崇拜形式只不过是对既定社会群体或者共同体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社会体系——是这个社会群体或者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所采用的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手段,用来形成与这种环境的各种社会关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 与它进行对话;通过这种方式,这种环境对于这个既定社会群体或者共同体的每一个个体成员来说,就变成了整个一般化的他人的组成部分。”②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霍杜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68在自媒体语境下人们对 “锦鲤” 符号的追捧与崇拜也是如此,在个体的 “客我” 作用下,网民们纷纷效仿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与转发 “锦鲤” 符号的行为,既是出于盲目从众的社会心理,亦是出于能够转运、祈福的希冀与特殊的精神寄托,但实际上无论是“锦鲤大王” 等粉丝众多的微博大V,还是进驻网络社交平台的商家,“锦鲤” 符号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吸引网民注意并将他们控制、组织起来的一种营销手段。勒庞在《乌合之众》 中解释道:“群体的行动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孤立的个体在受到刺激后会结合其他理由进行充分的思考,所以个体采取的行动与群体采取的行动往往是对立的。”③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体时代的社会心理.[M].张倩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7其对群体心理的见解虽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对于自媒体语境下的 “锦鲤热” 现象仍然适用。在自媒体时代,“自我” 发展的实然状况为个体在无意识因素占上风的情形下欠缺了理性思考,这既为自媒体时代的营销号和广大商家提供了盈利机会,亦抑制了个体 “主我” 的发展,“主我”、“客我” 在自媒体语境下的统一融合发展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展望个体 “自我” 在自媒体时代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长期使 “自我” 处于漫步于无意识领地、欠缺理性思考的状态,我们要明白自己既是网民群体这一 “一般化的他人” 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网络场域内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我们也应保持冷静的思考与分析能力,既考虑 “客我” 的态度需求,也给出理性的 “主我” 反应,可以有精神寄托,但减少盲目从众的无意识群体行为,让 “主我” 与 “客我” 无论在线下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线上的虚拟社交中都能形成融汇与贯通,让“自我”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真正统一,这便是 “自我” 在自媒体时代良性健康发展的应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