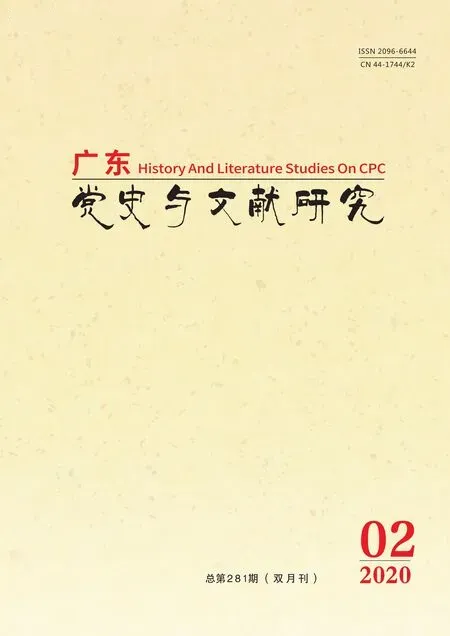中国社会各界纪念列宁话语研究(1924—1927)
郑康奇
1924年1月21日18时50分,列宁逝世。这一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十分活跃,很多组织、团体、个人对列宁的逝世都留下了文字,很多杂志还辟有列宁纪念专刊。
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471 页。关于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少成果,②相关研究见金涛:《十月革命纪念与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苏区研究》2018年第4期;周月峰:《“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刘淋淋:《十月革命与早期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苏区研究》2018年第1期。在当时纪念列宁的文章中也大都描写了十月革命与列宁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作用,可参见秋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中国青年》1924年第3卷第52期,第16~21页;超麟:《十月革命与列宁》,《中国青年》1926年第6卷第14期,第360~367页等。这对研究列宁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以往关于纪念列宁的研究中,胡国胜从“列宁符号”入手,研究中共如何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③胡国胜:《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马建标则通过权力与媒介的关系出发,选择了“一战”时期作为背景,探索列宁主义在早期中国社会的传播及媒介背后的人际关系与权力运作方式。④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228页。近几年“话语”研究较热,以陈金龙为代表的研究者对纪念史学进行探究,并出版了专著。学术论文则以研究中共具体纪念活动为主,中共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纪念,如五一纪念、五四纪念、七一建党纪念、长征纪念、孙中山纪念、毛泽东纪念等,都有学者撰文加以论述。⑤胡国胜:《仪式、记忆与象征: 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评陈金龙新著〈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3期。这些学术成果对“纪念话语”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将研究范围仅局限在中共的纪念活动里,于广度上还稍显不足。笔者拟从1924—1927年中国社会各界纪念列宁的话语表达出发,结合相关的行动和历史背景、派系和人际关系,梳理出这个现象所引发的不同声音,探索列宁的形象建构和塑造,挖掘纪念列宁话语的深层次内涵。
一、话语权的掌握:中共方面对列宁的纪念
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对列宁逝世的反应当然令人瞩目。列宁逝世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打击很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个宣传自身理论、进一步发展自身力量的大好时机。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力量还很弱小,大多数人对中共仍是不太了解,通过对列宁逝世的纪念,可以达到宣传中共理论政策的目的。加之有着相同的革命信仰,纪念列宁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1925年1月21日,中共通过《向导》发布《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文中以较多的篇幅描述列宁革命的背景,最后号召中国的工人、农人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学习和了解“列宁主义”,“我们在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子里,应该高呼着”。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向导》1925年第99期,第1~2页。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苏联与中共合作的时期,苏联的诸多方针政策都被中共采纳借鉴使用,在这其中列宁起到了重要作用。陈独秀在1925发表的《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一文中开头就将列宁与释迦佛类比,“释迦佛说:要普度此世界众生于他的世界;列宁说:要为此世界人类中被压迫者脱离被压迫地位于此世界而奋斗”,陈独秀还指出:“我们若要指证释迦佛所说他世界在何处及超度了多少众生到那里,便未免太滑稽了;而由列宁奋斗所解放之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已经分明在此世界中令我们看见了,如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工人、农民之解放及苏联境内小民族之解放与夫近在远东民族革命运动之勃兴”,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说明了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②独秀:《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1925年1月21日,《向导》第99期。结尾提到“那些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都是中国反动军阀之好友,也就是中国民众之敌人”。③独秀:《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1925年1月21日,《向导》第99期。
同时,中共在列宁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宣言中,将列宁称为“马克思之后最伟大的首领”,明晰了列宁“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一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最终上升到“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④《中共“四大”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1925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09~610页。所表达的比陈独秀更激烈。
两年后,陈独秀在1927年1月21日的《向导》杂志上发表的《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之中国革命运动》一文则指意明显,此时距离四一二政变的时间已很接近,陈独秀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了担忧,他写道:“可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革命的中国,是否也会走到一种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因惧怕工农阶级及其政党的势力渐渐增长,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和国内黑暗势力投机分子和平空气所诱惑,……以回复到不革命的中国,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国。”⑤陈独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1927年第184期,第1~3页。三个月后,陈独秀在文中所担忧的事情就开始一一变为现实。
在纪念话语中,中共高层正是通过宣传逐渐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相对于大革命后较为宽松,故这一时期的社会话语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更加广泛。有学者认为,中共在1927年以前,仍是依靠私人的关系结合形成的政党团体,直到1927年后,中共才在政党管理上走向成熟。⑥Hans J. 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于“个体自由边界”的认知也在这次纪念中得以展现。个体对于社会的认知通过借助社会话语从而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话语的背后包含的是党派在当时的社会整体观念,进而投射到实践中。
二、借机发声:其余各方对列宁逝世的反应
列宁逝世后,纪念文章层出不穷。同一时期,美国前总统威尔逊逝世,但在中国社会的反响却远不如列宁。“一战”前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曾经风靡一时,当时的媒体正竭力将威尔逊塑造成一个拯救中国的伟大的“救世主”,而短短几年过后,威尔逊主义的风光就已不在。①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第211页。有关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专门的研究,研究者常忽略“一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对宣传威尔逊主义的主动性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由。
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中共、国民党、北京政府等与苏联之间都有着微妙的关系。这一时期,苏联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表面上风平浪静,与中共、国民党的私下合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苏联在各方面给予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帮助,故纪念列宁的话语主要是由中共与国民党两种势力构成。列宁逝世后,社会上大多数报刊都以集体的名义发出报道,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且往往仅报道列宁的生平,如“生于瓦尔拉河之布尔斯克”之类。②《列宁的之生平》,《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10期,第79~80页。
列宁是当时的国共合作之间的重要“中间人”。通过分析列宁逝世后国共双方的纪念话语,可以看出他们对列宁与苏联的态度。由于当时正处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大致看来,国共双方多从促进国民革命的角度,对他持正面积极评价。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月20日至30日召开,孙中山得知列宁逝世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在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列宁逝世的演说,大会也因列宁逝世而休会三天。此时正值国民党谋划改组之时,与苏联联系密切,欲借鉴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模式,而列宁自是其瞩目对象。同时,他在纪念演说中阐述自己所理解的中国革命,较多篇幅宣扬自己的革命地位,强调统一和纪律,指出目前国民党发展中的不足,阐释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道路对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表明今后要加强国民党的党员教育。③《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 (1924年1月25日),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一号,《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137页。次日,孙中山在给大会的提案中再次表明国民党需要学习借鉴列宁的事业,提案主要侧重于民生层面,表明要在民治之下,“增进国民之幸福,则其事业正为本大会之精神,本大会特休会三日以志哀悼”。④《哀悼列宁提案》(1924年1月25日),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一号,《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在当时,国民党内部由于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与孙中山的崇高权威,党内还未出现明显地反对纪念列宁的说法,还有人“提议去电莫斯科吊唁列宁”⑤《京众院又开谈话会》,《申报》1924年1月29日,第6版。。国民党的其他元老如廖仲恺在追悼列宁的演说中未提到“共产主义”等相关词语,仅是提到“革命”一词,而其他的国民党人的纪念文章也较为类似,称列宁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革命家”,将未来的中国寄托在青年兵士、学生身上。⑥廖仲恺:《追悼列宁大会演说》 (1924年2月24日),《廖仲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5~156页。由于1924年蒋介石日记的丢失,仅从1925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发现寥寥数语:“赴列宁周年纪念会”,⑦《蒋介石日记》1925年1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抄本。并无对列宁的看法。
北京政府对于列宁逝世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由于苏联强大的实力令北京政府忌惮,同时,北京政府也深知苏联对国共两党的帮助,北京政府对列宁的纪念话语数量并不多。北京地区的多次列宁追悼会都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种种限制,以致未能办成,如“追悼列宁大会,原定三月三十日在中央公园开会”,但因为该会筹备主任熊希龄得到了警察厅的公函,不敢擅自做主,所以也就未能举行。①《京宁两处追悼列宁未成》,《清华周刊》1924年第309期,第43页。但北大等校的纪念活动,却悄悄地进行。②《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第1396期,第3页。相比之下,南方地区对于列宁的纪念则比较普遍。列宁逝世后不久,广州市教育厅就要求各校在第一公园进行悼念列宁的活动,并称其为“吾国国民一大朋友”。③《函教育局接教育厅函在第一公园开会追悼列宁转饬所属各校遵照由》,《广州市市政公报》1924年第118期,第31页。但需要明确的是,北京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报刊中对列宁也并无污蔑性的话语。以《顺天时报》为例,该报在1月25日就刊载了《列宁之逝世与政治之理想》《哀悼列宁》等文章,比较客观理性地介绍了列宁的政治思想。④《顺天时报》 1924年1月25日,第2版。对于北京政府来说,列宁逝世的最大影响在于:一战后,列宁曾说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此时列宁逝世了,条约还能废除吗?
《国闻电报》在1926年的一则报道传递出了一些微妙的信息。这则消息在文章正中心放了一张列宁读报的图片(题名《列宁遗像》),而左右的所有文字均在论述孙中山的思想,用加粗放大的方式突出了几句话:“财产私有权存在,那共产主义是讲不通的”“是要耕者有其田”等,明显地是想通过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来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扩展。⑤《列宁遗像》,《国闻周报》1926年第3卷第41期,第5页。同年,《共进》杂志上刊登了有关纪念列宁二周年的文章,文章就从国民革命出发,将列宁与孙中山放在一起,强调要接受“列宁和中山两位领袖的遗训”,肯定了国民革命的积极意义。⑥志颖:《在列宁二周年纪念日谈中国国民革命》,《共进》1926年第99期,第7~8页。
妇女界也参与了对列宁的纪念。南开女子中学部加入了列宁纪念活动,⑦《女子中学部》,《南开周刊》1924年第86期,第15页。《妇女周报》还专门刊登《妇女们该怎样追悼列宁》一文来号召妇女群体对列宁进行纪念,“即全世界被压迫的男女,都从此得了光明大道”,⑧《妇女们该怎样追悼列宁》,《妇女日报》1924年第24期,第1版。这也体现出当时女性作为政治力量正在逐渐崛起。
在当时,各方都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写在文章中,以期能够掌握话语权。以中共、国民党、北京政府三方势力为例,中共对于列宁的纪念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以期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国民党当时的纪念话语中侧重于借列宁来突出孙中山;北京政府的纪念话语则将列宁塑造成传统权威者的形象。如何掌握权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也是一直讨论的话题,也有人通过诗歌表达对于列宁的思念,主要通过列宁的精神层面展开,其中隐藏着公共权力要依靠个人能力来制定的思考。⑨谷凤田:《哀列宁歌》,《学生杂志》,1924年第11卷第5期,第71~72页。这种“公共权力”的设立,就是需要把社会冲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党派和组织力量也都在思考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⑩可参见周尚文:《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5~108页。
三、革命与实践:纪念列宁话语中的劳工精神
苏联胜利的秘诀是众人的纪念文章中所重点谈及的,一般文章都谈及了俄国革命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苏联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仲英称列宁为“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完整的继承了马克思的“精义说”的核心内涵。对于列宁的革命实践,他认为如何引导民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指出,空想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的,但在革命的实践中,革命党时常是“归纳出几个奋斗的标语,再由此几种标语引导民众来奋斗”,这样是学习不到列宁革命思想的精髓。①《列宁之思想》,《中国青年》1924年第1卷第16期,第2~7页。列宁从组织“工人团体”到组织“工人国体”,集合了“少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对旧政权的斗争,②《列宁之生平》,《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10期,第79~80页。完成了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纪念的文字中有不少文字可看出对列宁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崇拜,可归纳为“列宁已死,列宁主义尚存”“列宁死矣列宁之伟业则永世不朽”等。③《苏俄领袖列宁逝世》,《学生杂志》1924年第11卷,第106~107页。
在列宁的追悼纪念会上,出现了很多挽联,都对列宁的劳工精神进行了赞誉,例如“大家当学你劳工运动的精神,我等势作这无产阶级之奋斗”“你是和平神圣,你是均富先锋,你是人群保障;我哭慈爱母亲,我哭良好朋友,我哭世界元勋”等,④冷雋录:《“列宁追悼会”里的挽联》,《清心钟》1924年第2卷第5期,第15页。这些纪念话语都反映出了中国社会部分人群对于列宁的认知,其中“劳工精神”正是其最核心的部分。文苑在得知列宁逝世后,在纪念文章中对列宁的“好学深思”“刻意孤行”性格进行了怀念,最后回归到了世界上的劳苦大众,会想到他们却仍在“悲着苦着”,战斗就仍需要继续。⑤文苑:《列宁死了》,《江苏省第四中学校校友会月刊》1924年第15期,第13页。芸子将列宁与孔子归类,甚至还提出“列宁氏既有此崇拜孔子之表示”,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但作者实际想表达的是对列宁实施“劳农神圣、绝对排斥贵族”的推崇。⑥芸子:《列宁死后的感想》,《华语学校刍刊》1924年第3卷第2期,第17~18页。
中共的领导人陈独秀在纪念文章中讨论了列宁的存殁与苏俄革命的关系,认为不能把苏俄的胜利与否都归在列宁一人身上,但他也肯定了列宁的个人努力和天才的创见。⑦陈独秀:《列宁之死》,《中国青年》1924年第1卷第16期,第1~2页。相反,也有人对于苏维埃的前途表达了担忧,认为列宁的逝世使得劳农建设国家的基础动摇,替“呱呱坠地的苏俄担忧!”⑧《弔列宁》,《旅京四川什邡县同乡会会刊》1924年第1期,第47页。刘仁静在《悼列宁》一文中描述了令作者难以忘记的三件事,主要阐述了自己对于列宁革命的理解,在他的纪念文章中,与他人文章最不同的一点就是称共产党为“秘密的组织”,称列宁为“为人民奋斗的共产党的创始者”,探析了俄国共产党成功最根本的秘诀就在于共产党纪律严明,积极与下层民众接触,团结被压迫的同胞。刘仁静还通过列宁的事迹说明革命想要成功,还必须要有独到的眼光,列宁提出了西方社会革命和东方国民革命联合以推翻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同时还建立了共产国际,团结了众多可能团结的对象,是“中兴马克思主义之唯一思想家”。⑨仁静:《悼列宁》,《向导》第2集,第52期。
当然,对于列宁的批判声音也是有的。当时的一位新闻记者就描述了当时的现象,在列宁逝世之前,骂声很多,死后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变。同时也对民众作了批判,他认为前后几天时间,主义未改,而舆论却大变,这种现象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谁在推动着媒介与传播的进程?最后还批判了舆论界的模棱两可、趋炎附势。⑩冷雋:《看了“列宁追悼会”以后》,《清心钟》1924年第2卷第5期,第10~14页。
革命推进的原动力在哪里?高尔松在《谁是制造革命者》一文中批判了“一般人说起来总是在乎社会上兴风作浪轻举妄动的不安分子”的说法,将原因追溯到了更深层次社会原因,“无辜民众,受了这样多层压迫”,已经是极其困苦了,“革命的火焰,已一天浓厚一天。即使没有国民党没有热血者,那大流血大纷扰的时期也是不远了”。⑪⑪《谁是制造革命者》,《松江评论》1924年第33期,第1版。革命需要青年的参与和付出,贤江在《列宁与中国青年》一文中认为列宁是“革命家”“好模范”“学者”“穷困力行的人”,那青年应该怎么做,怎样将列宁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去。他指出:“我们不单要刻苦,不要会研究,还需得问一问刻苦了研究了究是为了什么?我们也不要单想革命,不要空谈革命,还须得问一问革命究竟怎样着手,怎样预备。”①贤江:《列宁与中国青年》,《学生杂志》1924年第11卷第2期,第7~8页。
列宁主张权力归劳农会所有,正是这一政策使得“全俄起了大革命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共产党、全俄的人民——除了不堪自觉的人们——都得救了”,且在世界上崭露头角。②高尔柏:《革命家的列宁(续)》,《学生杂志》1924年第11卷第4期,第49~51页。但是,仅依靠劳农,发展劳农经济就一定就可以成功吗?“社会主义果能屈伏资本主义与否一问题,久为世人所知”。建设劳农经济首先需要建设劳农政府,但在苏俄的具体实施中,有人认为,这样的政策实施,直接导致了苏俄的产业荒废,所以说劳农革命在经济上是失败的。③点玉:《劳农经济政策之变迁》,《国闻周报》1925年第2卷第8期,第5页。要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巩固阶级斗争之实力”,在政策上要做到革命后的建设缓慢推进。④参见陈通:《列宁主义的要义》,《省商》1926年第45期,第1页。
苏俄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众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当时的中国要面对的。以民族问题为例,列宁在主政苏俄期间就明确指出要打破民族隔阂,打破“开化”与“不开化”的界限。而1922—1923年的中国,联省自治思潮盛行,各省纷纷要求独立自治,但孙中山对此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新青年》杂志在列宁逝世后翻译列宁的这篇文章,想必也是与当时流行的这一社会思潮有着一定的关系。虽然苏联早年的民族自治问题与中国的联省自治风潮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政治家却正好通过列宁逝世这个契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蒋光赤翻译了列宁的这篇文章也有对当时国内这种思潮的一种回应:“把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自治权相混,或藉民族的自治为割地的保证。如此,民族自决的原则,从为欺骗群众的工具,变为揭破帝国主义黑幕的工具,变为以国家主义的精神启发群众的工具。”⑤蒋光赤译:《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新青年》1924年第4期,第60~66页。
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党的基本功能是清楚地阐明工人阶级的历史目标并激励和动员工人去实现这些目标。⑥〔英〕尼尔·哈丁著、 张传平译:《列宁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在诸多纪念话语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代表的政党及阶级意愿。列宁逝世后,苏联代表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上就表示“列宁人虽死去,而列宁的主义仍在世界”,⑦《全俄苏维埃代表鲍罗廷在“一大”会议上之演说词》(1924年1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2页。但在纪念的全文中未表明“列宁主义”是什么。在当时国民党占领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下,鲍罗廷表示了对于国民党革命事业与核心地位的支持。这一时期苏联很清楚如何利用前沿组织和现代通讯媒介来发动群众,而当时中共在动员群众方面也逐渐走向成熟,“大得工人农民之同情赞助”。⑧紫醇:《列宁死后的一周年》,《共进》1925年第74期,第9~11页。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强调共产党人要保持着“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应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态度,⑨《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节选)》,(1924年2月),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件汇编》(1915—1937)第1册,学习出版社 1996年版,第566~577页。原载1924年4月11日出版的《团刊》第7期。强调现阶段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必要的,只有通过与国民党合作,才能达到现阶段中共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共也意识到了“救世的真正道路在于透过外在力量组织起来的集体人,而组织这个外在力量就是党”。①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7页。
四、“列宁主义长存”:列宁逝世与中国革命
“许多人都当国家与政府是人民的机关与组织,或有以为国家机关与组织,或有以为国家机关是中立的,军阀当权即为军阀的国家,人民当权即为人民的国家,但是列宁的主张以为国家是压迫阶级的机关”,②敬云:《列宁的政治主张》,《中国青年》1924年第1卷,第16期,第7~12页。列宁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建党理论一直受到孙中山的推崇。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来看,他在后期的革命中也一直是学习列宁这一点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在做出决策时就要考虑“采用策略之合于当时实际环境”,要做到“干练和精明”。③任弼时:《列宁与十月革命》,《中国青年》1924年第3卷第52期,第21~24页。
在列宁逝世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开始将列宁与孙中山放在一起来谈,特别是将列宁所推行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理论与孙中山所主导的“三民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相关联。在类比的同时,大多数文章都要对暴力革命进行一定的批判。在列宁的追悼会上,就有“中华中山大,列强列宁平”的挽联,④冷雋录:《“列宁追悼会”里的挽联》,《清心钟》1924年第2卷第5期,第15页。来表明列宁与孙中山都拥有革命导师的地位。苏联的党国制让孙中山看到了国民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之人格,本不必较短量长,中山欲推行三民主义于世界,列宁则欲以苏维埃制度代帝国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兴,其眼光均注在全世界”。⑤连瑞琦:《覆友人孙中山与列宁比较的信》,《共进》半月刊1924年第70期,第3~4页。相关的文章还有很多,如何孝纯:《列宁与中山》,《沪江大学月刊》1925年第14卷第11期,第15~21页;耘青:《中山欲列宁》,《共进》1925年第78期,第14~18页;《哭中山忆列宁》,《中国军人》1925年第4期,第21~23页;洪筠:《五月纪念周中不可忘记之三大伟人》,《中国军人》1925年第6期,第2~4页等。还有文章将列宁与甘地等人放在一起对比,但最终结论大同小异,参见《甘地与列宁》,《中国青年》1926年第5卷第14期,第400~402页。
任弼时在文章中表明了对于列宁“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理论的支持与推崇。列宁在当时国内复杂的环境下,国内意见不一,倘若列宁不进行集中且统一的领导,苏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势必无法进行正常的运转。要想革命成功,就需要拉得下脸面,他认为:“列宁在此危急存亡之际,能一眼看清大局,十天之内依环境的变化而屡次变更其政策,以促革命与成功”。这里作者也是想表明,不要怕犯错,要坚持真理。他在文中结尾称列宁“能以自己的毅勇刚强制驭群众之心力”可谓是值得钦佩的。⑥任弼时:《列宁与十月革命》,《中国青年》1924年第3卷第52期,第24页。但也有人在思考,这种模式对于政治的长期发展是否就是真的有利?在当时的纪念文章中就有记载列宁逝世后列宁的夫人对列宁生前所提出的有关商业权制度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⑦《列宁夫人夺其夫志》,《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27期,第11页。因为这种模式往往伴随着一定的个人权力集中。当权力集中的革命家逝世后,那国家又当如何?有的文章即提出,一把手逝世势必会造成权力的真空,所以在逝世前的职务分任就显得非常重要。⑧可参见《苏俄领袖列宁逝世》,《学生杂志》1924年第11卷第2期,第106~107页。列宁逝世后,各方势力就会进行权力的争夺,有时甚至兵戎相见。如《申报》就对当时的在沪俄难民进行了报道:“本埠俄难民闻列宁氏死耗,骤增其回国扑灭红党希望,颇有跃跃欲动之势。”⑨《列宁死后之在沪俄难民态度》,《申报》1924年1月28日,第13版。有人在纪念文章中指出:“列宁的思想即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因此他即注重社会事实的研究和与群众直接的接触”,⑩《中国青年》1924年第1卷第16期,第2~7页。这种建党理论倘若需要一直维持,就必须要做到主要革命家“其所主张,足以代表苏俄共同宗旨”。①《列宁先生事略》, 《建国粤军月刊》 1925年第2期,第3页。还有人指出,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办了一个《火花》杂志”,列宁开始掌权后就极力灌输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变成了‘列宁之火花’”,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了集权后所带来的革命成果。②亨如:《无产阶级的致命伤——尼古拉列宁之死的感触》,《批评》1924年第18~19期,第22~26页。
纪念列宁的文章中大都是褒奖列宁,但也有人在文章中对列宁其人其思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宪汉等人认为现在对于列宁的评价不能盖棺定论,作者并不认同列宁的理论,将列宁比作“怪物”,认为他“一意孤行,必欲达其所系之目的而后止”,但另一方面,作者又赞赏列宁“一切成功之父也”,表达了对列宁在精神层面的敬仰。同时,作者结合中国本土根深蒂固的“十八层地狱”等事物,谈到在列宁的指导下,开始迎来“世界革命之怒潮”。③宪汉:《精神之列宁》,《兵事杂志》1924年第118期,第1~11页。还有人对列宁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列宁是“革命的叛徒”,不承认他的革命导师的地位,认为他在掌握政权后就背叛了革命,开始违背自己早年的政策,“表面上挂了一个劳工专政的招牌,但若真正的劳动者要起来专政,于共产党自然有大不利的地方,故他们必要压迫劳动者,使劳动者无真正活动的能力,以便号尽量为他们利用”,认为列宁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其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列宁的劳工专政理念与具体实施中的劳工专政是有所背离的。④芾目:《列宁——革命的叛徒》,《学汇(北京)》1925年第477期,第3~5页。甚至有人直接对列宁进行人格侮辱,认为“列宁倡不道德之共产主义必变衣冠禽兽”。⑤王有孚:《列宁共产主义与太戈尔唯心主义孰为纯正试申论之》,《青年镜》1924年第38期,第25~26页。
李大钊将列宁的贡献与全世界的人类发展联系起来,不仅谈到了“当下”,还谈到了理想与未来。他指出,列宁“躯干虽死,但精神不死”。⑥李大钊:《列宁不死》 (1924年3月30日),选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0页。瞿秋白在参加列宁的追悼会时指出,是列宁带领苏俄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他回顾了列宁的生平,指出了列宁革命所带来最大的国际意义——国民革命。人们在谈及国际意义时,往往要与自身利益相关才能称得上是“国际”,而当时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正是在苏联影响下展开的。⑦冷雋:《看了“列宁追悼会”以后》,《清心钟》1924年第2卷第5期,第10~15页。列宁逝世后,世界各国对其都有所评价,除了对他精神的赞扬与宣传之外,也有国家社会对他的认可的描述,如《国际公报》就有“如拿破仑等遗留人物其名实可并驾齐驱”的描述。⑧东方时报:《悼列宁逝世》,《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10期,第14页。恽代英注意到了列宁的学者身份,注意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活学活用,即重视“俄国实际情形”。恽代英在文章中还批判了那一时期青年在革命实践中的幼稚与眼高手低,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未有过夺取政权的打算和计划安排。⑨恽代英:《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中国青年》1924年第1卷第16期,第28~29页。陕西早期革命者创办的《共进》杂志也通过1924年初所刊的《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一文表达了对于列宁的纪念,文章谈到了列宁与世界革命,强调列宁的革命,强调列宁的革命的方法,号召中国青年去认识真正的列宁。⑩松:《列宁之死与中国青年》,《共进》1924年第55期,第1版。
纪念话语中关于这一方面谈及最多的就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前后的苏俄形势。“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列宁事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受了革命先进国的指导和帮助,全世界劳苦群众及被压迫民族相信了自己的力量”,⑪⑪长天:《列宁与中国国民革命》,《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第45期,第1~2页。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国际角度下的列宁。列宁逝世后,不仅在中国,国外也有很多纪念列宁的讨论,如美国就认为列宁与苏俄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苏俄外交关系而论,列宁之死未必有重大影响。或稍推迟外交上之调整,则不可知耳”,①《美报论列宁逝世与俄国前途》,《申报》1924年1月26日,第6版,还可参见《美国舆论中之列宁》,《青年友》 1924年第4卷第789期,第47~48页。还有英法德等重要国家,对此也有相关的纪念或报道,中国社会各界对于列宁的认识也与之有关。2.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建立与如何推翻的。集体意识的构建会创造一种新的政治认同,有关纪念列宁的话语就是相关的群体所促成的,它是推动社会价值观念重整与重新建构的因素。3.党和阶级的关系。任何纪念话语的建构都是在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完成的,政党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过去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为了服务当前的政治需要,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即“历史为现实服务”。②参见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中共的集体话语也就在这一事件后逐渐形成,从知识分子的团体到有组织的政党转变。4.纪念话语中列宁的乌托邦思想。五四之后,自由主义思潮与共产主义思潮开始争论,但这种讨论往往集中在上层知识阶层。
在探索和反思中前行,是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共同方向。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是一个正在初步发展的政党,面临着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以共产党为例,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仍然很弱小,初期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困境,党的章程中很多条目想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践是十分困难的。而北京政府虽然在发展时间和力量上比国共两党较有优势,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国共两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统治已经有危机显现。中共和国民党开始一系列的实践,如中共开始讨论中共党员是否可以加入国民党?怎样与其合作?国民党开始思考如何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如何保持与苏联的关系,而这些实践与列宁的关系密不可分。各方通过对列宁的纪念,也是为了能够使自身获得列宁的政治遗产与中国革命的“解读权”,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与政治力量。
五、结语
1924年列宁的逝世,看似只是发生在苏联的一个政治事件,但在这个事件的背后,隐含着多种力量的博弈,同时也凸显出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对于中国革命道路及前途的探讨。列宁逝世后,中国社会各界形成了一阵纪念热潮,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在国外尤其是俄国,其纪念的文字更多,在其纪念话语中,更多的则是描述参加列宁纪念活动的心理状况。以《兴华》期刊中记载为例,作者讲述了韩克君(在俄国的美籍俄人)当天的悲伤心情。③《寓俄美籍俄人韩克君追述列宁出殡情形》,《兴华》1924年第21卷第16期,第14~15页。与此同时,列宁符号在俄国也有了更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列宁的墓标竣工后,列宁的遗像禁止用来作为商标或装饰品等,④《列宁墓标》,《兴华》1924年第21卷第18期,第29页。这与后来孙中山逝世的场景也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南斯拉夫学者德·列科维奇认为,列宁的遗产中似乎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面,或者简单地说,存在着两个列宁——具体环境中的列宁和本质的列宁。⑤参见《苏共历史问题》,1991年第3期。转引自王丽华:《国外列宁研究中的不同观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这一论述在周尚文《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也有大段的描述,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神奇的伟人列宁》一书中也有相关的描述。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列宁逝世”的表达也就逐渐发生转变,且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前后的话语差异也就异常明显。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与矛头在这一时期也就暂时放在了一边,例如《工人周刊》上在1926年的一则说明栏中就谈到列宁逝世两周年的消息,号召“全世界工人都能按他的主义奋斗”“全国民众现在应致电请国民革命军北伐!”①《书报说明栏》,《工人周刊》1926年第137期,第3页。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于列宁逝世的纪念,并不是一个举国大范围的活动,这与后来孙中山逝世的纪念程度有着较大的差距。笔者阅读了当时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大多数人对于列宁逝世并无相关纪念文字的记载,即使有,也大多与胡适、颜惠庆、吴虞等人的记载类似,仅有三言两语,比如:“今日报上有两件大事,一为列宁之死,一为英国劳动党内阁之成立”②胡适、曹伯言主编:《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列宁逝世”③《颜惠庆日记》(第二卷),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饭后阅报,俄列宁与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五十分逝世”④《吴虞日记》(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对列宁逝世,实则并无多少感触。大多数报刊也是一样,大都只是对其基本生平进行介绍,或介绍列宁的逝世消息、逝世原因等,并没有发表纪念或批判列宁的文章,“列宁已于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钟五十分,在莫思科附近之哥尔基村附近逝世,年五十四”,⑤《国外之部》,《未复》1924年第285期,第12页。且一些报纸的报道,往往也只是出于其新闻的商业价值。
纪念是举行仪式、保存记忆的一种活动,是一种历史书写,历史通过纪念来表达,历史因纪念而精彩。⑥胡国胜:《纪念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第16版。各种纪念活动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文化的演进和文明的进步。⑦孙业礼: 《“纪念”是篇大文章》,《党的文献》2012 年第1期。纪念话语是重塑社会记忆的必要手段,政治家往往会从中找寻事例,寻找与民众相似的境遇。⑧〔法〕布鲁诺·佩基尼奥:《集体记忆与新记忆的产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12月,第29页。各种有组织的话语纪念转化为社会话语下的意识、认同、价值观念,这种组织的定位既包括了个体思想的客观利益,也包括了组织的信念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探究的纪念列宁话语,也仅是局限在文本上的分析,而有关报刊的宣传效果,如报刊的受众、阅读后的心得以及报刊的销量,也是对纪念列宁话语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可开展进一步的研究。⑨关于纪念列宁的相关仪式,各个派系、组织的仪式也是不同的。以平民自治会的纪念仪式为例,“于昨日下午二时在该会所开列宁追悼会,会堂中间置一列宁遗像,门首扎松花圈门一座,上面横竖匾额一方,上书‘世界平民伟人’六字,计到会员二百五十余人,公推蒋作新主席首由主席叙述列宁氏生平事略述,毕令各会员向遗像敬三鞠躬礼以表哀悼……后有马杰提议将本会追悼情形致电北京全俄代表加拉罕君,请其转达彼国政府以表哀忱主席提议加入上海各团体追悼会,经全体一致赞同,时已四时,遂散会”。(《平民自治会追悼列宁纪》,《申报》1924年2月15日,第18304号,第13版)当时的广州地区也有下半旗三日等仪式来纪念列宁。(《笺 函七局各局俄国总理列宁先生逝世本厅各局本日下半旗三天由》,《广州市市政公报》 1924年第114期,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