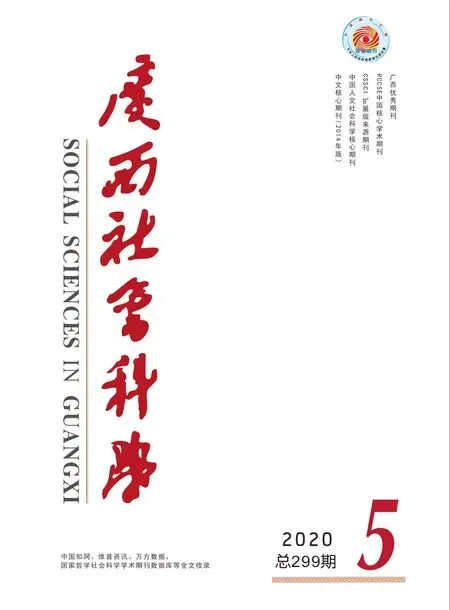“群众路线”实践与革命时期的政治整合
——以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运动”为中心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马克思认为,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其队伍必随历史活动的深入开展而发展壮大[1]。“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苏区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其具体论述为共产党和红军当开展“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等工作[2]。于其具体实践,1934年初毛泽东发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强调:“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3]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群众路线并丰富其内涵的又一关键时期。学界于“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问题的研究多是分而论之。其中,于“群众运动”,海外学者常会专文分析某一具体“运动”并将其融合于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相关主题论述中。而且,他们常将后两者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之一,是1949年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基本组织原则和决策模式及实现相应政治参与的基础。同时,作为一种治理方法它显现出了与所谓西方民主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总体而言,海外学者的此类研究虽不乏中性观点和立场,亦值得借鉴,但其相应论述毕竟与具体语境有隔离性,且结论或过度宏观,对象过度集中于某些具体命题,不能凸显中国革命、建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将“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相融合,具有显见的“思想史”研究特色。他们常多维度揭示“群众”及“群众路线”的概念内涵演进,并尤重关键历史节点、事件、人物与“群众路线”思想和“群众”理论演进之影响;或梳理其理论渊源、哲学基础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或论述其与党的思想路线演进,现代国家建构或国家治理之关系;他们对“群众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1949年后且多以“政治动员”“阶级斗争”或“群众工作”为问题意识,意图揭示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原因及影响,分析其与国家治理——尤以乡村治理为重——之关系;一些学者还注重梳理不同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等,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非正确“群众”观念对爆发“群众运动”的影响。总体而论,前此研究虽能凸显“思想史”的“新”发现,但却不能揭示“观念”如何观照于具体行动的实践机制及其过程。有鉴于此,拙文拟专论群众路线实践如何与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试图揭示群众路线实践内含的政治整合功能,以期丰富对群众路线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关系——尤其是群众运动的触发、运行机制——的认识。
一、危机:灾、疫肆虐威胁边区民众的生产、生活
陕甘宁边区曾是灾、疫高发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其即遇丰年也难免常现饥馑。1937—1949年间,边区每年常有一些地区,遭受旱、涝、雹、虫、霜、冻、疫等自然灾害。此间,在边区,又尤以1940年、1947年的灾情较重。1940年春,志丹、绥德、盐池等11县遭受旱灾,受灾人口558681人;同年,边区还有21县遭受水及冰雹灾害,“为近百年来所未有,哀鸿遍野,嗷嗷待哺”[4]。1947年,佳县、米脂、榆横、子洲、靖边及延安、安塞、子长、延川等县,春旱、秋涝、霜冻、雹灾、水灾、虫灾交相为害。值此之际,胡宗南进攻边区并在所占区域强行移民并村,边区损失粮食25万石粮食,牛和驴6万余头,农具23万件。此“人祸”和天灾并发,在边区造成灾民达40万以上的大饥馑[5]。
而且,灾、疫发生,亦皆常导致边区人口大量死亡。于此,李鼎铭曾言:“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高达3%。”[6]1939年国联防疫团的调查显示,“延安流行性感冒、痢疾、伤寒为最多”[7]。“延安是今日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流行鼠疫的地方之一。”[8]流感、花柳病、疟(痢)疾、吐黄水等是边区常见且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据调查,延安每年因感染此类病而死亡者达528人[9]。另,斑疹、伤寒、回归热等传染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亦高。例如,1941年1—4月,边区发生传染病疫情,甘泉、富县、志丹三县疫情最重。其中,仅甘泉一、二、三区876人染病即死亡186人[10];延安北区的红庄发生猩红热疫情时,“该村十岁以下之小孩子因患此病而死者已有十数名,该村现有小孩发生此种传染病占50%,发病后而死者占20%”[11]。另据统计,1944年1—4月延安死亡人口中,未成年人、妇女多死于破伤风、产后风,其余成年男子则因伤寒、回归热、肺炎等急性传染病而亡[12]。
此外,动物瘟疫亦对边区社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例如,1941年春、夏季,靖边、定边因羊、牛瘟疫而死羊20000余头、牛16000余头;1941年、1942年夏,延安县、志丹县因牛瘟而死牛分别为500余头、574头[13];1943年,边区的牛、羊的死亡率因羊瘟、牛瘟爆发而占其繁殖率的61%、81%[14]。
二、资源匮乏:贫穷、愚弱与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陕甘宁边区何以灾、疫频发?这其间,气候、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自当是关键原因。但是,除前述原因外,中国共产党则是以“社会革命”检视此类问题。毛泽东强调:“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15]就“穷、愚”而言,边区广大乡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盲高达99%”[16]。红军入驻前,边区人口识字率仅1%,“小学只有120处,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17]。
除“穷、愚”外,边区还缺医少药。1937年1月中央进驻延安城时,城内只有六七家诊所和少数坐堂中医[18]。盐池县城里有两三小中药铺,乡村有少许江湖郎中、花儿匠(种牛痘)、“卖药先生”等[19]。而且,“医药之道,多来于往来政商,有善医懂药之士,为民济救,或巫婆神汉。欺世渔利,草菅人命,殊为可叹”[20]。庆阳县仅西峰有一所仅10张病床的医院,医疗器械简陋,医护人员也仅11人[21]。时至1940年,边区的巫神仍多达2029人,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医却仅千余人,兽医50余人,“工作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22]。1944年延安县仍有巫神200余人。其中,有59个巫神治病时,使278人死亡[23]。华池温台一村庄49户300余人,“每年每人迷信消耗粮食达3斗零8合”[24]。李维汉于此曾言:“全区巫神高达 2000余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25]
前此情势使中国共产党认为唯有发动社会革命才能解决问题。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指出:“边区文化教育,必须努力除去革命前旧制度对于广大民众所遗留的文化落后状态——文盲、迷信、不卫生等,用各种方法,推行对于边区人民的自然科学常识与卫生常识的教育。”[26]事实上,必须克服灾、疫肆虐与民众贫、病合成为害的危机,即是党中央欲扎根边区并推动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历史背景。
1937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制定规划,强调扩大卫校规模和增设医院,主张以群众卫生运动推进卫生防疫工作。1939年1月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决议”,要求“发展卫生保健事业,以增进人民的健康”[27]。此次大会通过《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案中,“护林植树”、“提高人民卫生知识,注意公共卫生”、“城镇设立药房”、“培养卫生干部”、“破除迷信,取缔巫神”[28],即是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关键措施。而且,为使群众卫生运动做到有章可循,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此决议希望“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造成人民对身体、衣着、住宅、饮食、便溺等等均有清洁卫生的习惯”,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医药,研究中药,开办中医训练班。发展制药厂,设立医药合作社,增设各地卫生所,以发展医疗工作”①《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边区二次党代表大会文件汇辑,陕西省档案馆(220/0591)。。此后,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强调,边区政府“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1000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29]。而且,在接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时,他指出:“每乡要有一个医务所,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30]6月,中共西北局办公厅召集了延安医药卫生机构负责人开会,再次部署群众医疗卫生工作。11月,边区参议会通过《关于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再次强调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此外,1944年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各界卫生动员大会上指出,边区应开展“医药卫生运动,同病疫流行的现象做斗争,做到“人与财旺”[31]。总之,中央要求“动员边区各机关、军校、学校、医院参加清洁卫生运动,从机关驻地人民中做起,推广到各地等五项办法”②同上。。
三、历史记忆:优良传统与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能否将自身内部“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成一单一性民族政治共同体”[32],是发展中国家完成其现代转型须直面的难题。因为,现代化会造就或唤醒过去或根本不存在,或被排除在传统社会政治范围之外的某些社会集团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它们或被现存政治体制同化,或“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的祸根”[33]。“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34]为此,这要求政治主导力量整合分散或分化的社会力量,并动员、引导和推动相应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虽仍是一传统农耕社会,但却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场特殊的“农民革命”,农民曾常被视为分散且外在于政治的社会群体——进行再出发的“基地”。党欲将边区建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唯有依靠群众并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政治”。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35]这也恰如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政治整合作用所论,即“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36]。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在无产阶级运动初期,工人是分散且因竞争而分裂的群众[37],但是,他们更强调,工业发展必使成长的无产阶级能影响其他阶级。而且,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能积极创造世界历史。觉悟群众的“革命”被列宁认为是消灭专制制度的伟力[38]。因此,高度认肯并开展群众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之反映,是其领导革命的基本方法论。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关键贡献,即是能认识到唯有依靠群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39]。他视十月革命是依赖于“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40]。他强调:“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41]中共三大即强调:“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42]为此,中共三大还专案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需指出,毛泽东对推动群众运动及其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贡献。早在1921年1月的新民学会的会议发言中,他就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3]。他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痛言忘记“农民”是党内“左”右倾错误共有的思想特征。他告诫全党,把“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力量”[44]。据实而论,依赖群众运动以完成政治整合,是中共领导革命自始即有的重要特征。
若此,群众路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既有传统,就成了边区“群众卫生运动”的历史底色。例如,1932年,闽西、江西富田等地爆发高致死率的传染病疫情[45],苏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布第2号训令,要求为“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各级政府需领导工农群众来执行这一条例中各种办法,尤其是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使工农群众热烈地举行防疫的卫生运动,使瘟疫不至发生,己发生的迅速消灭,以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好更有力地向外发展”[46]。经此推动,苏区各根据地认识到:“卫生是与革命发展有关系的,在目前残酷的国内阶级战争中,避免灾疫,坚强一般群众的身体,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47]1933年4月15日,福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对内务部目前工作的决议》,指出“加紧领导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深刻去了解卫生是保护健康的唯一办法”,要求“最广泛的发动群众举行卫生运动竞赛,以提高他们讲究卫生的热情”[48]。
四、“权力技术”运用:“群众卫生运动”中的政治整合及目标实现
学界——以西方学界为要——常认为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是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49]。而且,它尤其依赖于将“权力技术”运用与群众运动相融合。在微观层次,如物质激励、宣传口号、情绪调动、典型示范等。其中,决策—召开会议—建立工作机构和队伍—宣传发动—颁行措施和组织实施,成为“群众运动”的范式性流程。陕甘宁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于此亦不例外。
为克服灾、疫肆虐造成的危机,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纳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50]。经此推动,1939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卫生干部扩大会议召开后,作了《发扬民族革命中卫生工作的精神》的报告。是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建立边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决议案,提出要“发展卫生保健事业,以增进人民的健康”[51]。边区政府1939年施政纲领亦提出需“救济难民灾民,不使流离失所”[52]。1939年11—12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更提出要将“群众卫生运动”与民众知识文化教育相结合,提出大力开展医疗卫生建设。而且,基于“群众路线”的指引,“面向基层,为群众服务”被确立为“群众卫生运动”应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如据不完全统计,1941—1943年,边区医院的群众病员比例分别是25%、27%、30%。其中,1943年边区医院医治群众病员9611名[53]。1944年,边区卫生处派出医疗队到延安县、子长、甘泉、富县等地累计为3500名民众看病;边区医院门诊初、复诊群众病员达50000余人次,收容群众病员2000余人[54]。
建立机构和确立“预防为主,医药为辅”的工作方针,为通过“群众卫生运动”进行政治整合奠定组织基础,提供方向指引。1940年5月26日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随后,延安各机关单位以及乡镇亦相继成立分会。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召开第六十三次会议专论卫生工作,要求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带头示范,定期进行卫生大检查。经此,边区形成以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为主干,防疫委员会、卫生合作社、保健药社、国医研究会等民间卫生机构为补充的医疗网络。7月,边区防疫委员会在《总结防疫卫生工作》中指出:“在此期间,各单位已成立了防疫分会,健全了组织。各机关、部队、学校、医院、群众团体加强了厨房、厕所的建设,挖了污水坑、垃圾坑,环境卫生比清洁,个人卫生比进步。许多单位实行分餐制,整顿市容,预防接种率达80%。”[55]此外,1941年4月,边区成立家畜防疫委员会,专事家畜防疫[56]。
而且,边区基于相应组织体系将群众卫生运动纳入规范性、制度性、程序性的动员体制中。如,为促进疫病“积极预防”的规范化和制度化,1942年5月13日,边区政府通过《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该条例要求,鼠疫、霍乱、天花等一类传染病例需于确诊后24小时内电告防疫委员会并实行隔离[57];对伤寒及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等二类传染病需与确诊后实行按周报告。1942年11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重视防疫》的社论,要求边区各界对传染疫病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此,边区政府常组织医疗队下乡巡回检查,或前往疫区巡视、调查、指导防病工作。如甘泉和延安东二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暴发后,边区政府即封锁发病区,派员赴病区医治并调查病因;对延安机关学校停止集会和报告;对来自疫区人员,不论病否均予以10日隔离;对发热及疑似者亦严格隔离[58]。5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夏季防疫工作》的时评和预防疾病的科普文章,批评一些机构和人员不重视积极预防工作。经此,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卫生运动”并将群众纳入运动即成政治整合的基本目标之一。
尤其是,边区对“群众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典范性的流程要求。例如,1944年边区政府召开文教大会通过多项有关卫生宣教的决议。其中,《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要求,“为要普及卫生运动,需要动员一切县、区、乡干部,小学教员和中小学生,劳动英雄和其他积极有威望的分子,驻军和机关人员都来学习卫生知识,并成为卫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宣传者。而教育家庭妇女使能了解卫生常识,尤为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对宣教的具体形式,《决议》要求,“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书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而且,《决议》强调应防止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必须注意发现、创造和表扬”个人、家庭或村、乡或区的范例,“用以推动全局”,并“在运动开展之后,即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组织领导,以求持久”[59]。
依循前述流程,边区政府首先组织卫生宣传队和动员其他力量开展卫生宣传。其中,干部、劳模、小学教员等需向群众讲解医疗常识,引导其树立正确卫生观念。而且,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文协、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边区群众报、教育厅、中央出版局等单位联合决定,文艺团体等下乡演出时卫生署即派出医护人员配合工作[60]。其次,举办多形式的卫生(知识)展览——如挂图、统计表格、生理解剖图等。例如,1940年“三八”妇女节,边区首次举办妇女卫生展览会,参展人数过万——后从中央礼堂转到延安大学礼堂[61]。再如,1944年延安再办卫生展览会,军、民参展人数分别达6667人、4303人[62]。此外,1943年延安留守兵团在生产展览会上展出自制药品60余种[63]。最后,报刊和印刷的小册子成为传播灾、疫防治知识的关键载体。如,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时即辟卫生宣传专栏,刊载边区或其他根据地的卫生工作报告、成绩、经验,介绍防病常识和传染病防治法。边区卫生处印发《军民手册》2000册、《传染病防疫问题》、100册、《防疫须知》300册及8种防疫传单[64]。基于经验总结,1946年4月23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一次大会通过《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建设计划方案》,对前此工作作出详细部署。该方案要求:“边区卫生署应协同各文化团体出版机关从速编印各种卫生常识,宣传卫生的挂图连环画等,各级报及各文艺团体应经常宣传预防疾病瘟疫的具体办法,利用各地庙会组织卫生宣传与展览。”[65]
尤需指出,塑造模范并以模范带动群众是边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宣传的基本形式之一。边区在防疫委员会的组织动员下,表彰和宣传严家湾、杨家湾、黑龙沟、高家园子和南窑子五个卫生模范村,以及宋志忠、高文亮、刘成义等十七个卫生模范家庭[66]先进事迹。此间,边区发动基层干部、劳模、变工队长、小学教员等与医护人员和其他积极分子合作便开展卫生宣传。如,杨家湾小学教员陶端予既当教员又当宣传员,又是卫生员,并力促该村成为卫生模范村[67]。边区开展学习崔岳瑞运动力促群众不信巫医神汉①崔岳瑞(1896—1965)是定边县红柳沟镇卜掌村中医。他深入群众,为群众治病,调查揭露巫医神汉骗人的伎俩,成为边区卫生运动中的模范。1944年10月,定边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三次会议和县“群英会”合并召开,崔岳瑞被选为县民主政府委员和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的代表。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决定在边区开展号召群众向崔岳瑞学习的运动。。而且,边区还推动从机关到农村在模范或模范村的带领下,开展制订“卫生计划”或“卫生公约”的活动。例如,白原村一老师既在学校发动制定卫生公约,又发动群众制定村卫生公约。其内容主要是:“(1)碗筷锅盘案,饭后要洗净;(2)剩饭和剩菜,不该苍蝇叮;(3)若要不得病,不吃生和冷;(4)人人手和脸每天洗两遍;(5)要将脚和衣,每月洗四回;(6)厕所经常铲,牛圈两次垫;(7)人人能做到,年年不生病。”[68]综上活动有助于使卫生文化知识传播同移风易俗结合以重构社会文化模式。
五、结语
面对陕甘宁边区的灾、疫肆虐与民众贫、愚交困,党唯有依靠群众并组织和引导群众参与“政治”才能克服前此危机。这就需将“多元社会”内部的“原生社会势力糅合成”一政治共同体。由此,党作为边区的政治主导力量,将多元社会力量纳入非常规性政治动员——“群众卫生运动”。这是将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自觉行动,使其力量触角遍及边区的城市、乡村,使卫生文化知识传播同移风易俗结合以重构社会文化模式。它亦使群众路线内含的政治整合功能因与群众运动结合而凸显,更揭示了党在革命时期进行政治整合何以常依赖于“运动”的关键原因。因为,首先,“群众路线”实践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提供了政治原则保障及话语供给。其次,危机严峻,体制内资源匮乏,常规性和程序性的政治动员亦难短时奏效,群众路线实践却能推动党凝聚和组织群众并形成磅礴力量。最后,与“权力技术”运用相合而成的“历史记忆”是“群众路线”实践演进为“群众运动”并被发展成为“政治偏好”的文化支撑。如党对苏区革命时的“群众卫生运动”的集体记忆,即是边区“群众卫生运动”的底色。事实上,对政党而言,“历史上在某种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成功加强了决策者坚持现行政策和制度的信心,有助于制度的连续性,在面临同样的困境时,决策者会很自然地从以往成功中学习以便于能够再次成功”[69]。
可申论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群众运动仍常出现亦与前述因素的演变相关。与之相应,当下中国传统群众运动显著降低的关键原因也系于此。因为,社会危机已解除,体制内的资源日渐丰沛,社会整合中的秩序建构更需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行为为支撑,所以,群众路线实践作为“路径依赖”,势必在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产生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