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近年小说创作的抗战叙事
陈进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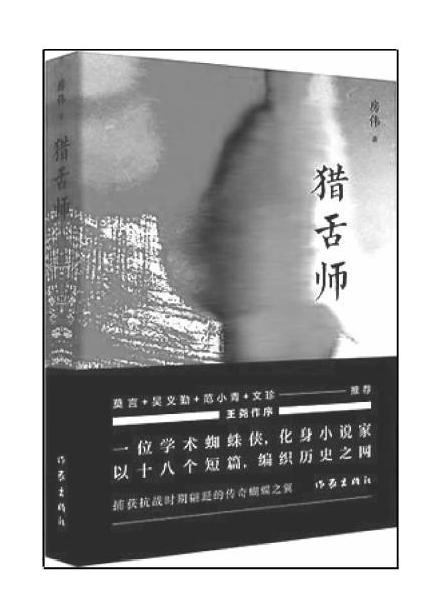
房伟是知名批评家,也是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但他又是作家,写小说、诗歌等。对此,范小青直言:“房伟多才,涉猎多个文学门类,小说、评论、人物传记、学术著作,而且,他在哪个门里都很精彩。”[1]201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这也是他首次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并为读者所熟知。最近几年来,他的中短篇小说频频发表在《收获》《当代》《花城》《十月》《天涯》《大家》等名刊,又总是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频繁转载。2019年,他的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一经推出,因以全新视角深入探寻抗战历史中的灵魂挣扎,备受文坛关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房伟已成为批评家从事小说创作的优秀代表。
稍加回望新世纪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侧重写历史的小说大多接续或拓展了新历史小说精神质素。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生死疲劳》、兰晓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麦家的《风语》、李锐的《张马丁的第八天》等,打破了传统意义的历史情结,消解了文学和历史的二元对立关系,不以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要求,也不再奉行所谓的尊重历史精神,而更倾向把人物及其活动时空置身于某种“历史形态”之中。然而,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并不着意于“解构”,也未倾心去阐发历史的文化性,而在处理文学和历史关系、探寻人性之真假善恶等方面实现了他有意而为之的创作突破。可以见到,房伟似乎并没有受到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言的“诱惑”,也未陷入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的“对历史的拒绝”之中。恰是如此,以《猎舌师》为代表的抗战小说获得了一种普遍性价值,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潜在的深刻性。
一
房伟对自己的抗战题材小说创作有他特别的理解和表述:
几年来,学术研究之余,我一直对抗战史料保持着业余兴趣。在历史的深处,我发现了很多非常有趣,令人惊讶,也令人慨叹的细节。同时,我对当下杭战历史小说也有诸多不满。很多作品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如何能写出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呢?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历史小说创作。[2]
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确,房偉创作抗战小说既是源于他对抗战历史的浓厚兴趣,又是出于他对当下抗战历史小说创作现状不满后的叙述冲动。既然要避免“流于戏说”或“过于沉重乏味”,那么房伟又将如何充分利用史料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历史小说”?或者说,房伟的小说到底书写了怎样的抗战历史?很显然,从首篇《中国野人》到尾篇《五三》,每篇小说都有着超越性的叙事视角和所抵达的灵魂高度,以时间为经和空间为纬,全景式编织了中国的抗战历史。
从叙述时间来说,房伟用18部中短篇小说串联并建构起了自1928年至1945年的抗战历史。短篇小说《五三》中可以追溯到关于抗战的最早时间。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写道:“作为房氏子孙,老济南城的后代,我更愿相信,爷爷房吉禄,一个普通小商人,在1928年5月3日那一天,触摸到了大历史。”另一部短篇小说《地狱变》则明确写到了抗战结束时间即1945年——“昭和二十年,原子弹在长崎和广岛爆炸,日本投降,光秀切腹自杀,骨灰回到了日本。”结合两部小说的内容来讲,《五三》中1928年所触摸的“大历史”实则与其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从1931年到1945年,关于“十四年抗战”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和阐释。循着小说的时间线索,我们很明显看到房伟小说对于抗战的各个时期均有展现。在《五三》中,蔡公夫人郭景鸾找到将军遗骨,突破日军阻挠,而后存放于南京外交部地下室。这个时间是1930年6月。在《副领事》中,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通知南京政府副领事“失踪”的时间精确到“1934年6月9日上午9时半”。1937年,南京城破,《五三》《幽灵军》《手肴》等都是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叙述中心。《猎舌师》《杀胡》等小说则将时间分别具体到1939年深春和1939年8月14日。日本陆军中尉长谷川信彦(《幽灵军》)失踪于中国南京郊区的麒麟营一带的时间是1941年秋。而兵库县但马区的水源清(《地狱变》)首次到中国的时间是1941年冬。《小太君》和《中国野人》写的都是发生在1944年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每篇小说中时间与历史节点相呼应,使人清晰地体悟到时代脉搏和历史律动。
若从历史时间的标示来看,房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用中国和日本两种不同的纪年方式多视角多层面呈现抗战历史。比如,昭和十二年(1937)、昭和十三年(1938)、昭和十四年(1939)、昭和十六年(1941)、昭和十八年(1943)、昭和十九年(1944)、昭和二十年(1945)和昭和三十三年(1958),等等。应该说,这种互为参照的历史时间的呈现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房伟对叙述空间的把控和调度。王尧指出:“虽然这些小说篇幅都不大,但从叙述空间讲,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岛,越南的河内,中国的则有南京、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济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据地、山东莒县、香港、台湾等。”[3]实际上,除了日本的北海道和屋久岛提及较多之外,房伟还是将叙述空间聚焦于南京和济南等城市及其相关区域。简要来讲,以南京为叙述中心的小说主要有《幽灵军》《猎舌师》《手肴》《副领事》等;以济南及其周边区域为叙述中心的小说则有《中国野人》《小太君》《五三》《杀胡》《起义》《指南》《七生莲》《花火》《还乡》《鬼子妮》《地狱变》等。可以直观看到,写济南等山东城市及其空间的小说占了绝大多数,这显然与作家的地域体验和生活经验等因素有着直接关联。不过,房伟特别善于将短篇小说的精巧发挥到极致,每篇小说构成自成一体的“点”,点点成线、以点带面,不动声色地织成了历史的横截面,从而形成了当下时空对于抗战历史的重新发掘和理解。
房伟的每篇小说开头都有着宏阔的地理区域和深远的叙事空间。不妨集中来考察以下小说的开篇:“参谋长翻过西凤凰山,看到了洪涛汹涌的漳河水。”(《花火》)“那不过是昭和年间的旧事了。世上的事谁都说不准,昭和十九年(1944)端午,少年兵黑木星羽在中国鲁地济南,遇到了女孩金娣,金娣就这样记了他一辈子。”(《小太君》)“进入冬至,吃了饺子,雾霾就不知不觉地笼罩了济南城。傍晚,我顺着护城河,过了解放阁和黑虎泉、老西门,多走一会儿,不知不觉来到淮阴区经四路的蔡公时纪念馆。”(《五三》)“北海道是日本北面的苦寒之地,最早定居着原住民阿伊努人。”“从北海道出发,坐船3天,才能到达中国青岛港,从青岛坐汽车,1天行程,才能到山东高密县。”(《中国野人》)“昭和十二年(1937)冬,东京雪花飞舞,遥远的中国首都南京,却格外肃杀冷清。”(《幽灵军》)“昭和十六年(1941)冬,兵库县但马区的水源清,梦中‘第一次见到中国鲁地的临沂。”(《地狱变》)上述地理和叙事时空的展示表明:一方面,不论是深入中国鲁地和日本北海道,还是聚焦中国南京或是日本东京,房伟巧妙地将蒙太奇叙事方法融入小说之中,很自然地将人物的当下遭遇与其昔日生活交错闪现;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无法认定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能否完全解释和揭示历史真相,但他的确在真实的地理时空中倾力呈现历史史实,最大限度回到了抗战的历史语境。
莫言谈到《红高粱》时说:“我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4]对于房伟而言,他又是如何开启通往“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方便之门”呢?正如《五三》所写的:“每次返乡,我都愿一个人顺着济南老城走走,不为别的,只是重温儿时记忆。”无疑,房伟笔下的抗战历史既是“公众记忆”又带有明显的“个人记忆”。这种“记忆”来源于祖辈和父辈,同时又有个人以及他对抗战历史的材料整合和文学想象。换言之,房伟不仅将抗战历史的“公众记忆”和“个人记忆”恰如其分地融汇于小说之中,而且很好平衡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并以探寻历史隐微的方式找寻到了言说历史和个体的窄门。可以见到的是,房伟抗战小说的立足点并非讲述前线战争场面,而多描绘抗战后方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物命运沉浮,这使得以表现中国抗战为主线的历史叙事得以丰富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读者能够切身体会到抗战的曲折复杂和历史的多样面貌。
二
读到房伟的《猎舌师》,莫言夸赞:“房伟的《猎舌师》抗战系列小说,没有从惯常的历史观念去解读笔下的历史人物,而是专心致志地以个人的感悟来塑造文学形象,把历史的传奇化作了一组战争人物的个体‘心灵史。他写了很多战争中的大人物,也写了不少小人物。他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战争的细腻想象,写出了生命个体在特殊环境下的尊严、伦理和挣扎。”吴义勤肯定:“这十八篇构思奇特的战争小说,诠释了中国青年作家在历史书写领域的强大想象力与探索精神。该作家更像一个历史‘猎魂师:他在历史残骸中打捞灵魂碎片,让那些无主孤魂、漂泊幽灵,在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各自展开言说与救赎。”[1]实际上,不论是莫言说房伟写出了“战争人物的个体‘心灵史”,,还是吴义勤所言的房伟是“在历史残骸中打捞灵魂碎片”的“历史‘猎魂师”,,都指明了房伟抗战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核心价值所在。在我看來,房伟以《猎舌师》为代表的系列抗战小说“胜”在两个方面,即多维人物形象的塑造和隐微历史细节的打捞。
一是以人物塑造来取胜。从《中国野人》开始,那个“独自在雪原生活了13年”的中国野人预示了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将打破以往人物形象塑造的惯例,从而描绘出特殊的人物谱系。在“后记”中,房伟表示他笔下“有大人物,也有八路军战士,国军士兵,还有日本军官,随军僧侣,也有伪军军官,维持会的灰色人物,更有很多大历史下的普通中日民众。这里有英雄、汉奸,也有战俘、逃亡者和普通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是有迹可寻的,如“《中国野人》取材于北海道的中国劳工的原型,《幽灵军》取材于南京大屠杀后失踪的川军部队的故事。《肃魂》取材于肃托事件。《副领事》《起义》《花火》《猎舌师》《鬼子妮》等小说都有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原型”。当然,我们无须探究小说中的人物出处,找寻中国劳工、中国士兵、日本军官等现实人物与“文学形象”某种对应。文学不是“考古”,不能靠“索隐”去感知。更为紧要的是,房伟赋予了小说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别样的内涵和价值,具有了文学史意义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很大程度超越了历史上这些可知可感人物的存在意义。可以直观看到,房伟并未刻意塑造哪种人物形象,而着意于展示抗战历史时空中芸芸众生的生存境遇和命运流转。
在抗战历史的旋涡中,房伟小说中虚虚实实的人物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不论是中国军民,还是日本军官或普通士兵,他们基于各自立场不同程度传达出了反战的态度。从写中国军民来说,《起义》中的师长亲见过军阀混战的惨烈,溃兵劫掠的无耻凶残,为此投笔从戎,希冀军事救国。当日寇侵略,他感到了平生最大耻辱就是“坐看家乡沦陷”。他最大心愿就是杀鬼子报仇,让“屈死的中国人的灵魂”安息,“把这些日本人赶回他们家乡的那些小岛去。”又如,《地狱变》中蒋巽迷茫无奈:“杀人,总是不好的。我只想活下去,做个普通人。”再如,《小太君》中金娣期盼:“如果真有和平,那该多好,日本人和中国人,谁都不欺负谁,大家和和气气,什么事情都商量,像有爱的邻居,那有多好。”这里的鲜明反战态度是从国家民族、正义/非正义或者敌我关系来设置和明确的。
从写日本军民来看,《幽灵军》中长谷川中尉是“国内征召的第三批预备役军人”,他从上海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时战斗早已结束了。虽然他满怀希望来南京寻求“建功立业”,但他始终坚守军人“不滥杀无辜”的操守。从当初雄心壮志到最后失踪于南京麒麟营,他似乎认同了“我们是不可饶恕的魔鬼,或许,还会变成小丑”。长谷川之死实则是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戕害。《副领事》中的副领事劝说自己:“帝国将铭记他的名字,也许会像昭和六年满洲事变前的中村大尉。但铭记又有什么意义?”又如《小太君》中黑木星羽激动得流着泪说:“战争没有出路。”他甚至还在安排的“奴化”演讲时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为祈求和平而来。”再如《七生莲》中鹤田英秋少尉在炮火连天的战场“感到心慌意乱”,他认定:“皇军作战英勇,但茶毒残杀平民的罪孽,却污损了军队的名誉。”尽管小说中写到了森将军、土冢、高岛、本多大佐等日本军官对战争的激昂和狂热,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被卷人战争中的日本军民表现出的焦虑和颓废。这种软弱和消极实质是他们人性未泯一面的真实呈现。如此既传递了反抗战争的态度立场,又揭示了日军在战争问题上的内部矛盾。不可否认,这样两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不仅打破了惯常对抗战历史的认知,而且又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张力。
二是以历史细节和虚构“真实”取胜。在房伟看来,好的历史小说是“力与美”的强力组合,“应是阔大神秘,又真实可感,能将人带人特定历史逻辑和情境,显现历史的荒诞、悲情、无奈,也表达历史的乐观、雍容与想象力”,“这种历史感,又必须是个人化、个性化的,充满生命细节,表达独特审美魅力与价值观。”[5]这些命名为“幽灵抗战系列”的小说正彰显了他“善于处理历史的偶然性、细节性和总体性的关系,善于赋予历史文学的光芒与魅力”。在《猎舌师》这部小说集中,房伟“试图展示一些战争横截面,有的是决定历史的时刻,有的则是普通人的生命瞬间,进而表现战争给民族国家、生命个体带来的创痛,揭示战争背后复杂的人性冲突,探究历史幽微深处的种种可能性”。[2]也就是说,房伟写战争,写抗战历史,注重历史细节。每篇小说所写的抗战本就是一种历史事实,这似乎决定了小说在虚构时必须遵循历史原则。无疑,房伟也正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创作的,我们用两个例子来看房伟的这种历史叙事的特点。
一个是《猎舌师》的结尾写道:“1939年深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举行外务省长清水留三郎招待会,发生震惊中外的厨师投毒案。总领事掘公一、陆军中将山田乙三,还有众多南京城内日本政军界高级人员等数十人中毒。宫下玉石和船山已之作等数人,中毒不治,于次日身亡。”另一个是《副领事》的结尾则是这样写的:“几年后,昭和十二年,即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日方再以失踪士兵为由,炮轰宛平城,中日战争拉开序幕。冬季,大寒,日军攻陷南京,紫金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英勇抵抗,全部殉国,加之无辜群众尸首,数万死体,尸蔽丘陇,骨曝山麓,紫金已成修罗场。后有人收尸于紫金山南灵谷寺前,立‘无主孤魂碑。”在这种历史叙事中,所有虚实人物、事件都和那些历史事实紧密融合在一起了。关于“历史性细节”问题,王彬彬直言:“小说家的方式则应该是微观的、具体的、侧面的。小说家应该善于捕捉历史过程中那种生动、鲜活的细节,通过对这种细节的描绘,表现出总体的时代氛围。”[6]显然,房伟抗战小说中枝枝蔓蔓的细节融合一定程度上丰满了“时代氛围”,同时他敏锐观察到了这种“历史性细节”并巧妙呈现了出来,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历史学家在面对历史事实或事件时本应有的注意之处。因此,房伟的文学细节呈现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為真切、更为深刻地洞察了历史史实,这也使得小说叙事获得了更广阔的延展空间。
三
房伟的抗战系列小说呈现出许多明显不同的面貌,赢得不少作家和批评家的肯定和赞誉。范小青认为:“无论是独辟蹊径的题材,还是法无定法的技巧,无论是印在骨子里的文学品质,还是文字中呈现的精神高度,都十分的惊艳,突破固有的模式,走自己的一家之路,给人以新鲜经验、莫名惊艳以及较强的震撼。”在青年作家文珍看来,“《猎舌师》十数篇小说构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作者有如被叙事之神附体的男巫,攥紧千变万化的水晶球,令观者中魔般深陷其中。除了对战争的控诉,小说的底色是对人性至善至美的追求,还原历史面貌的勇毅,更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罗曼蒂克。”[1]不难发现,透过多样人物的塑造和历史细节的打捞,房伟的抗战小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他的历史担当、战争反思、人性探微。循着房伟向历史深处的探寻历程,我们得以切身参与到接近历史的过程,并由此体察到作家所投射的历史意识和寄予的当下关怀。恰是如此,这些小说不仅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阅读挑战性,而且还赋予小说一种深刻性和普遍性。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其一,房伟的抗战小说注重历史责任的担负和抗战精神的彰显。尽管房伟并不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但他却有着学者、批评家和作家等多重身份。他始终在研究和反思历史、战争、现实、生存、死亡等命题。在短篇小说《五三》中,作为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者米饭铺小老板房吉禄后代的“房伟”出现在了小说之中。这部小说放在小说集《猎舌师》的末篇,有意无意传达了写作者书写抗战历史的目的和深意。小说写道:“我那时还小,有大把时间挥霍,并不知道,记忆在人的心里也会长出雾来。我依稀记得,经四纬三路有块蒋介石题字的石碑,护城河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后立的,铁像是前几年的事。那是南洋华侨林义顺捐款建的,前几年才运回来。从前中山公园还有纪念亭,‘文革后期拆除了。”拆除的纪念碑得以重建了,年少时未曾关心留意的抗战历史终究也在“我”知天命之年时,如同“很多看似遥远的东西,就一下子到了眼前”。如此看来,《五三》中房伟对房家和国家民族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实则是作家房伟立足当下对历史的回应和史事的探寻。正如小说写的“我注定只是一个普通凡人,但凡人有了坚守的意义,也就有了心灵的安顿”。可见,不论是小说中的房伟,还是作家房伟,都表达了铭记抗战的担当和坚守。
房伟的小说尤为注重挖掘中国民众面对战争和死亡时的精神诉求。一方面,这些小说不仅强调战争的个人性,而且突显了群体的参与性和责任感。小说《手肴》借用卜加民的话说:“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讲述抵抗的故事,但历史确实是这样。当日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进犯时,一些中国人在抵抗,更多的人逃离,大多数人留在原地,设法应付所处的环境。”(《秩序的沦陷——抗战时期的江南五城》)房伟既关注到了奔赴前线的军民的英勇抗战,又聚焦了那些饱受战争苦痛、失去家园而生活在沦陷区的普通民众的艰难处境。正如《手肴》中写的:“我还没有死”,但“我无处可去”,“我们要报仇”强调了抵抗侵略是每个人的责任。那些富有特点的“小人物”更是以各类群像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有起义的师长(《起义》)、投毒杀敌的中国厨师(《猎舌师》)、八路军战士(《七生莲》)、根据地民兵连长(《肃魂》)、自发抗战的普通村民(《还乡》),等等。
另一方面,房伟以相当篇幅彰显了战争内在的暖色图景。从传统意义而言,“历史”和“英雄”是两个被捆绑的概念,“历史”总涂满英雄主义色彩,显得悲壮雄浑、震撼人心和可歌可泣。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接受另样的历史观,即历史和英雄无关,只和细民有关。但房伟的抗战小说蕴含着写作者复杂的态度,小说中没有荡气回肠的英雄,却又存在“英雄”。他着墨最多的是平凡的普通人或者说更多是无名英雄。在《手肴》中,面对遭遇日军侮辱而悬梁自尽的表嫂,表哥选择了参加日本人的自治会。但他当“汉奸”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认为:“人总是要死的,我们作为舞台的演员,生逢灭国末世,太过执着喜怒哀乐,应当看透这些东西,为活人多留着‘活下去的机会。这就是大功德。”这种内心矛盾的人物,既有参谋长(《花火》)等中国军民,又有长谷川(《幽灵军》)等日本军官。他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心灵苦楚与情感变化,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反人类性。当然,房伟对战争的反思正是这种“暖色”的最大体现。另外,小说中闪烁的少年兵黑木星羽和中国姑娘金娣(《小太君》)的爱情故事为小说增添了几分暖色,这些色彩使小说多了一份悲悯情怀和人性思考。
其二,房伟的小说深度挖掘了抗战这一特殊环境中人性的真假善恶。房伟笔下的人物是复杂的,但不是英雄的复杂,而是人的复杂,更是人性的复杂。在这里,房伟深人思考时代环境和个体境遇,体现了“至真至爱”的人性关怀,而这种“人性关怀”在表现人性真假善恶中呈现出来。在小说整体创作境界上,统摄《猎舌师》这部小说集的是作家的一种大爱,既是对个体生命和全人类之爱,更是期盼人性的至善。房伟让身处战争中的各色人物来反观战争的残酷,以此显现战争的巨大灾难性。因此,小说处处有向善之意,如《猎舌师》中日本领事馆厨师虎太郎感叹道:“战争是不好的。”而《地狱变》中水清源则痛心:“战起如蝗,尸山血海,再难见无辜之人。说到底,我们都是魔鬼,不过是在乱世挣扎罢了。”可以见到的是,在人性至善统摄下还有着交织的真假善恶。比如,在《还乡》中,“我”从出版的史料中强烈感受到了历史的悲壮,但在黄矜墨的日记中意外发现了其中所隐藏的不能见光的私仇。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显然不是“我一个小记者可以应付的”。如同李奶奶说的:“人都死了,做这些又能有什么意义?”当然,即便是查清楚了,又能够如何?不过,正是这种人性真假善恶的显现,我们才能更真实体悟到各色人物在战争中的境遇、心理和态度,也才能拨开生活的芜杂探寻到更加完整的历史。这些都是当下小说抗战叙事的新质素和新经验。
曹文轩曾指出,新历史小说完成了一项从“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一切历史都是欲望的历史”的颠覆。[7]当然,我们不是说房伟的小说再一次完成了这样的“颠覆”。可以欣喜地看到,房伟小说虽渗透了一种新历史主义态度,但与新历史小说保持了一定距离,从而突破了新历史小说叙事的重围,呈现了鲜活的生命力量。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当下的文学面对“历史”时,要么难以背负重荷,要么出现失重感。在这样一个“负重”和“失重”的文学生态中,房伟以《猎舌师》为代表的抗战小说起到了某种示范意义,它敢于直面抗战的历史,道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给予了历史叙事尤其是抗战叙事循环的新鲜血液。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小说家的审美新质研究”(19ZWC00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9BZW141)和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房伟.猎舌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封底.
[2]房伟.后记:用文学触摸历史的褶皱[A].猎舌师[C].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321.
[3]王尧.序·猎舌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5.
[4]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J].当代作家评论,2002(1).
[5]王峰.房伟:展现南京在大历史中的力与美[N].南京日报,2019年7月12日.
[6]王彬彬.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J].小说评论,2011(1).
[7]曹文轩.重说历史——在真实与虚构之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1).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