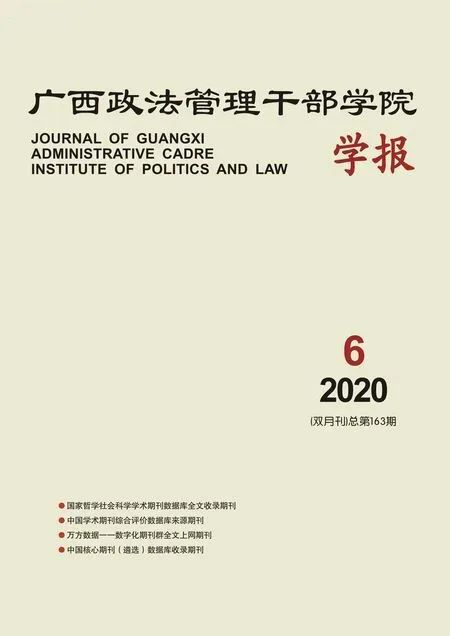防卫过当界限司法判定的三个维度分析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 401120)
正当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身权益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与不法行为对抗的重要法律武器。正当防卫问题一直是刑事司法讨论的热点问题,2020 年9 月3 日两高一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尤其对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予以明确,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指导意见》对防卫过当界限的明晰度及防卫过当司法认定的可操作性。如何有效指导司法者准确、合法地把握正当防卫依旧是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法律实用主义强调法律条文的实际运用。以法律实用主义视角,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分析防卫过当界限,帮助司法者准确判断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过限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期冀通过对A 市B 县的石某某故意伤害案分析,来阐述防卫过当司法判断的界限从而指导司法实践。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石某某系有持刀抢劫罪前科的社会不良青年,平时有随身携带刀具的习惯。2019 年10月3 日晚,石某某的女友吴某某与被害人张某某等人在A 市B 县一家烤鱼店吃夜宵。期间,张某某对吴某某进行搂抱的行为被石某某看见。4 日0 时30分许,石某某来到烤鱼店门口欲带女友吴某某离开,张某某便追至门口叫吴某某继续吃夜宵,并指责石某某对其无礼,借故与石某某发生争吵。期间与张某某一同吃夜宵的被害人冉某某、王某某和姚某某等6 人也来到烤鱼店门口,见张某某与石某某争吵,便开始对石某某拳打脚踢。石某某进行退让,但并未示弱,亦未还击。随后,石某某被张某某、冉某某等人继续追打,石某某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水果刀(非管制刀具)开始反击,并依次将上前对其殴打的冉某某、张某某二人捅伤,后逃离现场。经鉴定:张某某身体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冉某某身体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
二、司法审查分歧意见: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一)一种司法审查意见是嫌疑人石某某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行为人的防卫行为不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给施害人造成重大损害是构成正当防卫的必要性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明显”和“重大”是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罪量要素,也是区分防卫适当与防卫过当的标准。衡量防卫行为限度时必须结合不法侵害的行为性质、行为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进行综合考量。石某某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但其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损害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
首先,石某某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其适用前提是防卫人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暴力犯罪的行为人进行的防卫行为。本案中,石某某的身体健康权虽然正在遭受不法侵害,但对方使用的侵害行为仅仅是拳打脚踢,并未持械,该侵害行为不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因而石某某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
其次,石某某的防卫行为与张某某、冉某某等人的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其理由是:第一,从损害的后果看,石某某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刀具捅刺不法侵害者,造成二人两处重伤的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于“重大损害”;第二,从不法侵害行为看,虽然对方人数众多,但并未使用器械,未进行严重的暴力攻击,石某某身上的伤情只是一些轻微皮外伤,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的程度;第三,从防卫行为使用的工具、致伤的部位及后果综合衡量看,石某某使用带倒钩的单刃刀具,刺伤部位为冉某某、张某某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腹部等)。
最后,石某某有犯罪前科,且平时有携带刀具的不良习惯,系社会上喜欢打架斗殴的不法人员,故对其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后,在社会上宣扬就可能引发一些社会治安案件升级为严重的刑事案件,会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
(二)另一种司法审查意见是嫌疑人石某某的防卫行为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具体来讲:从双方力量对比、行为手段、造成后果等方面分析。其一,从双方力量对比看,张某某一方有7 人,石某某只有1 人,双方年龄相仿,体力差不多。对比而言,石某某明显处于劣势。其二,从行为手段来看,张某某一方7 人都参与了对石某某的拳打脚踢,张某某一方在人数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攻击行为积极。石某某持一把小刀进行还击,且该小刀经公安机关认定,不属于管制刀具。其三,从反击对象来看,石某某用刀刺的对象仅仅限于对其攻击程度最大的人,而不是随意乱刺。石某某有捅刺的行为系出于防卫和规避危险的本能,石某某自然会对攻击度最大的人持刀还击。其四,被害人受伤部位不能成为认定石某某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理由。一方面,对方多人拳打脚踢,场面混乱。石某某在此情境下并不一定能看清还击的部位。另一方面,在场面混乱的情况下不能要求防卫人只伤害不法行为人的非重要部位,否则就是对其过于苛刻的要求。其五,从致伤后果来看,被害人张某某、冉某某两处均属重伤,石某某只受轻微皮外伤,但这不足以证明石某某的行为明显超过正当防卫行为的必要限度。紧急情况下防卫人只有等到施害人的不法行为对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程度损害后果后才能去实施防卫行为的苛刻要求,不符合防卫人及时制止施害人犯罪行为的防卫需要。综上,根据案发起因、力量对比、攻击程度和还击程度、攻击方式和还击方式、当时具体情境等综合判断,不宜认定石某某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故其行为尚在正当防卫限度以内,构成正当防卫。
三、防卫过当界限的司法判断——防卫意识、限度标准与正当性分析
上述分歧意见焦点在石某某的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是司法实践中办理涉及正当防卫案件常见的问题,但是却一直存在处理类似问题的具有共识性的司法认定指引。从2009 年的“邓玉娇案”、2017 年的“于欢案”直至2018 年的“昆山反杀案”,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在努力讨论研究,试图寻找一个可以有效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防卫行为限度的判定本身具有主观性,决定其界限的模糊性与不易量化性,映射到司法实务就会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稳定性。基于此,从有利于指导司法裁判的视角出发,通过结合石某某故意伤害案对防卫行为限度的“意”“形”“神”三个维度,即防卫意识、限度标准与正当性根据的分析,探寻判定正当防卫界限的方法与路径。
(一)防卫意识认定问题:防卫人具有反击和伤害的故意不应否定其防卫意识
防卫人的防卫意识是评判正当防卫的前提,主观正当性决定了防卫人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对防卫人是否具有防卫意识的判定,可以保证防卫人主观维度的正当性。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固然需要满足防卫人主观的正当化条件,即具有防卫意识。关于犯罪嫌疑人石某某面对众人殴打的时候完全没有示弱,且有反击和伤害的故意,是否能够完全阻却他的防卫意识的问题,系本案分歧焦点之一。笔者认为,石某某面对众人殴打的时候完全没有示弱,且有反击和伤害的故意,不应否定其防卫意识的认定及其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从常情常理来看,一般人实施某一行为必然是在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而意识包含着各种想法、思考或者目的等主观因素。在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进行防卫,涉及防卫限度的具体把握问题。我们不能单方面要求防卫人处于此时此景之下仍然保持绝对理性且冷静的状态;相反,我们更应当设身处地考虑防卫人所处的情况进行判断。防卫行为通常是公民的本能应急反应,强求防卫人在惊慌害怕、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实施绝对精准、拿捏有度的防卫,刚好对不法侵害行为予以制止,这不仅要求过高,而且明显违背常理常情,不切实际,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及其要求。“以正对不正”是正当防卫制度的实质属性,表现为“正义行为”对抗“不法侵害”。“邪不压正”是最朴素的社会常理与常情,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合法与妥当,也即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与认定存在模糊与争议之际,应当倾向性地作出有利于防卫人的解释,以此伸张正义。特别是针对防卫人面对突然的、急促的不法侵害,在精神上处于恐慌、紧张,在情绪上处于激愤的状态下,如何认定防卫限度的问题,更应当坚定不移地选择站在有利于防卫人的角度,包容防卫人在此情此景之下无法周全、谨慎地选择相应的防卫手段,从而作出符合法理和情理的判断[1]。其指导思想在于,优先考虑防卫人的立场,对防卫限度予以“包容审慎性”的认定。面对紧迫的不法侵害来临时,强迫一般人实施防卫行为时不能有防卫意识之外的任何想法、目的等,即将正当防卫的防卫意识机械地界定为“单纯制止”不法侵害的主观内容,这不符合常识。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在与被害人张某某争吵时并未示弱、并做好反击的准备,属于防卫人预见到对方可能对其殴打而做好预防不法侵害的想法,属于正当防卫中防卫意识的范畴,而不能因其未示弱、有反击伤害张某某等人想法而否认其防卫意识、否认其防卫的正当性的存在。
从立法目的来看,正当防卫最初的形态是一种私力复仇形式,缘起于人类防卫的本能。近现代以来才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正当防卫作为一项法定化的合法制度。赋予公民自我防卫权,彰显了人性的本能,体现了近现代刑事法治中的“人道主义”精神[2]。法不强人所难,立法者设置“正当防卫”相关条款,无非是想告诉一般民众,当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而不是禁止或命令一般人进行正当防卫。不法侵害中防卫人即使防卫时具有伤害侵害人的故意,也不应当以其主观内容为根据而否认其行为被法律所允许,否则便是主观归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受到众人猛烈的攻击、自身人身安全受到紧迫危险的情况下,意图保护自身安全,而采用持刀反击的方式制止不法侵害,客观上符合立法者设置构成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并未违背立法者的初衷和法律的规定。
因此,面对不法侵害时,防卫人要实施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时一定有意识的支配,即防卫人认识到自己的法益受到了现实不法侵害后,思考如何反击、反抗不法侵害来保护自身安全的意图,故防卫人的防卫意识中必然具有对侵害人一定的伤害故意,不能仅仅根据其存在伤害的故意而否定其具有防卫意识、其实施防卫行为的正当性。
(二)防卫限度标准问题:防卫限度的司法判定应坚持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合理需要作为评判标准
防卫人的防卫行为限度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理论界对防卫限度问题一直存在多种学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必要说、基本相适应说和相当说。必要说认为,防卫人面对不法侵害时,其防卫行为是否超限应以防卫人实施的防卫行为是否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需要为标准,即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3]。基本相适应说认为,判断防卫限度时应将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方式、后果等方面是否基本相适应作为判断标准,司法实务界一般采用此种观点处理案件。相当说认为,防卫人防卫行为必要限度的判断应当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保证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及后果等方面的相当性[4]。不同学说有着各自的观点和立场,对正当防卫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
基本相适应说之前一直对我国司法实践产生着影响。以往司法实践中依据防卫的“手段”和“损害结果”来认定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基本相适应说评判标准,虽然便于司法办案,但是极易导致司法裁判者形成“事后诸葛论”“对等武装论”和“唯结果论”等惯性思维,即以防卫“手段”与侵害行为是否一致、防卫造成的损害后果与侵害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对等来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人为地限缩了正当防卫,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大众面对不法侵害时行使防卫权的积极性。众所周知,发生正当防卫的案件往往都是针对侵害人暴力犯罪而实施的,由于司法机关对防卫行为的认定过于苛刻,导致许多情况下遭受严重暴力侵害的防卫人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可能以防卫过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以至于防卫人遇到不法侵害,为避免造成侵害人重伤、死亡的后果,出现“法”向“不法”让步的不正常现象。
2018 年“昆山反杀”案的发生,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以防卫“手段”和“损害结果”作为认定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评判标准的反思。当前,司法实践存在着明显倾向[5]。以防卫“手段”和“损害结果”来评判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标准,实质上是“唯结果论”,即以结果论正当,要求防卫人应等到暴力犯罪造成一定伤害后果才能实施防卫,忽略不法侵害行为的危险性,更不符合一般人防卫行为的实施。这种评判标准既不符合一般人面对危险时的正常反应、违背人性,也不符合防卫人及时制止施害人实施犯罪行为、阻止施害人犯罪得逞的客观需要,更是人为缩小了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缺失法律的正义性。在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情况下,防卫人没有退避的义务(每个人都有在现场自由活动的权利),因为“正当没有必要向不正当让步”。故此,当前司法实践中再以防卫的“手段”和“损害结果”来评判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标准,已不符合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时代要求。
“昆山反杀”案中,司法机关对防卫人于海明“反杀”行为作正当防卫的认定,基本采用了相当说的观点,确立了必要限度的认定应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合理需要作为评判的标准[6]。这种评判标准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能机械地理解“明显”这一罪量要素。司法实践中,往往过分要求防卫人的防卫手段要与施害人的犯罪行为在暴力程度上相适应。如不法侵害人在对防卫攻击时并未使用刀具等凶器,而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使用了刀具反制施害人并对施害人的人身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害,此时不因防卫人使用刀具反击就机械的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明显”罪量要素,不仅仅需要防卫手段的比较、还包括力量对比、人数对比等等多方面的判断。二是不能机械地理解“重大”这一罪量要素。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时,需要衡量防卫行为给施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与施害人对其造成损害后果的轻重,来判断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符合“重大”罪量要素。这种比较不仅需要衡量现实的后果,更要衡量施害人不法侵害行为对防卫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如本案犯罪嫌疑人石某某虽然将侵害人捅刺成重伤而自身并未被打伤或打成重伤,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被侵害方众人殴打时生命和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危险。结合本案,石某某面对众人对其猛烈的拳打脚踢,自身健康和生命安全被严重侵害,而石某某只身一人要想制止被害人张某某等7人对其身体的伤害,赤手空拳反击众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持刀反击方可击退对方,保护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从视频证实也的确如此,被害人冉某某、张某某和王某某被捅伤后均停止了对石某某的殴打。因此,石某某的防卫行为符合制止不法侵害、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合理需要,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
防卫行为限度标准是判定防卫人防卫行为适度性问题,明确判定限度标准可以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操作性,确保司法裁判的准确性与公正性。因此,正当防卫应当改变以往的以防卫“手段”和“损害结果”作为评判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标准,而应采用防卫人制止施害人不法侵害和保护合法利益的合理需要作为评判防卫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
(三)防卫正当性根据问题:法秩序维护应当纳入正当防卫案件司法裁判考量的内容
正当防卫作为合法行为,原因在于其防卫行为具有正当性根据,而正当性根据为何的问题,理论界尚未形成共识。目前理论界认为防卫行为的正当性根据有二:一是从人道主义精神的角度来说,正当防卫的实质是防卫人私力复仇行为的“合法化”,即立法者在尊重一般人反抗不法侵害的人性而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将私力复仇行为予以法律保护,体现了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公民合法权益天然地受到国家的保护,然而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犯罪率的上升,国家难以实际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此时,国家需要通过制定法律将面对不法侵害的公民进行私力救济的防卫行为范围予以拓展,鼓励公民行使防卫权,对抗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防卫行为的正当性根据,实质是立法者将一般人朴素的思想和对规则的认识予以法治化,从而确保一种稳定、平和的社会状态,即维护良好的法秩序。因此,从防卫行为的正当性根据中可以推断出正当防卫具有法秩序维护的功能。
从有效维护法秩序的角度来看,正当防卫具有法秩序维护的功能,即立法者通过法律赋予防卫人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防卫行为制止当前的不法侵害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吓阻潜在的不法侵害人、增强国民对法秩序信赖的效果。因此,司法者在办理正当防卫案件时,应当将防卫人的防卫行为是否有效地维护了法秩序这一要素,纳入正当防卫案件裁判的考量内容中。具体到本案中,有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具有犯罪前科、且平时有携带刀具的不良习惯,被定性为社会上喜欢打架斗殴的不良人员,故对其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后在社会上宣扬,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社会治安案件升级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可能会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于法无据、与现实不符,更与时代民众的要求和认知不符。正当防卫是法律确证的公民在公权力保护不能及时到达情况下的一种私力救济权。在认定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问题上,要清醒地认识到防卫是经国家确认通过法律授予公民的权利,从而使其在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实施防卫保全自己。这种立法是对刑法人本主义的积极体现。
首先,在面临紧迫的不法侵害时没有退避的义务是一般民众的基本认知,正如面对无端无理的霸凌、侮辱时,有尊严的人都会奋起反击。“正当没有必要向不正当让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和理解,也正是立法者将正当防卫规定在刑法中的目的。防卫人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如果处于慌乱、恐吓或者惊吓的状态,就不能期待他不超过防卫限度[7]。防卫人不是先知,而是普通人,不可能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做出百分之百的准确预测。而事后的判断视角则恰恰脱离了防卫人(一般人)对防卫行为发生时具体情形的可能认识,动辄就认定防卫行为构成防卫过当,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让防卫人承担过多的风险,易使防卫人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无端忍受不法侵害,要么因反击构成防卫过当而面临违法犯罪的高度风险,同时也会降低不法侵害人的违法成本,助长潜在不法侵害人的嚣张气焰,这在一般预防和刑事政策上都是不应该的[8]。
其次,本案石某某系社会不良人员,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不能否定其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重要原则和维护的重要法律价值,要求司法者对每一个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试想,如果犯罪嫌疑人石某某系遵纪守法的公民、劳动模范或公务人员,是否会对其认定为正当防卫,当然应该认定,但认定的原因不在于其身份为何,而在于其行为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昆山反杀”案,纠正了以往司法实务对正当防卫问题的评判,已然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即“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秩序理念,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的要求。同时,如果真出现有不法分子借“正当防卫之名”行“不法侵害之事”,仍然可以依法予以打击,因为滥用正当防卫权利而实施不法行为,可能因阻却事由而予以否定,依然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后,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多方面措施予以解决,而不应苛求某一部法律、某一条法文来解决。社会上不良人经常在酒后发生像本案这种打架斗殴的案件,这类案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石某某案具有典型性,典型在于防卫人虽系具有前科劣迹的不良人,但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知晓自己行为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而侵害人相对来说缺少法律意识,预见不到自身行为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恰恰反映出司法人员需要深入到社区、学校等去做更多的法制教育和宣传,通过案件办理实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效果。
对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根据问题的探讨,可以从根基上奠定对正当防卫案件司法判定的方向、避免走向极端,确保司法裁判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故此,犯罪嫌疑人石某某构成正当防卫,符合法律规定,符合社会大众的一般认知。对其防卫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可以警示社会不法分子,一旦实施对他人侵害,被反击而受到损害时是无法获得刑法保护的。此案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犯罪、有效维护法律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彰显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价值。
四、结语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的规定旨在鼓励公民反抗不法侵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受静态的利益衡量影响,与立法目的背道而驰[9]。防卫过当应从防卫人防卫行为动态发展的角度去评判,防卫人的防卫意识是评判正当防卫的“意”,主观正当性决定了防卫人防卫行为的正当性,对防卫人是否具有防卫意识的判定,可以保证防卫人主观维度的正当性;防卫行为限度标准是判定正当防卫的“形”,明确判定限度标准可以提高司法裁判的操作性,确保司法裁判的准确性与公正性;而对正当防卫的正当性根据问题的探讨,是判定正当防卫的“神”,可以从根基上奠定对正当防卫案件司法裁判的方向、避免走向极端,确保司法裁判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把握住正当防卫案件的“意”“形”“神”,才能保证刑事案件司法认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