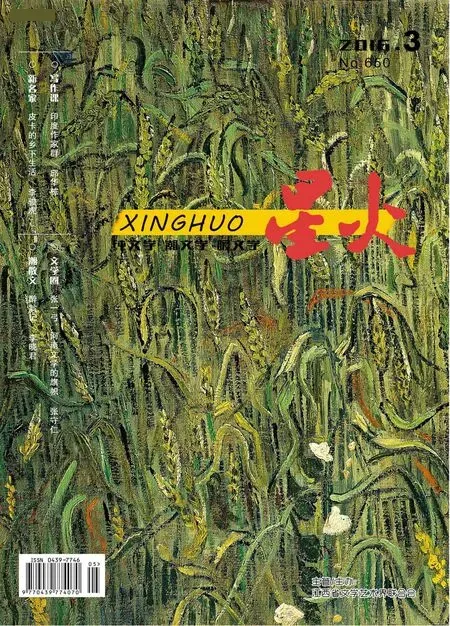天黑请闭眼
彭臻华
1
欣蕾躺在床上,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望向天花板。尽管关了灯,微弱而苍白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显得房间里更冷清了。都快零点了,庆伟还没回来。已经连续十四天,欣蕾不知道庆伟在晚上哪个点回到家的。
她只知道,有一天,他是凌晨五点回来的。凌晨三点半时,欣蕾上卫生间,习惯性地看了看门口的鞋。每天晚上睡前,她都会把庆伟的拖鞋在门口摆好,把门道里的灯开着,这样,他回来就能很方便地进门和换鞋。可是,那天凌晨,她看到拖鞋仍然照原样摆着。她就知道,他没有回来。这么晚了,他会去哪呢?
庆伟对她说过,如果晚回,他只是和他的麻友玩牌去了。找女人,他是不会的。他说他知道啥能干啥不能干,尽管现在这社会,在外面彩旗飘飘的男人多的是,红旗飘飘还被认为是有本事,但他看不上那种男人。
就找女人这一点,欣蕾还是相信他不会。凭自己对他多年的了解,他是一个保守的男人,一个洁身自爱的男人,还是一个自认为忠贞的男人。不过,遇上这样的凌晨,他没有回,欣蕾就会怀疑自己的判断——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仅仅是打牌,能每天晚上乐此不疲吗?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在那方面是有需求的,而他们已经分房睡五年了。两人每月也会亲热那么一两次,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相隔太久,每次都是她的情绪刚刚上来,他就完事了。每次都是那么草草了事,她就觉得意兴阑珊。不过,每次她都装得很好,她不想败庆伟的兴,不想让庆伟觉得自己不行。她知道,男人最怕被自己的女人说不行。
这样一想,欣蕾心里某个角落就会尖锐地痛一下。她拿起手机,想给他打电话,想想还是放弃了。她很快钻进被子,对自己说:还是睡吧。
他到底在哪里,就算知道,她又能怎么样呢?叫他回家吗?以前不是没这样做过,可每次引发的要么是两人在电话里大吵,要么就是他回家之后的大吵,或者是两人之间的冷战。这么多年下来,她对他们的感情,有深深的无力之感。
那天的下半夜,欣蕾是半睡半醒度过的,到五点时,听到庆伟开门的声音,欣蕾闭着眼睛装做熟睡的样子。天亮之后,她洗漱上班,之后她也没跟他提这件事。说她生气,好像也没有特别生气。到了这么个尴尬的年龄,经历了这么多的争吵,她已经懂得,生气就是伤害自己。她不想伤害自己,她想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要说完全不在意嘛,好像也不是,每每想起来,总觉得心里有根刺似的。
欣蕾觉得自己是很能开导自己的。人到中年的夫妻,也许多半如此吧,有一点悲凉,有一点无奈,有一些不甘,又难以挣脱和离开。毕竟结婚几十年,两人已习惯了彼此,不想再折腾,更不想再去习惯另一个人。生活有时候就是如此,将就着过,反正过着过着就老了,一辈子也就那样了。
2
夜晚,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人的耳朵就会异常的敏锐。此时,欣蕾的耳朵正是如此,捕捉着门外的一切声音:路上车辆驶过的声音、楼下那个麻将房哗哗洗麻将的声音和麻客们高声争执的声音、对门黄好夫妻俩上楼的声音……从脚步声,欣蕾就能判断,黄好走前面,她老公邱林走后面,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总是先响起。
“今晚这样的折腾,是甭想睡得着了。那个傻B 闹啥,没一点自己的主见,全是听她哥的!”黄好愤愤不平。
“你着急也没有用,她要离也没办法。不过,再劝劝她看在孩子的面上能不能不离。”邱林劝慰他老婆。
“真够呛!”欣蕾想,他们夫妻俩肯定是刚从老娘家回来,去当和事佬了,估计又是黄好的弟弟和弟媳妇闹腾了。
有一天,欣蕾去扔垃圾的时候,在楼道里碰到黄好,出于礼貌,她笑着打了个招呼。没想到黄好站住了,和她拉起了家常。其实欣蕾不太想听,黄好说的不是这个男人养了小三,就是那个女人在外面有了男人。欣蕾不喜欢听这些八卦,这些负面的东西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心情。
这一次,黄好说的是她弟媳妇与她弟闹离婚的事。说她弟媳妇太愚蠢了,什么都听她哥的。小事还算了,现在她连儿子都不管了,今天下午把读大班的儿子扔到她父母家就走了,说必须离婚,说他们家是骗婚,必须还她一个公道,否则只有法庭见。
原来,前段时间,黄好的弟弟黄佳霖在超市做保安好好的,因为和一个顾客争吵被投诉,老板把他给开了。一个人关在家久了,琢磨来琢磨去,把婚前的抑郁症和被害狂想症给复发了,动不动就对老婆说屋里有人拿着刀要杀他。一会儿又在屋里大喊大叫,说要去把超市给砸了,让那些人知道他的厉害。
黄好的爸爸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含含糊糊地对儿媳妇说了儿子以前的病情。黄好的弟媳妇听了号啕大哭,哭自己的命苦,骂他们骗婚,说终于知道为啥黄佳霖到哪做事都做不长,原来是有神经病!
黄好的爸爸辩解说不是神经病,她一口咬定就是神经病。当夜,她就哭着回娘家了。
第二天,她哥嫂陪着她回来收拾衣物,说要离婚,她不可能再跟一个神经病生活,太可怕了。因为他们家骗了她,所以他们家必须给她青春赔偿费,还有房子必须转为她的儿子所有,由她带儿子在里面住,儿子成年后,房子归儿子。
要离婚就算了,还提这么多要求。黄好的父母当然不会同意。儿子是她生的,她不心疼拉倒,爱带不带。再说了,她说什么带儿子,还不是要骗房子,她才三十三岁,以后肯定要嫁人,不可能带着儿子这个拖油瓶的。
黄好对欣蕾说她弟媳妇好蠢,放着好日子不过。她爸妈就一个儿子,有两套房子,以后还不都是她的。说她弟弟哪是精神病,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大造成的暂时心理失衡,到医院调理一下就会恢复,哪有她说的那么严重。而且她弟弟特别疼老婆,就算现在她要和他离婚,他还说她好,说她想离就离,她想要房子就给她好了。黄好和她爸妈当然骂他猪脑壳。
欣蕾倒觉得她弟媳妇精明,离婚,摆脱负担,又不贪心,只想一套房子。不过欣蕾没说出来。
黄好说她天天为着娘家的事操碎了心,天天晚上睡不着,数一千只羊都没用,她一定是患上失眠症了。
3
楼道里很黑,庆伟借着手机的光找到锁孔,轻手轻脚开了门。这个点,他知道,老婆孩子肯定早睡了。门道的灯亮着,拖鞋是朝里摆好的,他只要一抬脚就能穿上。他知道是老婆欣蕾怕他进家门时看不见,特意留的灯。老婆是个贤惠的人,顾家,爱孩子,在单位求上进,连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
庆伟却总觉得他们之间隔着啥,到底是啥,也说不清。好像老婆对那方面没什么需求,也就是性冷淡。可庆伟是个正常的男人,他是有那个需求的,看着老婆那个丰臀细腰,他就想要。偏偏庆伟不想勉强,这种事情,得两厢情愿,才能两情相悦,否则剃头担子——一头热,可没意思。
为了分散注意力,庆伟就看电视,看着看着,思绪就跟着电视剧情走了,下面就软了,他也就不想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哪知老婆抗议,说他电视总是播放到天亮,费电费钱不说,还有辐射。又说那声音吵得她没法睡觉。庆伟干脆把声音关了,她还是不罢不休,说那些光波一闪一闪的,扰得她根本睡不了。
庆伟只好把电视给关了。没有电视,他在床上摊大饼,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已经有了睡前电视依赖症,没有电视的声音,他就觉得不对头;这么多年,他只要一回家,就打开电视机,让家里充满电视机的声音,他才安心。他从来没有觉得不妥,现在要他关了电视睡觉,他才觉得大大不妥。可是没办法,老婆白天要上班,在西药房发药,可马虎不得,万一发错了药,那是要死人的。他看到老婆的黑眼圈,也确实心疼。
关了电视,房间里安静下来,老婆慢慢睡着了。听着老婆匀称的呼吸,庆伟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侧过身子背对老婆,打开手机,找出下载的视频,把声音调到最小,侧着脖子看了起来,也不知什么点了,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发现自己渐渐地越来越难入睡了,准确地说,他失眠了。
有一天早晨,庆伟是痛醒的,他的脖子久侧一边,落枕了。欣蕾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心疼地说:“你以后还是开电视吧,不要躺着看手机了,脖子受不了,眼睛也受不了。”
于是,从那晚以后,庆伟又开始开着电视睡了,一边看一边睡。欣蕾用手挡着眼睛,把脸藏到被子里去,可那一闪一闪的光、那响在耳边的声音,让她怎么也睡不着。欣蕾失眠了。欣蕾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有一夜,她抱了被子,到靠近楼道的那个客房里睡,没有了电视的干扰,她想她会睡得很好。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如此。可是后来,她总是半夜会醒几次,然后就会习惯性地去门口看看拖鞋,看看他回来了吗?她发现他越来越晚回家了,渐渐地,她患上了失眠症,她的黑眼圈又重了起来。
4
庆伟说:我也失眠,要不失眠,我干吗那么晚回来?!这失眠也不是啥大事,失眠的人多了去了,白天补补觉呀。
庆伟自己当老板,只要乐意,可以直接从午饭后睡到第二天早晨。可欣蕾不行,白天要上班,晚上得陪孩子写作业,十点完事算早的,有时得到十点半。有一夜,孩子写到十一点半,老师说上课纪律差,全班罚抄。孩子写着写着歪在桌上睡着了,她却睡意全无,拿过孩子的作业本抄了起来。第二天自然又是黑眼圈,又是头晕眼花、头重脚轻。
失眠绝对是病,欣蕾觉得必须得治。怎么治?她想还是自我解决下。她上网查询如何解决失眠。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失眠有那么多名堂,分什么抑郁失眠、焦虑失眠、神经衰弱失眠等。失眠按病因可划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
网友建议自我调整,睡前泡脚、冥想、背唐诗……欣蕾试了一个又一个方法,所有的方法均宣告失败。欣蕾决定还是求助医生。
看中医吧,中药副作用小。那个杨医生是个负责的医生,他先详细给欣蕾列出失眠的种种原因,然后一一给她排除,说这样便于对症下药。
一是外在环境因素,如光线、声音、湿度以及环境给人的安全度等因素的变化。
二是内在因素,主要为社会心理和自身素质因素,如受到较大心理刺激,或处于过分焦虑状态,或有家族遗传倾向。
三是疾病因素,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症,躯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帕金森等。
四是药物因素,如精神科药物和某些内科药物。
五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睡前喝刺激性饮料、兴奋性保健饮料,吃高脂类、烟熏、烤制类食物或睡前大量运动、玩手机、玩电脑。
好像这五点欣蕾都靠不上。她单独睡客房,睡前只喝白开水,不爱运动,睡前不用电脑,偶尔玩手机。
杨医生听了她的陈述,颇为怪异地看了她一眼。
“什么原因都靠不上,那为啥失眠?”
“我也不知道啊,越睡不着,越想快点睡着,就越睡不着。”她好像说绕口令,想起对着天花板张大眼睛的黑夜像个黑洞要把她吞没,她就心烦意乱。女人睡眠不好老得快,这是谁都知道的。欣蕾不求大富大贵,只想每天晚上好好睡一觉,她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睡到半夜醒几次;要不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梦,不是没赶上火车,就是上班迟到,不是找不到卫生间,就是把钱包给掉了,或者去工作现场,忘记带笔记本了……总之没一个梦是好的。
第二天自然是头痛、头晕、心慌、脚软、想吐。所以她想吃药,彻底把失眠治好。
杨医生说她是神经衰弱,想得太多。给她开了五包中药,说调整一个疗程,就没什么问题了。还交待她水煎三次,然后混合,兑阿胶一起喝才有效。
欣蕾像小学生一样,拿了手机一点一点全写进备忘里,回家后认真按医生的要求煎服。五包药吃完了,效果却并不明显,她还是失眠。
5
这一夜,庆伟到天亮都没有回来。欣蕾也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早晨起来脑袋里好像有一万只苍蝇在飞,脚下像踩了棉花。她煮了饺子让儿子吃,自己一只也没有吃。心里想着:这天杀的,又死到哪儿去了?越来越不把我当回事儿,这个家连旅馆都不算了;住旅馆还要登记下,这倒好,他回不回,连个电话也没有。
欣蕾想打电话给他,按了一半号码又放弃了。她想吵架,又觉得特没劲。她送完儿子到学校,再赶到护士站已是踩着点了。欣蕾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工作几十年也是做腻了,做油了。四十岁前她工作尽心尽力,原以为守了这么多年,护士长早晚是她的,领导也透露了这个意思,大家也都以为是她,最后却是后她五年进医院的院长的远房表妹成了护士长。这件事后,她啥也不想了,就想好好培养孩子,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现在看来庆伟连这个小日子也不想和她好好过了。当她这样想时,心里特别窝火。
“欣蕾,昨夜又没睡好吧?看你这黑眼圈都赛过熊猫了。”交接班时好姐妹小卫贴心地问她,并咬着她的耳朵说:“我听我家的说,昨天上午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看到你家庆伟的车了,副驾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妖得很,你可上点心,别任他在外面胡作非为。”
“不会的,庆伟不好那个,他就好打牌。”欣蕾一边配药一边回道,心里却“咯噔”了一下:三十来岁的女人?谁?公司那个财务?办公室那个秘书?……整个上午,这个疑问都在欣蕾的脑子里绕: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欣蕾打算晚上等庆伟回来问问,要不堵在心里难受。
可是,晚上,庆伟没有回来。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欣蕾听到庆伟开门的声音,她“噌”地坐了起来,伸手抄过一只拖鞋就朝门口砸了过去。
“你说你死到哪个野女人那去了?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你要有本事,你别回来!”
“一大早的,你发什么疯啊,跟个泼妇似的,我不被大刘拉着打牌不让走嘛!三缺一,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信你个鬼!打牌打牌,鬼晓得你打到哪个野女人床上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欣蕾彻底爆发了,简直像个母狮子。
6
“是我错了,欣蕾你别这样,你别把孩子给吓着了。”欣蕾的样子把庆伟吓着了,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再说他也确实两天两夜没回家,好像有点过了。不过,他的确是被大刘他们拉着打牌,看时间太晚了,他们说别回了,将就着几个小时就天亮了,所以他就真的没回。
他是想,这么晚,回了也是吵醒母子俩,再说了,回去也是他一个人的冷被窝,还要被大刘他们嘲笑怕老婆,何况进进出出的,欣蕾好像也不管不问,就当没他这个人似的。哪知欣蕾这次像吃了枪药,发了疯,甚至还拿拖鞋砸他,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庆伟走过去,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双手把欣蕾揽进了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说:“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改还不成吗?”
欣蕾开始还挣脱,后来委屈地哭了。庆伟抱得更紧,后来干脆抱到了床上,一边撕扯着把她的睡衣给脱了,一边说:“你说你老不跟我睡,我回来跟不回来有啥差别啊,像个没老婆的男人。”
欣蕾想一脚蹬开他,又想,不对,如果他在外面真的有女人了,哪能这么猴急呢?就任由他手脚并用,满脸乱啃了。
完事了,欣蕾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人家说看到你车里带着别的女人,长本事了?想在外面彩旗飘飘了?”
“借我个胆也不敢呀,媳妇你别听他们瞎咬舌头,再说,你也知道,我不好这个,要好这个,早几年就有了,你知道,又不是没有女人喜欢我,可我心里只有你。”庆伟说得挺溜,这话,欣蕾爱听,她是个耳根子软的女人。
这事就这样翻过。吃过早饭,欣蕾要送儿子去上绘画课,庆伟去公司,出了门各忙各的。好像风平浪静了。
但事情过去半个月了,欣蕾还是时不时在心里把庆伟所有认识的女人排了个队,包括他的女同学。特别是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什么不堪的画面都涌上脑子。
到底是哪个女人坐在他的副驾呢?到底是谁呢?
这个问题让欣蕾快疯了,只要庆伟在家,她就忍不住问。她想要一个答案。庆伟一口咬定纯属乌有,不信可以去查监控。再问就骂她是不是神经了,老揪着不放。
这事,成了欣蕾心里的一根刺,不时冒出来刺她一下,不见血,但是痛,是那种抓不着的隐痛,如牙痛,分不清是哪颗牙坏了的痛。
欣蕾的失眠更严重了,有时整夜睡不着觉,白天精神恍惚,她真怕自己上班时会拿错药,那可是关乎人命的事。
周四,吃过早饭后,欣蕾照例先送儿子去学校。在环城路转弯处,她一个恍惚,睁眼看到自己的车奔一辆货车而去。她紧急刹车,却踩成了油门,等她醒来,只剩一条腿,好在儿子有惊无险。她痛不欲生,都怪失眠闹的。
六个月后,庆伟坚决地提出离婚,自愿净身出户,保险公司赔的钱全部留给她和儿子,也算仁义至尽了。离婚的理由是夫妻志趣不一,情感淡薄,无法共同生活。真正的原因是庆伟只要和她在一起,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开电视也无效。
欣蕾欲哭无泪。
7
吃晚饭的时候,欣蕾的弟弟欣迪来找她,愁眉苦脸,很憔悴,二十五岁的人皱着眉像个小老头。欣蕾心疼地看着他,尽管两人相差十岁,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毕竟一母所生,心血相连。
“怎么回事啊,这么没精打采的?一点都不像快结婚的人。”
“碰上难处了,夜里睡不着。”欣迪挠挠头,为难地说。
“难怪,原来是没睡好。”欣蕾说。
“姐,我也知道你的难处,我也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我不应该来找你,可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他期期艾艾地说,“我和王丽莹不是说好这月六号定亲,五一结婚么?昨天她妈又提要求了,原来说好礼金十万元,再加上‘五金’近三万元,还有其他的各类开销,差不多十五万,另外还得准备十五万装修房子。可她家昨天说还得买一辆车,说结婚以后,我们回她家方便,上班也方便。这一时半会,我往哪搞买车的钱呀,少说也得十来万,可愁死我了。”他把拿在手里的水杯放在茶几上,一口水也没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什么方便,还不是装排场!现在借这么多钱,以后结婚还不是你们俩还,有意思么?”欣蕾一听就着急了。她知道弟弟刚参加工作没两年,本来没打算这么早结婚,想先拼两年事业再说。可王丽莹说要不结婚,要不分手。还说是她妈说的,她妈说女孩子可耗不起。
欣蕾的父亲在乡村医院当医生,母亲是个小学教师,真没什么钱,这十万礼金就把他们给愁坏了。她妈每次看到欣蕾就说:“这女孩子现在这么值钱?你以前才收多少礼金啊,就嫁给他了!”
以前,以前她是个傻白甜,相信爱情可以打败柴米油盐,老妈说要三万元礼金,伟庆说手里真没有,她还偷偷拿了一万元钱给他。现在的女孩子现实得很,要高富帅,要有房有车收入高,还要暖心,懂情调会做饭。这些都是欣迪告诉她的。
“为了个排场,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值吗?”
“这不头大吗?不是我要,是对方要。说没车不结婚。”
“不结就不结,还愁找不到老婆咋的?何况你年纪又不大,再玩几年正好。”
“我们都谈三年多了,她可是我在大学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追到的,我可不想鸡飞蛋打。”
“好吧,你就是给她迷住了,为了你买房还有装修,老爹老娘可是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以后日子过成咋样还不知道。”
“都到这份上了,我也没办法。”
“好吧,要多少,你说吧。”欣蕾深深地叹了口气,眼泪就涌上来了。离婚都过去快一年了,她还是无法走出来。
今夜,她和弟弟终又是失眠之人。庆伟呢?他现在睡得好么?她脑子里突然跳出一句话:天黑请闭眼。
天黑请闭眼是个网游,欣蕾不会玩,但欣蕾喜欢这五个字,天黑了就闭眼,好好睡觉,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用想,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