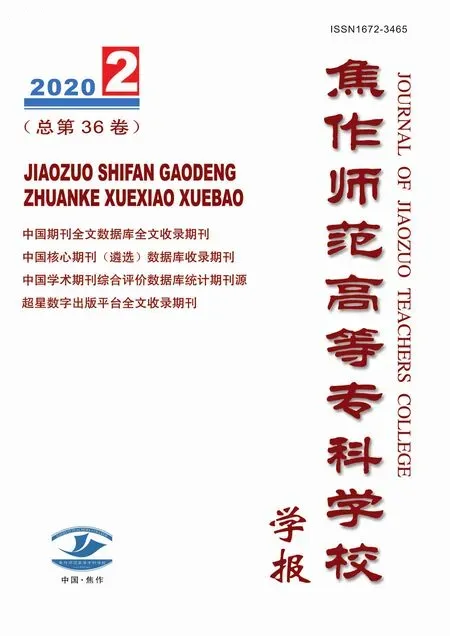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个性化特色论析
王绍凯
(1.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89;2.河南大学 濮阳工学院,河南 濮阳 457000)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史上,郭沫若无疑影响巨大,关于其治史特色的论述也并不鲜见。比如赵典曾论述郭沫若诸子研究中“人民本位”的史学特点,认为“有其合理性”,但“各种思想的产生都是多元的,只用一个标准去衡量,用一种视角去管窥,都是看不全面的”[1];周文玖认为“郭沫若研究历史的特点是不断创新,不断追求”[2],“他重史料,尊重考据学”,“具有‘以情智交融之文笔,传古老历史神韵’的历史写作风格”[3];还有更多的则是论述郭沫若史学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等。现在看来,作为对其最具个性化特色的描述,现有论述显然仍欠准确,因而仍有必要加以审视解析。
一、生物医学视角:史学研究获得新思路
在论述郭沫若校释特色时,黄烈认为其“除运用传统学术外,还博采现代科学知识以求新释”[4],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5]465——赴日留学所受西式教育,无疑助力郭沫若形成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无疑是新鲜的。
以医学生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时常出现于郭沫若史学研究实践中,且屡有创获,可算是郭沫若史学研究一大特色。在《驳〈说儒〉》一文中,他说到“三年之丧”的问题,有人依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记载而断定殷代已行三年之丧之制,郭沫若却借助医学知识给以新的考查和解释——
健康的人要“三年不言”,那实在是办不到的事,但在某种情态上是有这个现象的。这种病态,在近代的医学上称之谓“不言症”(Aphasie),为例并不稀罕。据我看来,殷高宗实在是害了这种毛病的。所谓“谅阴”或“谅闇”大约就是这种病症的古名。阴同闇是假借为瘖,口不能言谓之瘖,闇与瘖同从音声,阴与瘖同在侵部,《文选·思玄赋》,“经重瘖乎寂寞兮”,旧注,“瘖古阴字”,可见两字后人都还通用。这几个字的古音,如用罗马字来音出,通是am,当然是可以通用的。亮和谅,虽然不好强解,大约也就是明确、真正的意思吧。那是说高宗的哑,并不是假装的。得到了这样的解释,我相信比较起古时的“宅忧”、“倚庐”的那些解释要正确得多。
……“不言症”的病理……据说是大脑皮质上的左侧的言语中枢受了障碍。有时是有实质上的变化,如象肿疡外伤等;有时却也没有,没有的自然是容易好的。殷高宗的不言症,大约是没有实质变化的一种,因为他是没有受手术而自然痊愈了的。
殷高宗的“谅阴”既是不言症而非倚庐守制,那么三年之丧乃殷制的唯一的根据便失掉了。
(追记)殷高宗曾患不言症,卜辞中已有直接证明。武丁时卜辞每多“今夕王言”,或“今夕王迺言”之卜,往时不明其意者,今已涣然冰释。[6]439-440
不管郭沫若这种解读逻辑能不能最终经得住历史检验,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还相当有说服力的、“科学化”的解释,而这对“三年之丧”问题的研究又相当关键,所以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索,而这显然受益于其医学专业之学养。同样的阐释视角应用于古代史研究,还可以举出几例——
他的悲伤忧郁,长久不能去怀,精神和身体都不能不受损害。他似乎是有失眠症的人……还有身体上也确实有痛苦……这大约是神经痛,不然便是肋膜炎。至于他有心悸亢进的征候,在他的诗里是屡见不一见的。再说《离骚》那种诗形,《九章》的大部分也是同样,是有点“印版语”(Settertyped expression)的倾向的,这也是精神多少有些异状时的常见征候。[7]104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应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根据课程目标,精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学习内容,变革学习方式,使全体学生都获得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语文素养。
——《屈原研究》
万宝常患的究竟是什么病虽然无由确知,但既说是“卧疾”,当然不是外伤;既说是“饿而死”,当然不是病的胃肠。病到将死还可以起来烧书,而意识也很清明,当然不是瘟热和癫狂。我揣想他的病怕是属于呼吸系统的,或者怕就是肺结核吧。[7]141
——《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
其实死于牛酒,并不是不可能。不过不是“饫死”,或“饱饫而死”,而是由于中毒。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二十四小时至二十八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加以又有白酒促进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而杜甫的身体本来是在半身不遂的状况中,他还有糖尿病和肺病,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杜甫死于牛酒,既见诸史籍,又可以用腐肉中毒被酒所促进而加以科学的说明,怎么能够同样斥为“荒诞无稽”呢?
要之,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7]436
——《杜甫嗜酒终身》
其它还如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文中,从《史记·本纪》对秦始皇的记载中,推理得出秦始皇患有软骨病、气管炎等疾病,进而推导出秦始皇幼时一定受人轻视,进而发展为后来残忍的性格;在《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中,对于导致李白去世的病因的症候式分析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案例显示出一个学医出身的史学研究者的特色,且表明适当运用这一方法的确可以为史学上的一些断案找到些合乎道理的解释,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突破口,这是不容一概抹煞的。而从根本上看,郭沫若的这一研究选择也自有其学理必然性:“唯物史观对现实人的活动做了实证性的表达,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需要回到现实存在的物质资料及其生产方式中去找答案,也内在要求了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8]但我们也要说任何方法也都有它的局限,毕竟时过境迁,即便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也仍然免不了主观推断的成分,故万不可据以自蔽,走向另一个极端而绝对化。比如像上面一番分析之后即断言“要之,杜甫死于牛酒是毫无可疑的”无疑并不合适,因为下这个断言的前提是“聂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而并无证据证明这个前提是确实存在的,它只是一个推测而已——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做出绝对的判断,焉足信服?所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也要密切结合事实分析,否则便失去了这一方法的意义和价值。
二、文本细读法:新识见乃是源自旧材料
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中倡导的一种方法,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中却已经可以寻觅到它的些许影踪。通过细读文本——古文献资料,郭沫若跳出成见,发前人所未发,得到了一些独到的研究发现。事实证明,推进古代史的研究,不仅可以靠新史料的发掘,而且也可以从对已有史料的细致整理解读中获得新认识。
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象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着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他们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6]335
“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确实是一个细心的发现,并且得到这一发现居然只是依靠已有文献资料即可以做到,这让人不能不信服郭沫若文本细读的功夫。同样,运用这一有效方法,郭沫若也对《载芟》这首诗进行了新的解读,得到了新的认识——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
……(二)从事耕作的人有主(即王)有伯,有大夫士的亚旅,有年富力强者(“强”),有年纪老弱者(“以”),全国上下都是在参加的。——“以”与“强”为对文,应当读为骏或骀,即是不强的人。《传》、《笺》均当作雇佣讲,那可讲不通,被雇佣者力当强,何以乃别出于“强”之外而成对立呢?当时假如已经能有雇佣存在,主伯亚旅何以还要亲自参加呢?因此我的讲法有些不同。[6]410
又如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谈到井田制的变革,郭沫若通过对《论语》中一段旧有资料的重新思考和仔细分析,终于把“难以索解”、恒被误解的文献变成为论证井田制变革的关键文献资料,这也是借助文本细读法。所以,对于史学研究而言,文本细读应成为阅读文献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待一段文献资料,一定要摒弃成见,视若初见,通过仔细阅读分析,不盲从、不自蔽,认真细致地发掘其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
三、诗人史学家:史学研究的文学色调
“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一直能够吸引广大读者,除了他的论述缜密、材料丰富、鞭辟入里、奇峰迭起之外,还有他文字上的强大魅力。他的文字有如高山流水,一泻千里;有如波涛汹涌,气象万千。给人一种美的关照,美的享受。”[9]的确,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也时有流露出浓郁的文学气息,“诗人史学家”大概可以标示其这一研究特色。透过郭沫若史学著作文本,我们看到这一特色体现在这些方面:诗化的语言、浪漫式的笔调、浪漫的推理与想象,以及幽默休闲的研究心态等。保守看来,在史学研究领域,这或许会被讥为治学不规范,如有学者认为,“其在书中表现出的文学家式的想象力有悖于史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严谨的逻辑论证的原则”[10],但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位勇于创新的研究者。
在郭沫若这里讲语言的诗化,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女神》似的激越的感情,力拔千钧的气势,绚丽繁复的意象等,在郭沫若史学著作文本中,这样的语言亦时有见到。比如他在《王阳明礼赞》一文中,写到王阳明临终遗言时有这样一段: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啊,这是伟人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再回头读他的《泛海》一诗吧,我们请看他的精神是不是如象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是不是如象夜静月明中的一只孤舟在和险恶的风涛搏斗呢?但是他是达到光明的彼岸了!我们快把窗子推开,看看那从彼岸射来的光明!我们的航海不幸是在星月掩蔽了的暗夜之中,狂暴的风浪把我们微微的灯火吹灭了,险恶的涛声在我们周围狞笑。伟大的灯台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快把窗子推开,吸收他从彼岸射来的光明!我们请把那《泛海》一诗,当成凯旋歌一样,同声高唱吧![11]297
一气读来,简直就是《女神》里的某段节选!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其时郭沫若已经长期崇拜王阳明思想。“王阳明先生是我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人物,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巨人。”[12]写到自己拜服的人物,尤其是王阳明生命最后的场景和铁骨铮铮的遗言,感佩之情难以自已,所以,在这里,在史学论著写作这严肃的笔尖上倏然跳跃着一个怒放的灵魂,为其笔下的人物引吭高歌!这不禁为严肃的史学研究增加了文学式的强烈感染力。
同样的案例还有《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其中写到万宝常一生的悲剧:妻离子散,境遇飘零,穷苦劳顿——
以他之专精于音乐而又贫苦劳顿,他当然冷落了他的夫人。以他之音乐奴隶的身分,他当然没有本领去满足她的物质欲望。他所有的“资物”竟以一个女人便能窃取而逃,当然也是没有多少的。但其中或者怕有他所倚以为生命的乐器(我相信是琵琶)吧?那在他,怕比失掉了一个老婆还要贵重吧?他的夫人逃走了,他能够起来烧书。他假如高兴时,也尽可以起来烧饭。大约米已经是没有了,买米的钱也是没有了。没有钱,没有米,他不肯去向人赊借,与其说是邻人的无情,宁可说是万宝常的不妥协。是的,不妥协![7]141
这里并不是实景再现,而是充斥着作者大量的揣想。从内容上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郭沫若小说“漂流三部曲”中的爱牟,而爱牟又是作者影子的折射,因此,这样的文字倾诉,应当是融入了作者顾影自怜的伤感。诗一样的语句,诗一样的情境,构成了那幽怨的、浪漫的推理与想象,不由得读来黯然神伤,深为一代音乐天才空怀抱负、郁郁而终而叹息!在这里,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郭沫若无疑尽了诗人之能事,让原本严肃枯燥的史学研究也变得人情味起来。
这种诗化语言有时也与浪漫的笔调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增加了它的诗化特色。在《庄子的批判》一文中,论述道家对“道”的观念的执着,有这样一段:
把一切差别相都打破,和宇宙万物成为通,说我是牛也就是牛,说我是马也就是马,说我是神明也就是神明,说我是屎尿也就是屎尿。道就是我,因而也就什么都是我。道是无穷无际、不生不灭的,因而我也就是无穷无际,不生不灭的。未生之前已有我,既死之后也有我。你说我死了吗?我并没有死。火也烧不死我,水也淹不死我。我化成灰,我还是在。我化成为飞虫的腿,老鼠的肝脏,我还是在。这样的我是多么的自由呀,多么的长寿呀,多么的伟大呀。[5]199
熟悉郭沫若新诗的人一定会为之拍案叫绝,一定会想起《女神》,想起《天狗》,想起郭沫若的诸多新诗作品:从笔调到神韵,从意象的选择到情境的营造,无一不体现出郭沫若浪漫豪情的诗风,而这实在只是郭沫若史学论著中的文字。
郭沫若是熟稔幽默艺术的人,在史学研究中却也把幽默艺术带了进来,不时营造出一种轻松休闲的论史空间,与传统治史状貌相比,这也是大异其趣了,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风格。他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论述该派以人民为玩物的为政态度:“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道德经》第三章)紧接着,论者直斥“这办法是养猪养牛的办法”[5]185——幽默、滑稽,而又一针见血地痛陈其为政的本质。再往下,论者又对道家消极的“五色令人目盲”说给予了嬉笑怒骂的一番嘲讽,顺带着痛批了巧于辩护的章太炎,文字既有《女神》式的江河奔流、无可遏止的气势,又充斥着令人赧颜的嘲讽调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意一一列举。
有人说,翦伯赞“发扬‘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传统,强调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写出许多文采飞扬和饱含激情的经典史作与历史散文”[13],但通过对郭沫若治史实践的考查,我们看到郭沫若作为一位诗人史学家无疑更具典型性。
综合上述对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特色所做的具体而微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郭沫若以医学士、新诗人、革命者的多重身份投入到古代史的治学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创造社同仁成仿吾曾说:“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11]263另一方面,在其深入独到的研究实践中,郭沫若凭着骄人的才赋、辛勤的努力、创新的意识、求实的精神等,使其研究也确实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色,这些也理应成为郭沫若不容抹煞的治史成绩,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亦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