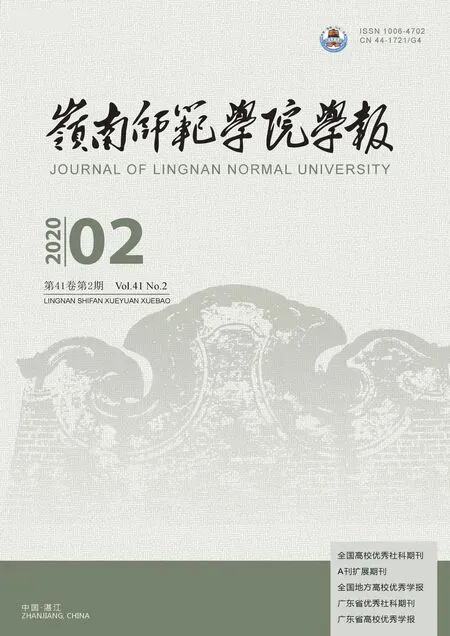论卡西尔对西方艺术本质观的批判
宋 梓 祎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艺术和美是人类生活经验和人类审美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可观、可感、可知的感觉维度和认识维度。同时,艺术和美也是人类思维和人类意识的思考对象,美的哲思将艺术引领到形而上学式的具有思辨性质的理论层面。这种思考正是基于人类经验世界并超越经验世界的一种本源性追问。从艺术理论史的发展变迁来看,对艺术“本体论”发展历程的看法通常表现为由注重“经验性”到注重“形而上学性”的转变,即艺术作为自然客观世界的“摹仿者”向艺术作为构建人类主观感性世界的“表现者”的转变。尤其是受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将艺术本质归结为情感表现的观念已经逐渐颠覆了古老悠久的摹仿论思想。作为20世纪符号形式美学的开辟者,卡西尔以其符号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独特视角对模仿论和表现论进行了批判。
一、对摹仿论和表现论的批判
何为艺术,即艺术的本质问题向来是众说纷纭。纵观艺术史发展,原始的艺术还不具备自律自主的条件,而是承担着宗教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功能,艺术还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实用”成为原始艺术的代名词。到了西方近代,一直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现才真正确立了艺术的自主法则。康德提出“鉴赏判断是审美的”[1]39这一论点。康德认为,鉴赏判断的逻辑不同于知识判断,因而鉴赏判断不属于一般逻辑法则,而应遵循审美逻辑法则。这就意味着鉴赏的标准、法则和尺度都要由审美的判断、审美的逻辑所决定,卡西尔紧随康德思路,称艺术“隶属于一个相异的裁判权”,这里的“裁判权”指艺术回归自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逻辑——想象的逻辑。在这里,艺术完成了由理性活动的“产物”到感性活动的“主人公”的角色跳跃。
自古希腊起,哲学被划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这三大板块,到了康德后期哲学的发展中,他不得不扩大了这种划分,将美学作为批判哲学的一个特殊门类添加进来[2]22。尽管如此,艺术的“自主权”并不能说明艺术想象的逻辑可以与纯粹科学逻辑的地位相抗衡。考虑到当时的艺术现状,无论将艺术放置在人类经验和现象的范围去考虑,还是对艺术自身进行哲学思索,艺术都没能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而是被视为道德律令的传话筒,被界定为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预备阶段,是“一种指向某种更高目的的次要而从属的手段”[3]235。面对艺术所显现出的“附属性”地位,卡西尔并不赞同,他为艺术正名道:“我们绝不能把艺术当做人类生活的装饰品,而必须把它视为人类生活的要素和本质条件之一。”[4]139在这里,卡西尔将艺术的本有属性与人类基本而实际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将艺术看作是人类经验维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神秘之物”。也就是说,卡西尔敏锐地察觉到“艺术经验”与“生活经验”之间的共通之处,以此来确立艺术的基本属性和地位。艺术是不外乎我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存在,艺术经验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卡西尔对传统摹仿论及情感表现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艺术摹仿论最早是柏拉图所构建的“理式”概念的产物。在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来看,世间万物皆为理念世界的摹本,人类经验世界的真理要在超验世界中去寻找,因而现实世界是受理式世界来规制的。柏拉图由此归纳出一般的诗歌本质为“摹仿”,或称为mimesis。诗的摹仿对象是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摹仿的对象是理式世界,因此诗的摹仿是对“影像的摹仿”[5]348。譬如,柏拉图控诉诗人,并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的原因有二:一是文艺不能传达真理,文艺与“理式”隔着两层,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二是诗人同诡辩者一样,他们歪曲真理,制造幻象,从而文艺具有扰乱世界秩序,加速社会道德败坏,蛊惑人心的影响。柏拉图从“理式世界”的概念出发来思考文艺活动,认为艺术的摹仿不足以揭示真理,因为事物的真理只存在于他所建造的理念世界之中。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则认为摹仿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同时摹仿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人类可以在摹仿中获得知识和快感。尽管二人对待艺术摹仿论的态度大相径庭,但对于“艺术源自摹仿”这一说法深信不疑。
就艺术创作来说,艺术作品不可能一味机械地复制自然,那样便丢失了艺术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创造性。无论出于多么强烈的摹仿目的,呈现出来的作品都会不可避免且不同程度地存留创作者的“印记”。这种“印记”可以理解为创作者的个体经验之体现、感性情感之流露以及审美趣味之凝练。在卡西尔看来,任何艺术都要跳出单纯而机械式的“复制自然”的桎梏,“摹仿自然”并非艺术的目的,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摹仿“美的自然”,也就是“偏离自然”[3]238。为了达成“偏离自然”的艺术美的效果,需要在摹仿自然的同时对自然进行剪裁、取舍和提炼,而这一系列活动统统离不开艺术家的主观性创造。
19世纪仍有为数不多的文艺批评家坚持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摹仿这种观点,法国的丹纳便是其中之一。丹纳认为,艺术是源于经验而非观念的一种形式,艺术与生物学具有一致性,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一致性。究其根本,丹纳这种将艺术类同于动植物的思想最主要植根于一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韦勒克对此有过这样的评判:“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基础的。”[6]57韦勒克更加清醒地指出文艺活动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与“进化”阶段,拒斥了艺术的“进化论”思想,二者之间不存在合理的可比性。伴随着18世纪中期对摹仿说的种种质疑,情感表现说成为一个崭新的艺术理想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和歌德等人成为这一“新力量”的领衔军。相较于单调而机械的“摹仿自然”,情感表现论倾向于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和情感抒发,遂发展为一种新的文艺潮流和艺术风尚。
在卡西尔看来,情感表现说有几个地方需要重新界定。第一,对艺术中情感的种类和程度进行界定。情绪可以看作是情感的一种,但情绪不等同于情感,情绪是日常生活中个人化、主观化的一种宣泄方式,而情感表达才是艺术世界中能够引起接受者共鸣的一种表达方式。情绪表达没有固定的对象,而情感则不同。试想在舞台戏剧中,艺术家歇斯底里地宣泄自己大量的情绪,不仅破坏了整个作品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欣赏,还会降低观众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一封情书尽管表达了强烈的爱意,拥有丰富的情感,仍然不能被称作艺术作品。正如卡西尔所指出那样,“被情感支配只是感伤主义而非艺术”[4]150。在艺术创作中,如若将重点完全放置在情绪方面是十分片面的。卡西尔认为,表现论与摹仿论的不同之处并非根本意义上的转换,而是由原来摹仿论中对自然世界的摹拟转换成了对人类感情和情绪的摹拟,他将之称为“记号的变化”[3]241。
第二,对艺术中表现对象的界定。依据卡西尔的符号论,文化和艺术具有超越于“单纯事物”的“符号”属性,回到具体艺术作品中,艺术所表现的主题也应是超越于纯粹事物的,即“符号-文化”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表现”一词最初是生物学概念而非审美概念,生物性的动物表现譬如猴子眦牙示威、孔雀开屏求爱都是一种表现性动作,然而这些表现性动作远非艺术表现。与此同时,卡西尔还强调艺术表现中“目的性结构”的重要性,他说道:“对于语言的表达和艺术的表现来说,有目的性这个要素则是必不可少的。在每一种言语行为和每一种艺术创造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明确的目的论结构。”[3]243也就是说,一声叹息、一个动作、一种姿势都是表现自我的方式,但这是非自愿、无目的的本能式反应,这种表现形式中并不存在“目的论结构”,从而与真正的艺术表现有着本质意义的区别。
二、艺术的想象特性
除了对摹仿论、表现说等传统艺术本质论进行剖析,卡西尔还围绕艺术的想象特性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美学流派分别进行考察。尽管各个美学流派之间纷争不休,每个学派关于艺术想象都各执己见,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即“艺术是一个独立的‘话语的宇宙’(universe of discourse)”[3]260。在卡西尔这里,艺术的想象特性是使艺术成为独立于科学、宗教等其他符号形式的本质要素,因而有必要对艺术的想象原理做出具体的、历史的理论阐释。
法国古典主义盛行的时代是“理性的时代”,因而要遵从“理性的原则”。一些文艺批评家认为艺术想象应遵从理性的原则,主张情欲应由理性约束。法国思想家布瓦洛为抵制从意大利传来的文辞纤巧之风,认为文章中的“音韵”是“情理”的奴隶,“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7]62。“三一律”最早引申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了16、17世纪被不断阐发而成为法国古典主义恪守的戏剧标准乃至权威性规范。在这里,诗人的想象力被禁锢在纯粹客观之中,艺术想象的力量几乎被理性的力量完全湮没,卡西尔称之为“古典的可然性理论”[3]261。
浪漫主义中的诗意想象原则反驳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诗歌的题材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和不可思议的奇妙世界,情感性和审美性的艺术品格成为浪漫主义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正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想象与诗歌是一对互相联结的概念。诗歌是想象的巢居地,想象是诗歌的独特品质。想象是人类意识的产物,与人类意识具有一致性,因而想象是无边际的、自由的、非客观事实的意识存在。诗歌在18世纪成为最富有浪漫主义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物质载体,它承载了神秘莫测、魅力十足的想象世界。想象是诗的重要生命源泉,缺失想象的诗歌将成为一口枯井。
卡西尔追溯“想象的逻辑”时涉及了意大利维柯的重要哲学思想。维柯区分了人类进化必经的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维柯认为,在前两个时代中表现性和想象性的功能占据主流,后一个时代中科学性功能占据主流。维柯预知并道出了哈曼、赫尔德的心声:诗性思维诞生于最早的神话世界,“诗乃是人类之母语”。这就意味着,只有在充满想象的神话世界中才能找回真正的诗歌,想象世界中的诗与诗歌的想象品格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在时空层面上,我们距离“神的时代”已经十分久远,然而在艺术领域中,我们可以重拾那早已远去的“神的时代”。卡西尔认为想象的创造力源泉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因为想象力的品格早已烙印在艺术的基本特质之中,想象力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时代内容,熔铸成艺术和诗的内在力量。
还需注意到,艺术想象在浪漫主义这里已经不是客观世界人类意识的单纯产物,而是超越实在、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式的概念。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人类用理性、用概念把握整个客观世界。到了浪漫主义时期,理性思潮逐渐褪去,情感表达、艺术想象成为人类探索实在、把握客观的唯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具有与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为此卡西尔说道,“把哲学诗歌化,把诗歌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3]267。在浪漫主义诗人那里,“审美”大于“求真”,艺术中的诗意想象程度越高,越接近真实世界。凭借艺术想象的至高地位,艺术与诗化作真理的终极显现。谢林曾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确立艺术的客观属性,同时认为艺术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理智直观的这种普遍承认的、无可否认的客观性,就是艺术本身。因为美感直观正是业已变得客观的理智直观。”[8]308黑格尔发展了谢林的客观唯心论,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之显现,可是在卡西尔看来,“艺术的真正主题既不是谢林的形而上学的无限,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我们应当从感性经验本身的某些基本的结构要素去寻找,在线条、布局,在建筑的、音乐的形式中去寻找。”[3]269-270
如果说浪漫主义将焦点放在“先验形式”上,那么,19世纪兴起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焦点则是经验世界的“内容”。现实主义打破了一直以来艺术世界与人类经验世界相割裂的传统二元论思想,为艺术重新展现人间百态、平凡世界图景开启了新的窗口。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一个平凡无奇的街景或是其他不起眼的物件……这些微小的事物都是现实主义作家们可以描绘的题材,然而在对浪漫派的排斥中,他们不免重陷“模仿自然”的窠臼。卡西尔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艺术的符号特性的存在,而是对艺术符号特性的理解有所偏颇。为此,他强调道:“艺术确实是符号体系,但是艺术的符号体系必须以内在的而不是超验的意义来理解”[3]261。在这里,卡西尔借此来区分自己的艺术观与浪漫派最大的不同,他的艺术符号体系的出发点是人类经验世界而非超验世界。
传统的观点乃至当今的观点一直认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摒弃了浪漫主义的抒情与想象,缺乏艺术想象空间,卡西尔则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想象力不低于浪漫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在承接浪漫主义方式的基础上做了许多革新,其主要运用典型化方式来塑造人物。恩格斯曾说“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运用典型手法并不是“照相式”的记录和描述,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选取有意义的人物或事件进行个性化和艺术化的加工。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罢,都力图在还原生活的原貌之上凝练出艺术结晶。现实主义不是用浪漫主义的感性抒情方式,而是用典型的方法塑造人物、讽喻社会和人生。所以,我们不能说想象仅局限于一种浪漫主义方式,现实主义的艺术处理就是现实主义式的艺术想象。
三、对现代心理学美学的批判与继承
20世纪的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反对以理性主义和理智主义为代表的艺术观念,强调从人的心灵出发来把握艺术。古典主义主张把艺术理解为枯燥的算术命题,浪漫主义将艺术置于高耸入云的形而上学彼岸。现代心理学理论反对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也排斥浪漫主义的感性原则,在重回美本身中打破了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现代美学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美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积淀和批判支点。
艺术和美的心理学理论研究致力于探究和分析关于美的事实与现象,从而对美现象背后的“逻各斯”鲜有定论。在人类几近所有的感知活动中,审美活动给人类带来的愉悦和快乐超过了其他的经验性感知方式。在人类经验世界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拥有了味觉、触觉、听觉、视觉等等感知方式,其中视觉是人类感知系统中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带给我们感官上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直接抵达心灵和精神世界,达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视觉之所以比味觉、触觉等感知方式高超在于它不仅仅局限在“看”的生理性需要,而是“看”的背后内蕴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心理性诉求。暂且不论约翰·伯格(John Berger)“观看先于言语”[9]4命题背后的深刻哲学含义,人们透过视觉图像获得一份“特殊的”审美快感却是不争的事实。以绘画和雕塑为例,我们透过特殊的物质材质抑或光影色彩的形式观看所带来的审美愉悦,是任何满汉全席的大餐所不能替代的,因为只有进入审美世界的殿堂,我们才会距离精神本源更近一层。
从最素朴的美的心理学角度出发,艺术的特质是能够带来愉悦和快感的“美”。然而这种“美学快乐主义”所关心的并非是艺术现象背后的意义问题,而是能够带来多大快乐的问题,即快感程度的问题。康德曾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审美快感与花钱做过类比分析:想要获得更多金钱与想要获得更多审美快感一样,不会关心来源问题,而是关心多少问题。卡西尔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如果快感是共同特性的话,那么真正重要的只是它的程度,而不是它的种类。”[3]272
美国的桑塔耶那认为美是一种快感,更是一种善。快感不涉及事物的功利作用,快感仅仅在直觉层面上得以实现,他将美定义为“事物之属性的快感”。紧接着他概括道:“美是一种最高的善,它满足一种自然功能,满足我们心灵的一些基本需要或能力。所以,美是一种内在的积极价值,是一种快感。”[10]34审美快感是主观的个体的存在,其不存在普遍性,然而如何能达到客观化呢?桑塔耶那认为,科学与艺术都需要真实性,但二者的真实性有着本质区分。科学真实是本着求知的原则,要求对人类世界和社会进行客观把握;而艺术中的真实则有助于满足“娱乐要求”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没有哪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本着娱乐的目的完成的,当然我们不是要排斥艺术中的娱乐和快感成分。
卡西尔对以桑塔耶那为代表的美学快乐主义进行批判从而提出:艺术中的享受不是单纯事物的享受,而是对艺术中形式的享受,其中形式的享受只有在创造时才会感悟得到。由单纯事物到艺术形式的转变当中,快感也由一种单纯感受转变到功能层面。卡西尔认为以桑塔耶那为代表的美学快乐主义虽指明了美学心理学理论,却没有真正认识由静态日常事物到动态艺术形式的根本转化。与此同时,桑塔耶那的“美是客观化了的快感”也过于笼统不清,卡西尔认为桑塔耶那对“客观化”的理解比较片面,因为客观化是一个动态的构造性活动,而非静止的状态。他指出物理世界和艺术世界都有客观化的过程,但是二者为达到“客观化”所凭借的依据有所差异,即物理世界借助概念和科学,艺术世界借助构形和直观。
还有一些现代理论避开了将艺术等同于快感的研究,但是他们仍主张将艺术品与其他现象相联系来阐发艺术的真谛,只不过这次不是快感,而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了。譬如柏格森将审美状态喻为“催眠状态”、尼采将艺术喻为“做梦状态”与“醉酒状态”等等。在这里,虽然艺术确实与某种现象或状态有着相似性,但是仍然不能成为我们打通艺术实质的那把“金钥匙”。卡西尔认为,“这些现象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上的;它们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心灵状态”[3]274。拿审美经验与催眠现象来说,被催眠的人与感受艺术的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在我们的审美过程中既要有“审美输入”,也要有“审美输出”,她不会向催眠活动那样只有单方面的“输入”。因而审美活动不是单方面的被动式的接受,艺术活动是一种依赖于观照的活动。同样的,艺术也不是散乱无章的酒醉式的兴起,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尽管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通道,但梦幻和酒醉却更多地展现了杂乱无章的情感而非秩序井然的结构整体。这里忽略了艺术的一个本质特征,那就是形式结构的统一性。
除了对美学快乐主义进行批判,在卡西尔看来,还存在另一种试图将艺术等同于游戏的危险。实际上,关于二者关系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游戏”的性质。康德曾经以游戏来区别艺术与手工艺这两种活动的本质并且界定艺术是一种“游戏”[1]149。康德这里的“游戏”是一种自由的、愉快的、合目的的状态,这种游戏状态符合艺术活动中的“无功利”和“合目的性”的审美特质,这就把“艺术”和“游戏”紧密连接起来了。而手工艺由于受到雇佣关系的影响,并没有产生愉快的、游戏的非功利性的审美感受,因而不是游戏的。席勒则进一步考察了艺术的起源问题,认为艺术起源于力量过剩的游戏。席勒的游戏说不同于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游戏说,因而他的观点也不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和自然意义上的“游戏”。他的游戏是人走向自由世界的表征,他继续沿着康德的路径,因而他的游戏概念是“自由”的,只有人的世界才能够通达自由。卡西尔认为席勒与歌德的美学观具有一致性,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不认为‘自由’和‘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在上述这两个概念之间,他们找到了一种相互关联而不是相互对抗的关系”[11]129。在席勒这里,游戏不是一种普遍生物机体的活动,而是带有人属性的特殊活动,正如他说,“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12]209。卡西尔虽承认席勒反对将游戏置于自然主义的观点,但是与席勒不同的是,卡西尔对“游戏”与“艺术”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提出质疑,他强调游戏的意义有别于艺术的意义,游戏活动所缺乏的深刻性和反思态度恰好是艺术最弥足珍贵之处。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艺术与游戏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主要体现在人在游戏过程中与在审美活动中所体验到的快感均为无功利性的。在游戏状态下,人处于无功利性的自由之中,游戏的材料是虚构的,可以是人类经验生活的也可以是超出经验生活的,游戏活动所为人们带来的快乐是随意的、松弛的、不带有任何实际功用色彩。在审美过程中,我们徜徉在色彩、旋律、节奏、造型等等形式之中,抛却实际生活需要,在静观中构建,在感悟中创新,这同样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成分的活动。
然而,艺术与游戏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二者是等同的。卡西尔认为艺术想象与游戏活动中的想象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他说,游戏所带给我们的是虚幻的假象,而艺术则带给我们虚幻的“真实”,这里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经验事物的、能够激发美感的“纯形式的真实”。卡西尔将想象分为三种:虚构的力量、拟人化的力量和创造激发美感的纯形式力量。在游戏活动中,我们能够发现前两种力量,而在艺术中则能感受到最后一种力量,这是源于我们在这两个领域所运用的素材不一致。正如卡西尔所说,“孩童是用事物做游戏,艺术家则是用形式做游戏,用线条和图案、韵律和旋律做游戏”[3]281。在这里,孩童眼里中的“事物”与艺术家眼中的“形式”都是另一种人类经验世界的表达。游戏者是在一个虚假的“经验世界”中玩耍,游戏的世界最终是对经验世界的某种“事物”进行模仿、虚构、抽象的达成,这一“事物”就是我们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变形”;艺术家眼中的“形式”也是来源于我们经验世界的产物,但却不同于单纯的“事物”形象,这里的“形式”主要是指赋有灵性的、创造性的想象结晶。这是因为艺术中的想象将静态的“事物性世界”进行重构,塑造出了一个基于人类经验世界、又不同于人类经验世界的“活生生的形式世界”。
卡西尔还指出欣赏者所持有的恰当的审美态度应该是审美判断和艺术关照的前提。在游戏活动中,或许我们更加需要娱乐式的消遣感受,那是一种松弛的情感态度;在艺术欣赏活动中,我们的审美态度应是强化的而不是松弛的。“艺术要求最高度的全神贯注。只要我们没能全神贯注,而是追求令人愉悦的感觉和联想的单纯游戏,那我们就无法领悟艺术品本身。”[3]283在这里可以看出,卡西尔是想倡导一种积极的、崇高并且相对严肃的审美态度,这种审美态度区别于消极的、情绪化的、游戏化的观赏态度。简而言之,我们持有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观念,就会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艺术风貌。在卡西尔这里,游戏世界与艺术世界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且艺术世界是“高于”游戏世界的存在。因为依靠游戏的、悠闲的态度是不能发现艺术中的“美”,真正的“美”体现在“活生生的形式”之中,需要我们静观作品中情感与形式之美,这时才能将观赏者的情感和创作者的情感放在同一个维度相互交融、碰撞,从而产生“美”的感受。
四、“感性形式”的审美维度
无论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艺术史论角度乃至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对“摹仿论”和“表现论”这两种学说持否定的态度都不在少数。那么,以卡西尔对这两种传统艺术本质观的批判为例,能够从中得到哪些独特的启发便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叶秀山曾这样总结说:“从根本上说,在卡西尔看,艺术是一种符号形式,是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因而它的问题就既不是‘模仿’,也不是‘表现’,而是‘解释’。”[13]51叶秀山透辟地指出,理解卡西尔艺术观念之根本在于对他所提出的符号概念的准确把握。那么,也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卡西尔的艺术观即是他的符号观,“艺术”是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艺术”是人类能动的文化结构。
实际上,在他对传统艺术本质观进行批判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他的表述中“摹仿”与“表现”并不是完全分离开来的。但是,即便将二者简单联系起来,仍然不足以建构他的艺术观。这是由于“艺术的世界”不同于“事物的世界”,而是一种“形式的世界”。卡西尔是以一种“感性的形式”来界定艺术的实质,艺术形式可以给予艺术情感以一种确定性,同时,艺术的“构形”(formative)活动也体现了人类文化活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艺术家与他面对的世界的关系,就不是‘模仿’、‘再现’的被动关系,而是要从他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意义,看出世界的新意蕴,做出一种新解释”[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