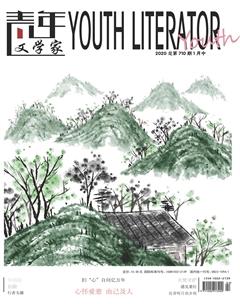内外力量的反向撕裂,灵魂幻灭的必然落脚
摘 要:《小城三月》作为萧世的最后一部作品,对于女性内在情感在特定环境下的抑制性书写和作者寄寓其中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思索,都要有别于其他作品所传达的内在意蕴。在当前的萧红作品研究中,将《小城三月》主题意蕴界定为是表现“东方女性悲惋曲致的哀歌”加以阐释处处隐现的女性视野在作品分析中有多种看似“合理化”的暗示。然而本文将前人之语稍加搁置,将以全新的视角从内外双向力量,主体生命向外扩张延展的强烈欲望和可能,与向内无限萎缩生存空间的主客观作用相互力量的激荡碰撞对主体灵魂的撕裂冲击中,重新审视《小城三月》所营构的悲剧生成的必然性。
关键词:内外力量;反向操控;灵魂撕裂;悲剧必然
作者简介:宋艺焱(1999.9-),女,辽宁沈阳人,本科,沈阳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2
一、在男性形象弱化中初见端倪
对新式人物“哥哥”的形象始终以一种模糊性处理,同时对所谓的安排好的婚姻对象的着墨可谓是少的可怜,仅有几笔有限的勾勒,却也显得苍白和浮光掠影。刻意对男性形象留有遐想的余地而预留出一定的空白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在外,“我的哥哥,人很漂亮,大概在我们家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物”、“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这何尝不是五四新文化风气的具象化的显现?相比翠姨被包办的婚姻对象“人长的又低又小,穿一身蓝棉袍子。”同样暗示一旦顺从必将是重回孤寂保守的悲剧性的生命轨迹?男性在文本中的存在空间微乎其微。如果叙述的重心是因两人的懦弱促成的爱情悲剧,那么最基本的与“爱情”相关联的两个基本对象的联系应该寄予更多的悲观体验的投射与情感书写。对于对象间联系处之以淡化,情感线索隐秘背后,翠姨个人向理想化身份确立和摆脱他者地位的追寻却是伸向深层,并以外化形态显露,从而使爱情悲剧的实质性确立受到质疑。
二、双向力量的灵魂撕裂
“作者发挥其熔环境背景与抒情写意于一炉的散文笔调,以春为环境背景将这一梦幻哀愁般的心理流布图描画的更为楚楚动人。”但这却无法掩盖背后的对于女性生存前提和安身立命基础的严肃性反思。萧红小说是获取了这一世纪性的现代文化背景而在“深度进向”上实现了其“强大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跨度”,在新的广度层面和深度进向上展现人類的觉醒意思,寻找到“一种新的活动方式”的艺术表达。而在这里,无论是个人内在的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环境使然,都催生着翠姨对新式生活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的渴望与追求,同时衍生出抑制其自我生长的内外元素。
(一)向外—对释放生命力量的渴求
1、充满矛盾的女性自我表达
翠姨并非完全排拒自我于现代文化环境之外,她曾带着新鲜的眼光,澄澈的充满生命气息的心灵去寻那付诸于独特意义的“一双绒绳鞋”,却最终难以如愿,反复哀叹着“我的命,不会好的”,也曾在“吹箫欢唱”的自由氛围里,“不惜一切地向着这生命的灯火踽踽独行”,却越发衬托出自己生存处境的落寞失意,僵化而缺少生机。在大家一起打网球时,“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市影痴望着。”受到哈尔滨大都市的文化洗礼,翠姨越发隐藏不住自己渴望出走于狭小天地的隐秘情感和对现代化气氛的憧憬。当她像一个女学生一样被当地颇为都市化的庄严、漂亮的学生招待着,“以俄国人的规矩受着尊重”时,一切的悲伤孤寂都在那一刻化解,成为“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事实更多的是个体对于这段充满暧昧情愫的无知和浪漫化的想象,翠姨个人的无知是在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之下,对于早就上了洋学堂的哥哥—那个只被赋予了模糊叙述的男性寄予了崇拜感和带有“自卑”心理的幻想,将崇拜对象进行置换,本质上是构建出将“哥哥”作为现代文明表征的自我假想,进一步引申出对于封建婚姻束缚的本能性的拒斥,将个人的命运寄寓于一个陌生化的、理想化的精神依附对象之上,这本身缺少情感的真实附丽,最终使个体灵魂倒向内外力量的双向撕裂而无法避免悲剧处。“内隐情感的自我克制与长久的不可言说”压抑消磨着本就不堪一击的灵魂,加之数千年来传统规范约束下的愚昧无知的乡镇生存环境,将对现代文明氛围的痴迷与憧憬转化成对于哥哥“深切的爱”,压抑着自我独抒性灵的表达空间。这种情感本身就是“空虚而没有血肉的”,缺乏支撑其永恒存在的基本条件。
2、外在力量的多重虚幻营构
难以抗拒的外化力量。“我”和我的家庭的出现,进一步萌生出翠姨编制出依靠“现代化的新思想的载体哥哥”来追寻幸福的假想。“我”是个洋学生,将外界的一切新潮流新思想带入到翠姨封闭的闺阁。“我”的父辈们参加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个家庭都咸与维新起来”,在现代化的文明昭示之下更显翠姨个人的封闭拘泥和卑微不堪,从心底而言,翠姨就带有着对于新的情感生活方式的不受抑制的憧憬和渴求,“因为我在学堂里读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有很多事都问我意下如何。”我成为了翠姨表达自我、放逐自我、升华自我的栖息地。
(二)向内—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否定
1、生命本体多重对照下的无力体验
长期留守于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乡镇,受着母亲改嫁身份的牵连,感情的无所依附使翠姨生性多愁善感,心理细腻多思。加之母亲寡居的孤寂、封闭心理环境将自我放逐在无人之境,对外界的自我拒斥,在否定了自我内在价值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催生着她的内在生命里对自由的渴望,对外在生命世界无限开拓的欲望和对确立自我生命价值的强烈的呐喊。文化教育的受之匮乏使精神流浪无所归依,加之落后闭塞的乡镇生长环境的日益捆绑之下没有足够的养分供给,文化心理的浅薄窄化了翠姨的内心和对外部世界的视野投向,作品中第三节中重点提及到哥哥那“一切洋化,彼此说话哒哒哒,见了女人不怕羞”的新派青年,绝然不同于翠姨生存环境中充斥的那般在压抑、缺少人性关怀的、愚昧腐朽的传统文化规制下的狭小天地。生存与五四运动之后,“反对封建主义的春风,度过山海关,终于吹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满洲原野”,复苏了翠姨将要干涸无生气的生命之源,将她的灵魂荡起了一阵阵涟漪,也衬托出翠姨个体生命之流的苦涩。
2、生命体验自我审视下的卑微设定
与其说是对着哥哥的深切而无法表露的爱挤压着她个人的情感表达余地,倒不如说是翠姨本身是将哥哥无意置换成了带离自我摆脱困境、冲破礼教藩篱、奔向现代文明的完美归属。对于自我选择的爱情的憧憬无处言说,便只能由有限的外化可能转变成最大程度的内化,将内心情感无止境地隐藏,“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五四新文化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俯视着拘泥于封闭空间的保守思想。在高尚且以科学先进标榜自我的五四新文化面前,一切拘泥于封闭文化空间的生命个体都会自惭形秽,“女性受制于男性”的时代命题感召下,翠姨从内心早已作出自我的卑微设定,将自己的命运定格为一个“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连连哀叹自己的命运的无力把握。在极为珍贵的在所爱之人展现自我的时候,赶忙退回自己早已计划好的命运之中,“跑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萧红对翠姨内心的隐秘心理透漏出一个重要的文化认知信息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所确立的女性生命体验与生存方式。翠姨看似是悲观心理的覆灭,觉醒到“出走于乡镇”的必要性,但遥想到个人的无所依傍,彼此人生境界的难以跨越的巨大鸿沟,家庭的催逼和无视、生命价值的难以确立都是她最终香消玉殒的无形推手。即使是在表层欣喜于新文化的“文明守礼、自由平等”,但在本质层面上个人的生存哲学和道德认识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各方面都已经被封建文明所同化而难以改变。
固然封建礼教和迂腐的文化拘束了翠姨的情感表达空间和生命审视的视角。但深层的是她感受到了不同于妹妹受着自己丈夫毒打的凄苦无望的遭际的那般受人尊重,文明有礼、尊重女性的新文化的冲击,重生起实现新生、确立自我生命价值的可能性欲求。对约束重重的旧有传统的厌弃感与日俱增,内心渴望逃离奔向新生的情感欲求与客观现实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的否定质疑以及本体的孱弱无力,如两个趋于相反方向的绳索猛烈地拉扯着,最终撕裂了翠姨的灵魂。内外双向的是非纠缠使得灵魂幻灭的悲剧结局注定成为生命的落脚而难以避免。
参考文献:
[1]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99-P102.
[2]孙延林.萧红研究第二辑[M].哈尔滨出版社,199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