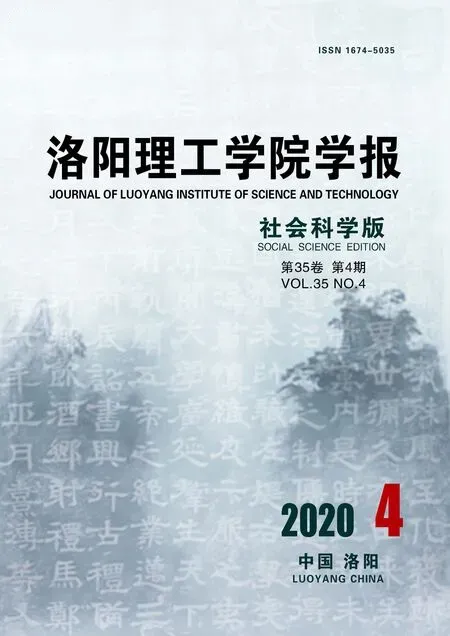论唐代的孔雀意象与社会生活
刘啸虎,文新宇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孔雀,别称越鸟、南客。李济早年于安阳殷墟考古时曾掘得孔雀骨[1]114,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孔雀已出现于时人的视野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孔雀以进贡的方式进入中原,南北方的交流也使南方孔雀进入北地。及至隋唐,孔雀的文化涵义已应运而生[2]。早在20世纪80年代,曾昭璇便对不同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孔雀的分布、种属进行过研究[3]。之后,学界对孔雀的研究层出不穷,涉及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又有学者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孔雀的分布与变迁,对孔雀的食药及配饰价值、传统艺术中的孔雀文化以及孔雀在宗教文化及传统风俗中的反映进行了考察[2]。时至今日,宏观视角下的孔雀研究已蔚为丰富;而以微观视角对特定朝代的孔雀进行研究,则相对较少。笔者拟以唐代为中心,就唐代孔雀的分布、利用与形象等问题展开分析,希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一、唐代孔雀的来源及分布
目前世界上已定名的孔雀种,只有绿孔雀和蓝孔雀。此外,也有学者将白孔雀另划为一种。绿孔雀主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越南和我国的云南等地,在我国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蓝孔雀主要分布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白孔雀是其变异品种[4]1-2。竺可桢曾提出历史上隋唐处于温暖期[5],许多学者围绕这一观点展开探讨,成果颇丰。一般认为,隋唐时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摄氏度,气候带向北移动1纬度左右[6]。孔雀生活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其栖息环境主要是海拔2 000米以下有针叶、阔叶等树木的开阔高原地带,或开阔的稀树草地、灌丛、竹薮地带,尤其是靠近溪河沿岸或林中空旷的地方[7]。据此可推测,唐代的亚热带最北界与今秦岭-淮河一线可能相差1纬度,孔雀生存的最北界应大致与此重合。
唐时中原地区的孔雀,应以绿孔雀为主。一般认为,绿孔雀是我国唯一的原生种孔雀。《交州记》云:“孔雀色青,尾长六七尺。”[8]3《异物志》云:“(孔雀)自背及尾,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9]5这些描绘的都是绿孔雀的特征。
据史料记载,唐时绿孔雀的分布地主要有三。其一,岭南地区,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全境及越南红河三角洲等地。《北户录》载:“雷、罗数州收孔雀雏养之。”[10]2《岭表录异》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11]15雷州、罗州、交趾均属唐岭南道,孔雀多出于此,并作为土贡进入宫廷。《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罗州招义郡……土贡:银、孔雀、鹦鹉”[12]1099,“雷州海康郡……土贡:丝电、班竹、孔雀”[12]1110,“爱州九真郡……土贡:纱、施、孔雀尾”[12]1113,“开元中安南所领有庞州,土贡:孔雀尾、紫穀”[12]1115等。晚唐齐己送友人到蒙州,吟诗:“蛮花藏孔雀,野石乱犀牛。”[13]81蒙州是现在广西梧州蒙山县,唐时即属岭南道。
其二,江淮地区。相关记载可追溯到汉代,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便有“庐江孔雀”。及至魏晋,魏文帝曾想派使者往荆、扬二州求孔雀[14]2828。到唐代,江淮地区的孔雀应为数不少。
其三,滇边地区。唐代樊绰《蛮书》曰:“茫蛮部落,并开南杂种也……孔雀巢人家树上,像如水牛,俗养以耕田。”[15]20-21唐时滇边地区孔雀的司空见惯,可窥一斑。
关于蓝孔雀,学界尚无定论。《魏书》载:“(龟兹国)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草乳如鸡鹜。其王家恒有千余只云。”[16]2267《晋书》载:“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17]2235王研博据此推测,以龟兹为代表,中古时期的西域存在较多孔雀;而西域无法满足绿孔雀的生存条件,西域的孔雀种应该是适应能力更强的蓝孔雀,蓝孔雀“经古丝绸之路,由南亚经中亚或翻越葱岭过新疆乃至河西走廊进入中原”[2]。王子今认为,西域的孔雀可能来自天竺等地,但无法完全排除当时龟兹存在原生孔雀的可能[18]。如前文所言,分布于印度的孔雀品种是蓝孔雀。总之,无论原生还是传入,西域孔雀很可能是蓝孔雀,并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
除蓝、绿孔雀外,中国古代也有关于白孔雀的记载。《宋书》载:“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闳献白孔雀。”[19]872《前定录》记载:“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20]11今人多认为白孔雀是蓝孔雀的变异种,但文献所记白孔雀出自盛产绿孔雀的交州等地。古人以白孔雀为祥瑞,可见古时白孔雀之稀少,也可见孔雀本身地位之特殊。
二、孔雀与唐代社会生活
汉《西京杂记》载:“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襚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21]8而“三十五条”中有“孔雀扇”,可见早在汉代孔雀已为宫廷生活所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有向外求取或征集孔雀的记录。如《晋书·陶璜传》载,邓荀从交州“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17]1558。魏文帝曾与朝臣有诏:“前于阗王所上孔雀尾万枚,文彩五色,以为金根车盖,遥望耀人眼。”[14]4104彼时孔雀毛已成为上层社会流行的奢侈品。《南史》载南齐文惠太子、竟陵王“性颇奢丽”,“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采金翠”[22]1100。及至隋唐五代,孔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更加耐人寻味。
《太平广记》引《纪闻》载:“(罗州)山谷夷民烹(孔雀)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23]3774孔雀肉、血、头可解毒的说法,在唐代为人所熟知。唐代药书《日华子本草》记:“孔雀,凉,微毒,解药毒、蛊毒。血,治毒药,生饮良。粪治崩中带下,及可傅恶疮。”[24]169然而,后世却逐渐出现了孔雀有剧毒的记载。如清人有言:“(孔雀)血最毒,见血封喉,立能杀人。”[25]169“孔雀胆”更成为毒药的代称。傅爽据此提出了“藏源假说”,认为孔雀有毒说法来自藏医,并随着喇嘛教的传播渗入宫廷,进而遍及社会[26]。
孔雀有毒的说法,或与蛇有关联。蛇多有剧毒又可入药,这一观念在唐代显然深入人心。柳宗元名篇《捕蛇者说》言:“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27]455《酉阳杂俎》也记载:“冯坦者,常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陆绍郎中又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因疮毁其鼻如劓焉。’”[28]115孔雀捕蛇本乃寻常的自然现象,但《纪闻》载:“卢肇住在京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来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23]3775似乎可以看到,唐人心中孔雀与蛇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在蛇是“毒”与“药”的共同体这一观念基础之上,又有蛇和孔雀存在某种特殊联系的观念(“蛇与孔雀偶”)与之相结合,孔雀或经历了一个从“解毒”到“剧毒”的信息传递过程,蛇的二重属性从而推及到了孔雀身上。及至元明,熊太古《冀越集记》言:“孔雀虽有雌雄,将乳时登木哀鸣,蛇至即交,故其血、胆犹伤人。”[29]505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发问:“按孔雀之肉既能解毒,何血独伤人耶?”李时珍注意到孔雀从“解毒”到“剧毒”的变化,而把原因归结于:“雉与蛇交时即有毒,而蛇伏蛰时即无毒。”[30]2669且有研究指出,孔雀确有喜食蜈蚣、蜘蛛、蟋蟀、蚱蜢、蜥蜴等昆虫动物的特性[31]166。因此,“孔雀有毒”的说法之所以广泛流传,或与之有所关联。
唐代服饰典制中已有使用孔雀氅、孔雀纹的规定。如《新唐书·仪卫志》载,“元日、冬至大朝会、宴见蕃国王”时充“供奉仗、散手仗”的仪卫军人,便有着“小孔雀氅”者[12]483。唐代上层社会较为常见的孔雀相关制品,当属孔雀扇和孔雀屏。有研究显示,周代的丧葬制度中始有用“翣”之规定[32]。更有研究进一步指出,“翣”是远古时期的扇子,长柄缚羽,最初是贵族身后侍者持在手中遮尘挡风的屏障,到殷周时期演变为一种仪仗的饰物[33]。就域外而言,《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载:“(婆利国)侍女有金花宝缕之饰,或持白拂孔雀扇。”[34]5271《新唐书·南蛮传》则有:“(婆利王刹利邪伽)坐金榻,左右持白拂、孔雀翣。”[12]6299婆利国远在海外,中土大唐却与之颇多相似。《旧唐书·职官志》载:“凡大朝会,则伞二翰一,陈之于廷。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旧翟尾扇,开元年初改为绣孔雀。”[34]1866唐代宫廷仪仗所用的“孔雀扇”,经历了用孔雀羽做材料到布绣孔雀图形为扇面的转变。晚唐薛逢吟诗“孔雀扇分香案出,衮龙衣动册函来”[35]6330,其所见的孔雀扇已是布绣孔雀图形。李颀作《王母歌》,极言王母降承华殿之盛况:“羽盖淋漓孔雀扇。”[36]287王母以“孔雀扇”为仪仗,是对唐代宫廷所用孔雀制品的真实反映。
除扇面绣绘孔雀的孔雀扇外,孔雀屏风同样在唐代上层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唐代屏风盛行,除装饰作用,在隔离空间和礼仪方面同样意义重大[37]。杜甫曾吟:“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38]30有学者认为此处指孔雀屏风[39]。孔雀姿态优雅,羽毛文采悦目,自古被称为“文禽”。又因孔雀有“细颈隆背”“足有距”[9]5等习性,世人赞誉孔雀有“九德”[40]。《逸周书》《尚书》等上古文献对“九德”的具体所指虽记载不同,但大都包含忠、信、敬等士人之道德规范。一般认为孔雀之“德”,实际是孔雀所象征比拟的社会伦理道德[41]。孔雀屏风流行于唐代,背后自有其相关文化因素。
在唐代孔雀产地,人们捕猎或饲养孔雀主要为其实用价值。孔雀可充作食物,《太平广记》引《岭表录异》载:“(交趾郡人)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23]3774孔雀也可制成器物,《岭表录异》载:“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探金翠毛为扇。”[11]15南方居民用“养其雏为媒,旁施网罟”[23]3774之法诱捕孔雀,或是抓住孔雀“尾沾而重,不能高翔”[23]3774的弱点伺机将其生擒。南方居民甚至掌握了繁育饲养孔雀的方法,《纪闻》载:“南人得其(孔雀)卵,使鸡伏之即成。”[23]3774唐代人更相信,孔雀怀孕不同寻常,其过程颇具神秘色彩:或是“音影相接”,或是“雌鸣下风,雄鸣上风”,或是“因雷声而孕”,又或是“相视而孕”[10]2。这些神秘的孕育方式,与唐人心目中孔雀的“神禽”属性直接相关[42]。一如唐传奇集《博异志》中描绘东岳真君府邸:“白鹤孔雀,皆举翅动足,更应玄歌。”[23]286孔雀与仙鹤并举,绝非凡俗所在。
到了孔雀输入地,饲养孔雀主要为观赏。唐时宫廷中盛行饲养宠物,以土贡的方式进入宫廷的孔雀便是其中之一[43]。依据孔雀“拍手则舞”[9]5的特性,唐时还出现了专门驯养孔雀跳舞的情况。如新罗国献孔雀“解舞”,唐德宗遂命边鸾在玄武门画出了这只孔雀的美丽姿态[44]23。孔雀也是唐代园林中的重要动物。皮日休吟“烟花虽媚思沈冥,犹自抬头护翠翎”[35]7072,是以园林孔雀的动作神态表达自身志趣。由此即可理解三国时杨修的赞叹:“(孔雀)寓鹑虚以挺体,含正阳之淑灵。首背而鸾颈,徐轩翥以俯仰,动止步而有程。”[45]1574历代孔雀多受上层社会的喜爱,唐人尤甚。唐人之爱孔雀,除爱其优美的外貌形态和“文禽”的美好寓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孔雀常与富贵相联,成为彰显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产地之外,孔雀殊为难得,是上层社会的“专利”;而孔雀的“背连钱文”[14]4124,本身即让人产生“富贵”之联想。唐人边鸾曾作《牡丹孔雀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唐代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宋代《宣和画谱》有:“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46]392显然,唐代孔雀的“富贵”寓意特别直观。
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论者言上层社会的奢侈性消费“令人发狂”[47],唐人之爱孔雀与之关系密切。一方面,孔雀是祥瑞、吉祥的象征。唐愍太子墓室壁画中所绘双孔雀,与仙鹤、凤凰共同飞翔[48]。《酉阳杂俎》说“孔雀辟恶”[28]240,道教更是将孔雀列入仙班[49]22。另一方面,一般认为中唐前人们的审美观念是喜衣饰华丽,崇五彩缤纷之美[50]33。孔雀华丽的外表同这种审美观相契合,孔雀在唐代的风行可想而知。
三、唐代诗歌中的孔雀形象
唐代多南客,而南方的孔雀贡入北地,也被冠以“南客”“越鸟”之名。李德裕吟:“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51]204在美国学者薛爱华看来,“越鸟”一词最初可能是指广义上的扇形尾鸟类,唐代的“越鸟”则专指绿孔雀;唐代文人依赖与鸟类相关的传统进行比喻和寓言,孔雀的鸣叫成为了乡愁的隐喻[52]476-479。“越鸟”在词义上的变化,体现出孔雀在唐人心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游子促成的。比如,岭南是唐时贬谪文人的主要流放地,岭南诗歌多南迁文人之作[53]。时人常吟:“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35]3800、“瘴岭冲蛇入,蒸池蹑虺趋。”[35]5460环境恶劣,毒物繁多,是唐代文人笔下的岭南意象。这种卑湿、多虫毒的环境使北人不由心生恐惧[54]。在这种情况下,孔雀与鸿雁一道成为唐代南客思北归的象征。中唐李涉南贬,贬谪之地尚不及岭南,仍吟“南随越鸟北燕鸿”[35]5429。唐末韦庄不是以贬官身份南下,而是入仕蜀中,但其仍作“越鸟南翔雁北飞”[35]8046以表思乡之情。孔雀这一归乡心愿的迫切象征,代表的范畴已超出了南客北归。晚唐李郢吟《孔雀》:“刺桐花谢芳草歇,南国同巢应望归。”[35]6853孔雀久久无法归巢,李郢将其意象进一步引申为“受禁锢者”。唐代游子寄情的孔雀,大多为“归巢孔雀”“孔雀向南飞”的形象。李白有“魂随越鸟飞南天”[55]809,李涉有“越冈连越井,越鸟更南飞”[56]853,李群玉有“越鸟日南飞,芳音愿相次”[57]16等诗句,皆属此类。
唐诗中还对孔雀的动作体态进行描绘。如李珣的“孔雀双双迎日舞”[58]75,欧阳炯的“孔雀自怜金翠尾”[59]61,李郢的“越鸟青春好颜色,晴轩入户看呫衣”[35]6853等。“舞”“自怜”是女子的姿态,而把孔雀与女子相比,可以说是唐代孔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典型代表当为薛涛。“涛自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辩惠,娴翰墨”[60]103。韦皋出镇蜀地时,南越赠其孔雀一只。韦皋依薛涛的建议,在宅院中开池设笼饲养孔雀。唐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孔雀死去,第二年夏天薛涛也去逝[61]88。据统计,与薛涛及孔雀有关的唐代“孔雀诗”共9首,其中武元衡、王建、李德裕和刘禹锡4人更是直接将孔雀与薛涛一起歌咏[62]。这些诗作中,孔雀美丽却飘零、孤独,薛涛才华横溢却委屈、不幸。刘禹锡《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云:“玉儿已逐金镮葬,翠羽先随秋草萎。”[63]551刘禹锡将二者隐秘地联系到一起,赋予了孔雀如女子般细腻的情感。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开篇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64]44,为后文刘兰芝、焦仲卿夫妻二人的“长别离”埋下伏笔。李白复用此典:“孔雀东飞何处栖,庐江小吏仲卿妻。”[55]1042孔雀形象不可避免地与爱情、姻缘产生联系。《旧唐书·后妃传》记载,唐高祖皇后窦氏“生而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周武帝特爱重之,养于宫中”[34]2163。父母认为窦氏“‘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34]2163。这段佳话后世称为“雀屏中选”,其中“双孔雀”暗含“缔结良缘”之意。如此,唐诗中孔雀多与鸳鸯并用,如李商隐“撩钗盘孔雀,恼带拂鸳鸯”[65]72,顾夐“绣鸳鸯帐暖,画孔雀屏欹”[35]10105等。唐代服制规定,敕三品以上官员“许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袍袄”[66]582,三品以上命妇则“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12]531,寓意相当明显。
孔雀类女子,孔雀喻婚姻,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学者指出,先秦女性尚拥有户外活动和男女交往方面的自由,随着社会演进,礼教的兴起,女性地位随之下降。这种“下降”体现在爱情诗上,便是传达爱意的意象由自然意象(如草木、玉石、鸟兽等)向人工意象(如灯、镜台等)转变。孔雀属自然意象,这显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工意象占据主导地位、女性被物化区别开来。孔雀明艳美丽,虽受禁锢,仍迫切“向南飞”,依据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或可反映出在女性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下,唐代女子社会地位的反向抬升[67]。
四、结 论
在民族交融、文化昌盛的唐代,中原孔雀主要为绿孔雀,在地理上多见于岭南、江淮、滇边等地。西域等地则有蓝孔雀,并通过进贡等方式进入中原。在孔雀自身的“文禽”“富贵”等含义及唐人的审美观念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流行于上层社会的孔雀相关制品,还有孔雀的捕猎和饲养,为唐代的社会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又有“蛇与孔雀偶”的奇特观念,或与“孔雀有毒”之说的广泛流传有所关联。在唐代的诗歌意象方面,除供游子移情之外,孔雀还与女子、爱情产生了联系。在“缔结良缘”的美意背后,或深层次反映出唐代女性地位的反向抬升。而唐代社会中多姿多彩的孔雀文化,仍值得进一步探究。